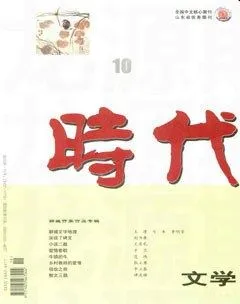谭庆禄散文三题
谭庆禄,男,1954年生,山东临清市人。现供职于聊城市教育局。以创作散文为主,曾先后出版散文集《冬天的树》、《读书的歧路》、《盒子里的日月》等。
乡贤傅斯年先生
一
傅斯年陈列馆建成有日,我身居聊城,却没去看过一次;今年四月,陪安黎先生看聊城风物,在海源阁迁延太久,到了傅斯年陈列馆,又吃了闭门羹:到了下班时间,管理人员走了。这事在我好像是一个象征,我与傅斯年先生似乎缺少某种缘分。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也喜欢收集一些乡贤的材料。然而对于傅先生,这个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最伟大的头脑,我却一直有些隔膜。这在我是深为愧疚的。
与傅先生的相失,当然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大变故中,傅先生选择了去海峡那边,他的著作自然就在毁禁之列,我所能得到的关于傅先生的资料,至今不过三数种;二是傅先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太复杂也太独特。他的复杂也许是一种伟大,就像乍临一道广袤的大山,每每令我们觉得难以把握;而他的独特,又不是随便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成例,以一个这个家那个家就可以概括。我发现,这种困难并不是我一个人遇到。包括傅先生的同时代人,他的师友,也面临过与我相同的困境。他们对傅先生的评价,也往往见仁见智,你看到一条腿,他看到一段胸,到头来,好像没有人抓住根本。
我开始知道傅先生,是在与傅先生不相友善的人的书中。这对傅先生显然不够公平。当然,这些大都在傅先生魂归道山之后,他已经不知道了。也许就算他知道,他也不在乎。
《新潮》时期,鲁迅是表扬过傅斯年的。到了中山大学,傅斯年与顾颉刚同学同好,过从甚密,鲁迅恨乌及乌,鲁迅对傅斯年也就有所保留了,在给章川岛的信中,认为“孟德固有齐鲁方士夸诞之风”。以杂文笔法,将傅斯年的字“孟真”写为“孟德”。鲁迅的评价,固然有主观情感在,但也似乎说出了一点傅先生的个性。知堂在为《亦报》写的随笔中,有两三篇讲到傅斯年,说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说实话,苦雨斋的文章,我一向认为写得好,而这几篇则是少有的坏文章。这倒不是因为他说了傅斯年的坏话,我还不至于那么不讲道理。他先生一直反对在文章里太激动,以为呲牙裂嘴的样子如泼妇骂街,实在难看。可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不光放下绅士架子,开口骂人,而且甚于打落水狗的无聊,未免恃强凌弱之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这种文格卑下的文章,如果不是收在他的书中,真不敢相信竟是知堂所作。知堂对于傅斯年,应该是老师辈的人,他讨厌傅斯年,与数年前的一件事有关。1945年11月30日,即将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发表谈话,说“伪北大之教职工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工职。”知堂见报后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其悻悻之色可见。
傅斯年先生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点像胡适之,“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也是他不平庸的表现。如果众口一词,都说好的一塌糊涂,那就没了意思。傅先生有一个绰号,叫做“傅大炮”。说他好冲动,敢说话,声音高。坏的评价,最严重的还当属知堂所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唐振常以为,傅斯年“是一有性格的血气之人”;罗家伦则认为傅斯年“大气磅礴”,“元气淋漓”;蒋梦麟说:“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是天才。”又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朱家骅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李济认为:傅先生有“高度的责任心”,“极端的认真”而且“没有偏见”。在他的秘书那廉君眼里,“孟真先生是一位‘坦率’也可以说是‘天真’的长者”。在妻子俞大綵看来,“孟真天性仁慈,最重感情”。傅先生与胡适之,谊在师友之间。胡适之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感情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好了,这么多人,七嘴八舌,叫人不知信谁的好了。
二
还是看看傅先生的小事吧。
最先知道的关于傅先生的琐事,是傅先生的胖。不少的人叫他傅大胖子,他自己有时也这样称呼自己。我想,他的外号“傅大炮”,与傅大胖只是一音之转,之间恐怕也有联系。据回忆,一次赴宴回来,他的身高体胖,吓跑了抬滑竿的,看后让我乐了半天。从此在聊城的大街上,看见体胖的人,再也不敢小觑。傅先生的体胖,大概与遗传有关。他的母亲李氏就体胖,而且也患高血压。俞大綵以其不宜食肥肉,不进肥肉,触怒婆婆,傅先生只得从中曲于转圜,以息事宁人。
傅先生胖,也有胖人常有的毛病,就是打鼾。一次与李济先生从宜宾到重庆,乘船,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打鼾太响。后来,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二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害得我们一夜都没睡好。一个胖人,而且打鼾,我觉得这很好。傅先生再也不遥远,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了。
傅先生十三岁离开家乡,二十四岁出洋,此后,天南地北,居无定所,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他爱吃肉包子。这一点鄙人颇有同好,觉得傅先生确是知味之人。傅先生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他的食谱不可能像梁实秋《雅舍谈吃》里那般精细,他的嗜好也符合他“大炮”的性格。他的夫人俞大綵女士出身名门,又是南方人,对他这种习惯印象极深。傅先生讨厌狗,恰有朋友送给他儿子仁轨一条狗,一天午睡时,那狗舐他的手,醒而怒打,狗逃掉了,却打碎了自己的眼镜。夫人与之辩,三天不与交一言。然而三天之后,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对夫人说:“我无条件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吧,闷煞我也。”夫人取笑说:“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每个人都有他的西西弗斯,每个人都有他排解不掉的苦恼。我想,傅先生晚年最大的苦恼就是他的病与他的馋。他不讲究衣着,不积蓄家产,我感到,他的爱好,读书治事之外,就是吃点什么。吃东西使他体胖,体胖使他生病,病又使他不能大快朵颐,他难过极了。俞大綵夫人回忆说:“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这期间,回家的路上,他偶尔就到路边的小吃店,吃他爱吃的北方面食,并嘱咐同行的那廉君秘书:“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有一次,他在学校体育场鱿鱼摊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忘在那里。秘书替他去取,他不让,说还是自己来。后来有人看见,傅校长去取烟斗的时候,又补喝了一碗鱿鱼羹。那廉君回忆说,他为傅先生做记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台湾大学大一国文课本写的一篇短序。这篇目序言的特别之处,就是通篇以菜肴作比喻,“红烧肉”、“炸丸子”一类菜名,全在其中。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到傅先生对一顿饱餐的渴念。想到这一点真是让人黯然。
傅先生是个山东汉子,好冲动,而且不惮于与人打架。“五四”运动,他是游行学生总指挥,但是第二天,“北大学生集会,群言纷乱,”有一人失去理智,傅斯年与之“言语冲突终至动武互殴”。从此不再参加学生会的工作。朋友笑他,“你这大胖子怎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以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一次在巴黎,胡适见他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他!”后来在北京,胡君介绍他们认识:“这就是你当年要杀的丁文江。”不久他与丁成了好朋友。与鲁迅一样,傅斯年反对提倡中医。他认为血液循环发明三百年以后,还要把人的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简直是对人类知识的侮辱。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反对一项议案,与提案人孔庚辩论了一场,孔辩不过,气急而辱骂傅先生,傅先生生了气,说:“你侮辱我,散会之后我和你决斗。”会后在门口拦住了孔庚,见孔庚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他很失望,两手不禁立刻垂了下来:“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吧。”傅先生这副怅然若失的样子,让我觉得很熟悉,也好生喜欢。遇事不退缩,得势也让人,是鲁西人的行事风格,又暗合了“费厄泼赖”的精神。
三
对傅斯年先生的学问,老实说我是不懂。以前,看到过有名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话,感觉不到有什么好。后来年事渐长,经历日多,加上这些年的拨乱反正,对于世间之事,有了一些体悟,回过头来再看傅先生的这些话,才觉得真是不同凡响。
傅先生对于材料的强调,不厌其烦。他认为:“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更进一步指出:“(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的材料便于工作进步,不能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于工作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的这些议论,初读让人觉得未免过分,但细想之,就会知道其中颇有深意。中国的史学传统一直不能让人满意。鲁迅说,一部二十四史,不过帝王将相的家谱。又说其方法,不过是瞒和骗。胡适也曾慨叹,文人有夸饰的习惯,深感“纪实传真”之难。惩于以往的传统,出于对西方现代史学方法的了解,提出所谓“史料学派”的宣言,其意义可谓大矣。想一下近几十年出现的所谓“御用史学”和“阴谋史学”,想一想人们曾经如何删改历史和虚构历史,就觉得傅先生好像有先见之明似的。特别是他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些话如果不是说在几十年前,听起来就像是对今天某些人的耳提面命。沉下心来一想,就知道傅先生是个目光如炬的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通人。
傅先生的一生,一直热切地呼唤和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反对中世纪主义。从新潮时期以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反对拿中古时代的思想来误国误民。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国家应该如何建设,应该向哪个方向走,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
傅先生的思想里,还有一个见解让我感兴趣。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他从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类名词。他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发现这真理的人,不管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是一样的。他的这个观点,看起来十分简单。比如,有人说饿了就得吃饭,说的人是西方人,我们也不能说他说的不对;若是有人说,人饿了应该喝水,就算说的是东方人,甚至是中国人,我们也不能真的去效法。傅先生说的是大实话。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承认,那就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在这片土地走出去的读书人,近百年来,傅先生可以说是最好的了。这一方人对傅先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当然这与傅先生无伤,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
四
终其一生,傅斯年先生似乎从没想过做一个书法家。
他那一代人生逢其时,风云际会,有更重大、更精彩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不仅如此,年轻时代,他甚至还曾说过废止汉字一类的话。当国门初开之际,率先感受世界之大势,兼之曾经沐浴欧风美雨,将世界引向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是天将降于斯人的大任,于是,造就了他们一批风云人物。
然而,他们毕竟属于“过来”的人,从其所受教育看,特别是少年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的,传统的,如傅先生者,十三岁时,已经能够通背《十三经》。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积淀在他们身上,就像长江黄河流淌于中国的大地,这决定了他们既是西方的,又是中国的,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健将们,当初倡导白话,反对文言最力者,如鲁迅、周启明、郁达夫、林语堂、俞平伯、叶绍钧等,到了晚年,也都开始了旧体诗词的写作。当然,写白话文章他们是一流的,而作起旧诗,写起文言,照样也是高手。
书法也是一样。
与当今一些活跃的书法名家相比,傅先生的书法也许不无可议之处,从纯技法的眼光看,或许有某些不足。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傅先生的书迹,也多是一些信函手札,以及文章草稿,于不经意间写成。唯其如此,其长处也显而易见。
最吸引人的,是这些作品的自然气息。对于傅先生那一代人,中国人手中那枝已历数千年的毛笔,依然是主要的书写工具。他们使用毛笔,就像我们昨天使用钢笔和今天操作电脑一样,自然而然。毛笔是他们身体的延续,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用毛笔写字,就像我们吃饭使用筷子一样从容自如,这就使他们写出的作品,绝无当今某些书家们挥之不去的刻意。苏东坡曾云,“瓦注贤于黄金”,“无意于佳乃佳”。傅先生书写之时,不觉得自己在从事书法创作,就没有面对笔纸的心理紧张,以自然的心态,从容写来,如泉水之涌,如江河之流,看去就像自然万物,禀之于阴阳之气,沾夫雨露之泽,发芽抽条,让人觉得本来就应该如此。自然乃艺术的生命,书法肇始于自然,其发展路途之中,又无时不得自然之惠。书法失去自然之品质,便意味着其艺术生命的枯竭。
傅先生之书写,从不想炫耀于人,故而显现出一种自在的精神,一种自信的气度。这一点对于艺术,尤其重要。创作之中,艺术家其实就是值班的上帝,他与美沟通对话,摈弃所有非审美因素的干扰,只有这样,才会于作品之中完整体现人的精神,艺术的精神。文怀沙先生曾言,书法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一种生命形态。”然而,当今某些书家,其心态复杂得很:既要考虑流行风气,又要考虑评委好恶,还得考虑公众认可。这也照顾,那也考虑,八面玲珑,处处作揖,讨好或许有效,结果呢,丧失了自我。与傅先生一辈人的书作相比,判若霄壤。语云:书如其人。作者是书法作品永恒的主人公,其精神气度,才是作品魅力之源泉。由于自信,傅先生的书法常常于不经意间,显现一种磅礴的大气。为董作宾先生所篆《平庐》,及其行书长跋,古雅肃穆,有一种崇高之美,与跋文之意蕴互为表里。具备了书写时的自信,其从容与高贵也就存于其中了。
傅先生的书法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浓郁的书卷气。这种渊雅的气息,充溢于其间,挥之不去。当然,这主要得益于傅先生无与伦比的字外功夫。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是中国文化最为精微的部分,从东方文化最纯粹最充分的地方浸淫出来,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说到底,是本与末的关系。傅斯年先生学贯中西,他的书法,是其深厚的学养的自然延伸,其学养如肥沃的土壤,而他的书法,则是从中生长出来的艺术之树。他的历史学建树,有如横空出世,令人高山仰止。这种学术上的不朽地位,让我们在面对其书法作品时,感受到丰富的想象空间。当然,在其书卷之气的流泻之中,我们也时时感受到其峻拔的骨力。这与傅先生的人格息息相关,一脉相承。于台大校长任上为黄得时先生所书“归骨于田横之岛”条幅,于坚韧卓绝之中,流露出苦涩苍茫之感,睹之令人黯然伤神。
2002/9/1
东坡的个性
苏东坡天赋极高,个性优美,是个十分讨人喜欢的人。《漫浪野录》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此乃一病。’”东坡又是一个诗人,其运用语言的能力,古今很少有人能及,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他的爱说话也是很有名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有,不说出来,那就不是东坡了。《曲洧旧闻》卷五:“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他才学超绝,又辩才无碍,平时谈笑风生,议论纵横,常使他的论敌感到头痛,也令他的朋友为之担忧。他的弟弟子由,是最为他担心的人。“子由监筠州酒税,子瞻尝就见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祸。及饯之郊外,不交一谈,唯指口以示之。”东坡交友极广,爱东坡者亦众,故提醒或劝诫东坡的人也多。
《石林诗话》卷中:“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文)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言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文与可年稍长于东坡,与东坡甚友善,后人因误以为东坡之表兄。文与可劝诫东坡,宜也。毕仲游少东坡十一岁,也曾对东坡的言论表示担忧,作《上苏子瞻学士书》,其中有云:
“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记序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救溺也。”对于文与可的话,东坡不能听,但是毕仲游的议论,据说令东坡“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文与可的劝戒,应在任杭州通判之前。至入朝之后,入狱之前,仍不能改。在此期间,晁端彦数以忍事箴之。《曲洧旧闻》卷五:“晁美叔(端彦)每见,以此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叹久之,曰:‘朝廷若见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杀了我后好了你。’遂相与大笑而起。”美叔的默然,东坡的浩叹,足见他们不是没有看到杀身的危险,只是箭在弦上,身不由己而已。最后,东坡与美叔开的玩笑,差不多已经够得上黑色幽默了。不久,东坡为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 ,何正臣等锻炼成“乌台诗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摄苏轼至御史台”,让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遭受牢狱之苦。
东坡以诗入狱,入狱之后,仍不能罢手。作诗二首,托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其诗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出狱后,次狱中寄弟辙韵,又赋诗二首,《孔氏谈苑》卷一:东坡出狱,贬黄州团练副史,“狱卒曰:‘还学士此诗。’”“既出,又戏自和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子瞻以诗被劾,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
牢狱之苦对于东坡来讲,是刻骨铭心的。《善诱文?子瞻以己谕鸡》:“赦罪放免回家,每见庖厨有活物,即令放之。尝有言曰:‘吾得罪处囹圄,何异鸡鸭之在庖厨,我岂复忍杀彼之生命耶!’”然而作为诗人,往往忍不住技痒。贬到黄州,已是戴罪之人。所作诗文很少,更少外传。元丰五年作《赤壁赋》,六年,友人傅尧俞(钦之)有使至,遂书《赤壁赋》以寄之。在跋语中,东坡嘱咐说:“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来,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活脱再现了一个诗人对于言与不言的矛盾。
元丰八年,苏轼被召回朝,后司马光旧党执政,东坡渐被重用。初,东坡为礼部郎中。《宋史·苏轼传》云:东坡旧善司马光、章子厚。“时光为门下侍郎,子厚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子厚每以虐侮困光,光苦之。轼谓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许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然而东坡与司马光之间,遭贬谪时,有更多的一致性,一旦同朝共事,也不是没有分歧。有了分歧,未必当面有所表示,背后却免不了发泄发泄。《铁围山丛谈》卷三:“东坡公元右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及司马光死,朝廷命程颐主其丧事。程颐泥行古礼,苏东坡每戏之,遂致与二程及其之徒结怨。《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丧事。是日也,礼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炎,问之。公炎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尘糟陂里叔孙通也。’”
东坡不改故常,不为当政所容,不久,出知杭州。前辈重臣文彦博再次提出忠告。《明道杂志》有云:“苏惠州尝以作诗下狱。自黄州再起,遂遍历侍从,而作诗每为不知者咀味,以为有讥讪,其实不然也。出为钱塘,来别潞公,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喜者诬谤。言之再三。’……又云:‘愿君不忘鄙言。某言老悖,然所谓者希之岁,不忘也善之言’”可谓语重心长。是一个前辈对一个后辈的关爱,也是一个老人对一个旷世天才的珍惜。然而,天生东坡,不容他发言,就像一只鸣禽,不允许它啼叫;就像精金美玉不允许它发光,或者一架钢琴,却令它不要发出声音。
东坡黄州之贬,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文人,怀抱兼济天下之志,应该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而东坡不这样想。六年之后,他接到复其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的任命后,给友人王巩(定国)的书简中说:“谪居六年,无一日不乐,今复促令作郡,坐生百忧。正如农夫小人,日耕百亩,负担百斤,初无难色,一日坐之堂上,与相宾向,便是一厄。”
东坡是一个洒脱的人,官爵的高下,俸禄的厚薄,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可以在最困苦的日子里获得别人锦衣玉食不能换来的快乐,他的达观,令他只是在最小的程度上依赖于外物。如若以这种东西让东坡苦恼,不啻缘木求鱼。所以想让东坡变成一个乡愿,那也是不可能的。《西余琐录》叙东坡知登州,未几被召,“道中遇当时狱官,甚有愧色。东坡戏之曰:‘有蛇螫杀人,为冥官所追,议法当死。蛇前诉曰:诚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赎。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黄,可治病,所活已数人矣。吏收验,固不诬,遂免。良久,牵一牛至,狱吏曰:此牛触杀人,亦当死。牛曰:我亦有黄,可以治病,亦活数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狱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杀人,幸免死,今当还命。其人仓皇,妄言亦有黄。冥官大怒,诘之曰: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汝为人,何黄之有?左右交讯,其人窘甚,曰:某别无黄,但有些惭惶。’”
《论语?卫灵公》:“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依照孔子的说法,苏东坡算不上一个知者。然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东坡就因为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机心有韬略的人,所以他可爱。
2001/11/11
田野的树
一
我喜欢树。北方的田野上,总是寸土必耕,舍不得让一尺半尺土地闲着,难得种上一株两株的树,这未免让我有点失望。好在北方的树大多不是什么珍稀的种属,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只要有一截枝条,或者一粒种子,遇着水土,它们就会生长,所以,田野上总还是有一行一行,或者一株两株的树的。特别在庄稼收割之后,那树也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田野上的树不同于城市的树和村庄里的树。城市的树,为了踵事增华,一般都经过慎重挑选,多是珍奇名贵的品种。但是,它们虽然生在都市通衢,有园林工人四季的服侍,看似尊贵得很,其实不过是城市的装点,难脱仆婢的地位;乡村的树要好一点,以其略近自然,“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那样的树我喜欢。生长在一起的树,就是所谓的树林,在田野上尤为难得。试想,一大片树长在一起,如果是种类繁多的杂树,而且都已经长得很大,那很好。一片树林兀立于平阔的原野上,打破粮食或经济作物的一统天下,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林木秀,则鸟雀至焉。风雨至时,树林发出声音,那是很雄浑的。等到农闲无事之时,一个人,或二三好友走进树林之中,也比走进农田的感觉好多了。
不过,平原上除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果树,是很难得有所谓树林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看看那不能成林的树了。而不成林的树,一排排的站立于路边或者沟沿的,以及一小方一小方的幼树,像出操的学生,或是过去上工的社员,很守纪律的样子,我不怎么喜欢。若是远远看去,我以为似乎还是一株株独立的树更有意味。陶渊明诗云:“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陶公也喜欢独立的树。这叫我觉得很有意思。
二
田野上的树一般都长在井沿上,或者长在坟地里。不过也不尽然,也有就在田野的中间凭空长起来的。唯其稀少,才更加可贵。
井沿上的树是人们有意栽种的。井沿是一块必要的空地,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种一株树,此其一;人们在井上浇水,往往时间很长,有一株树就是一柄绿色的伞盖,避免太阳直射,此其二也。不过,有时候井沿上也舍不得种榆槐杨柳之类,而是种上一株枣树。作为遮阳之具,枣树的叶子是嫌稀疏了些,却也少争夺一点庄稼的阳光,而且秋来还多了一重收获。田野中的枣树不同于村里,因为较少有孩子攀折,它的枝柯往往垂得很低,显得较少提防之心,看了让人感到舒服。我在枣树之下摇辘轳浇过水,那淡淡的树荫似乎也能拂去一些太阳的毒辣。到了枣熟时节,早熟的枣子也会落入井中,等随着水斗升上地面,吃起来就多了一份清凉。
知堂以为,杨树宜种于丘墓之间。也许南方是那个样子,北方据我所见,坟地里一般是种一些松柏,那是大户人家的坟地,一般的,我倒是看见种上一株两株的柳树。坟地里的树一般长不大,就被别人芟去了。
在我们村的东南方向,邻村的土地上,远远可以看见有一株树生在地里。那树生得高大茂盛,整整一个春夏,都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树冠,在晴空之下,显得很是触目。它虽然就在目光所及之地,却难得有机会走近它。听走近过那株树的人说,那是一株平原上少有的核桃树,据说,核桃的果子并不是一开始就皱巴巴如老太婆的脸,也是青绿浑圆的,收获之后,埋入土中,让外面的青皮腐烂掉,剩下的才是我们常见的核桃。核桃这种奇异的经历。更增加了我们的对那树的向往。可是,一直到我离开老家,也不曾走过去,结识那株大树。这可以说是我一个小小的遗憾。
三
人在路上走,看到田野里一株一株独立的树,心总是难免为它所触动。秋天里,庄稼都已经芟割回家,田野更其空阔辽远,一株树孤零零站在那里,有如一个孤独的人。特别是一株小树,恰像一个孤独的少年,尤其使人牵念。一株独立的树是自足的,它不依赖于别的什么东西而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昨天,我在车上走,看到了几株孤独的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一种树长在远处,我叫不上它的名字。当然,我叫不上它的名字只能怪我,不能怪树。这树长得很有意思。它的树冠从一个中心向四围辐射,像是凝固了的绿色爆炸,或者像凝固了的焰火。它的周围没有别的树,也没有什么庄稼,它就孤单地自己站着,持久地演示着绿色辐射的特技。白杨一般总是作为行道树,给栽在大路的两边。站成一排的白杨很是威风。行道杨树长到很大,也很有看头,不过还不如单独长着的白杨更有意味。茅盾曾说,白杨是一种力争上游的树,又说它的枝桠决不旁逸斜出。我想,他的白杨,是在新疆和河西走廊看到的,所谓的新疆杨,与我们这儿的杨树不同。我们这儿的白杨,也是有一根主干,努力地向上伸展,下面的枝桠如何,它好像就顾不上了。杨树的干是很直的,不过那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直线,远远看去,它像是书法名家笔下的线条,极有意味,又富于变化。它的树枝细而且短,向左向右参差地伸展,树叶也稀稀落落,漫不经心。这不要紧,只要有了那条贯通上下的主干,这株树就显得极有章法。直说了吧,单独长在大野里的一株杨树,那是很美的。
不过,最让人感到震撼的还是那株梧桐。
我在冠县东北部的兰沃乡看到一株梧桐。兰沃是水果之乡,地里多是梨树,路边都植白杨,那株梧桐显得很突兀。我老远就看见了它,并惊异于它的沉着和大气。这株梧桐异常高大,异常雄伟。已经是晚秋天气,它还披挂齐整,似乎尚未感得秋的来临。它的树干很粗,很直,也很高,树冠也很宽博,枝杈一层层地堆叠着,充分使用着每一寸空间。那绿色是秋之绿,是不可摧折的生命力的体现,是历尽苍桑的波澜不惊。它自然达观,心平气和,不骄不矜,不怨不怒,如一个历尽忧患,火气消尽的老人,又像一个无忧无惧,心胸博大的树之王。
四
看到田野上孤独的树,一般都是在晴好的白天。到了傍晚,或者遇到雨雪的天气,人们都要回到屋顶之下,剩下那树在地里孤单单地站着。我没有观赏过风雨之中,那孤独的树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不过我想,那美丽的白杨和沉着的梧桐,应该是不怎么惧怕风和雨的。即使再严重的境遇,我想,那树也会坦然承受,至少不会失态。
与成片的树和成排的树相比,孤独的树更能体现个性,因此更易让人辨识。我喜欢独自生长的树,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孤独的树一般都显得落落寡合,也很是谦虚,这我很喜欢。我真希望自己能有陶渊明的悠闲,提一壶酒,走到田野里的一株树下,将酒壶挂在枯枝上,或席在而坐,或干脆就躺在树下,那种时光真是叫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