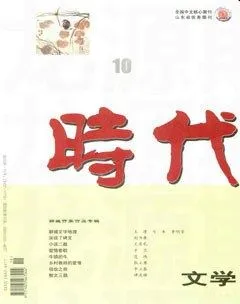记得是1985年,我随一个诗人采风团来到鱼山,拜谒长眠于此的建安诗坛雄杰曹植。站在海拔仅八十余米的鱼山之巅,蒙蒙细雨打湿了我的衣衫,也打湿了我的诗情,我诗歌的情愫开始萌芽。我相信,采风团的所有诗人,向东南远眺绵延起伏的泰山山脉,向西北极目郁郁葱葱的鲁西平畴,向脚下俯瞰滚滚东逝的黄河,定会像近两千年前的东阿王曹植,诗的激流在心中涌动,诗的浪涛拍打心壁。一阵秋风吹过,披襟当风,仙袂飘飘、神思飞飏的,当不只是忧思萦怀的诗歌先贤曹植,还有鲁西这块黄河冲积平原上的所有现代诗人吧?
那时,新时期文学正沐浴着春光;那时,鲁西的诗风劲吹,吹绿了鲁西。以张维芳、姜建国为旗手的聊城诗歌群体极为活跃,以姜勇、弓车为主的青年诗人开始步入齐鲁诗坛,鲁西诗坛正以它的葱绿、葳甤,开始进入全国的视野。
上世纪八十年代,鲁西聊城的诗歌创作之活跃,诗事之多,回顾起来,真是令人艳羡。创作学习班、研习班,诗歌大赛,作品研讨,诗歌采风,请省里、京城、外地的著名诗人前来讲座授课,几几乎令人目不暇接,好似每一株树、每一棵庄稼都被染上了诗的色彩,摇曳着诗的风致。
也是在1985年,扛枪走向诗坛又刚刚脱去戎装的姜勇,与同龄的弓车等人,组建了聊城地区青年诗人协会。几十位二十余岁的红男绿女,以青春靓丽的仪容、朝气勃发的姿态、新潮理念的自信,开始了诗歌的纵深开拓和深层挖掘。聊城的大中院校,也纷纷成立了文学社、诗社,尤聊城师范学院(即今天的聊城大学)为重,那时的莘莘学子们,有多少青春梦枕着诗做的,他们相信,诗歌开花的时节,也就是他们诗意人生的辉煌时节。学生如此,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也涌现了无数的诗爱者,其中不少人诗歌创作视为神圣、伟大的事业,真的信奉曹植的哥哥曹丕所言的诗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把诗当作生命旅程中的不二选择。
各类文学期刊也应运而生。当时的聊城文化局创作室办起了第一份文学综合杂志《绿野》,1982年聊城地区文联成立后,《东昌文学》编辑部成立,编选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聊城地区青年诗人协会的会报《七音河》,一俟面世,便以其新锐的风尚,给鲁西诗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鲁西的文学,也像全国各地一样,逐渐边缘化,但是,聊城的诗歌不仅没有,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有关单位、有识之士及一些老领导和企业家的大力支持赞助下,在张维芳、姜建国、朱希江等老诗人毅然高举诗歌的大旗,弓车、臧利敏等中青年骨干辛勤播种、耕耘,以1995年聊城诗诗人协会的成立为标志,鲁西诗坛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引起了全国诗界的瞩目。作为诗人协会会刊的《鲁西诗人》(老诗人苗得雨题写刊名),以每年平均出刊六期的速率,更以其海纳百川、唯质是取的信誉,迅速被全国诗界、尤其是中青年诗人所认可、所称誉。正如在面向全国的征稿启事中所说:“《鲁西诗人》虽冠之以‘鲁西’,但她像鲁西大平原一般襟怀博大且质朴真诚。多年来,她坚持开放式办刊方针,面向全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她的特色是:……大气、真实。九曲黄河在我们身边滚滚流过,《鲁西诗人》正是秉承了她的深沉和宽博的气质,这种基因是难以改变的,也是改变不了的。求真,是她一以贯之的风格,你在投稿前,要掂量一下,你的旋律是不是起源于你的真实心跳,就像黄河的波浪一般。”实际上,她的特色,正是鲁西新时期诗歌的特色,是秉承了曹植基因的特色。也正是她的不媚俗,不向金钱投降,不做商品的奴隶,坚持诗的高品位,才赢得了众多诗人的青睐。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包括一些名家,比如我省的老诗人苗得雨、桑恒昌,还有著名诗人谢明洲,活跃在全国的青年诗人黑马、杨健等,将力作佳构投给她,将她装点成全国综合性诗歌民刊中的一棵奇葩。迄今为止,她已出刊九十期,作者遍及全国。编发的一些作品还被选入中国年度诗歌选等选本。
除了全力办好会刊外,诗人协会的其他诗歌活动也颇为丰富,每年都要搞一到两次诗歌采风,遇有重大事件不缺席,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大地震,或出专栏、专辑,或举办诗歌朗诵会,发出我们的声音,为民生、为文明进程,为社会进步鼓与呼。还搞了两次全国性的诗歌活动。诗人协会除本身编辑出版了十几部诗集外,帮助协会会员编辑出版个人诗歌集几十部。诗人协会成立后的这十五年间,入会会员已达三百余人,形成了老中青梯队结构、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这些人中,有宝刀不老者如张维芳、姜建国,他们年过古稀,依然笔耕不断有新著问世,中青年诗人更是成了这个队伍的中坚,一颗颗诗星冉冉升起,在诗国的星空熠熠闪烁。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鲁西诗歌的繁荣期,那么,九十年代就是成熟期了,而本世纪以来的这十年,则是鲁西诗歌的黄金期,这,主要表现在涌现出一批实力派中青年诗人,弓车、臧利敏、秀水、田兆阳、书心、仇长义、康学森、淼淼、文梦、杨吉忠、张桂林是其中较为突出者,他们都在《诗刊》、《星星》等中国核心诗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在全国各诗赛中连连获奖。本期《时代文学》推出的,就是这一批人中的代表。这些诗人,功力深厚、扎实,审美层次高,具备较充足的现代诗学理念,不少人还具有较高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并善于从现代西方各流派中汲取营养,勇于探索,在当代诗潮中走在了前列,现代诗的写作技巧运用娴熟,这就保证了他们诗艺不断精进,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然而,无论上面论及的这些中青年实力诗人,还是新生代诗歌爱好者,还是老一辈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守着自诗经、楚辞、再到建安文学、中唐诗、五四白话诗中国主流诗歌传统,从生活中、从社会现实中撷取诗情画意,在内容上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注重修身和道德修养,“不语怪力乱神”,放达但不轻佻,狂放但不狂妄,智慧但不油滑,犀利但不轻薄,深邃但不绝决,独步但不险怪,旷达超脱但不玩世,先锋现代但不艰涩,秉承传统但不滞后,有承担、有肩负而无恶习,极少游戏文墨之作。即便是抒写小我情怀的诗,在外延上,也与“大我”相契合,在诗风上,就是质朴,大气,情感充沛。另外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平易,亲切,不偏激,不乖张,有亲和力。孔子讲求中庸之道,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无疑在这些诗人身上有着难以更改的遗传基因。
这些特征,这些诗风的形成,追根溯源,与鲁西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积淀、人文传统有关。聊城是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期名士辈出,现代的史学家、不畏强权的傅斯年,还有国学翘楚季羡林,国画大师李苦禅,都是聊城人引以为傲的重量级文化名人;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耸立在明洪武年间修建、至今保存完好的光岳楼下;书业印刷在清朝至为繁荣;《水浒传》、《金瓶梅》、《聊斋》中多处事件、多个人物发生、生活在这里。可谓钟灵毓秀之地,文化繁盛之乡。聊城地处山东的最西北,战国时属齐,与赵毗邻,这个孔孟之乡就不可避免地濡染上了燕赵的豪侠之气、慷慨济世的风尚;虽是沿海省份,但她与其说接近海洋文明和商业文明,不如说与中原的农耕文明更相近。然而,西风吹来之前,运河是中国交通大动脉的时代,明清两朝她又是沿运河的重要商埠之一,所以,又遗传了一些商业的脉息,至今屹立在运河岸边的山陕会馆就是明证。故此,你很难胪列清楚,聊城,到底是农业文明还是商业文明,是黄河文化还是运河文化,是齐鲁文化还燕赵文化,是沿海文化还是内陆文化,或者不如说,兼而有之。不过,我认为,鲁西新时期的诗风,与农业文明、与黄河文化更贴近,兼有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的特质。
这就是我题目中所说的“风”,是融会中原之风、燕赵之风的“风”,是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中的“风”,是绿色的风,是健康的风,是清新的风,是质朴的风,是散发着乡土气息的风,是可以穿透灵魂的风,是可以和大自然相互唱和的风,是可以在心灵里吹起波澜、掀起千尺巨浪的风,是激浊扬清的风,是从天籁里吹来的风……
这,就是鲁西的风。
本期《时代文学》推出的这批中青年实力诗人,在他们的诗句里,在他们的平仄中,我相信,你会体验、感受到这鲁西“风”的。他们风格不同,视角各异,或灵动若蛱蝶初飞,或悠远似长河落日,或雄奇或泰岳耸峙,或飘逸似白云出岫,或清奇若清泉过石,或跳脱似瀑布飞溅,五彩纷呈,但尽皆张力十足,诗思饱满,美不胜收。在此,不再一一点评,将他们在《鲁西诗人》“诗星存照”中的“诗观”移来,也算是夫子自道吧:
诗歌,它首先应该是自然、平实而深刻的。它是最简洁也最具包容性的文体,有时只几个字,却包涵着大海般深厚的内容。
诗歌在本质上应该是纯粹的。它往往是载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在飞,欢乐与痛苦,都因了它的纯粹而放射出令人心动的光华。
——臧利敏
用童心、爱心、诗心书写汉语诗歌的纯净和高贵之美。诗格即人格。
——秀水
诗既然能够精致、贵族、高雅,又何尝不能大众、明朗?以文字的排列和错综复杂和读者玩游戏捉迷藏,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和快节奏的时代,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
拯救诗歌,让诗歌在现实和梦想中找到赖以生存和茁壮的土壤,我们任重而道远。
——田兆阳
当你的心态不再浮躁,当你的眼光开始专注,当你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当你把整个的生命信任地相托,你便获得了爱,从而也开始抵达诗的境界。彼此,你的心就有了生命的光泽,有了心灵的深度,有了自己独特的视角与表达。
——仇长义
写诗已不是一个职业,诗人正挤在一个超员的公共汽车上,同工人、律师、医生、学生、职员、小经理、屠夫、生意人、贩子、妓女混在一起。诗人一点也不高贵,高贵的是他的心。诗人在自己的疆土上是一个君王,笑谈天地,纵横时空,一生为诗无怨无悔。
——康学森
从词语到具象到意象,到一首诗,是作者本人内心不由自主的表达、需要、坦露和归宿。
在诗里,我从没感到过孤独,倒是一种温暖。当我的一些心跳、一些思索、一些瞬间的思想的火花,想要走出我的内心,变成一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那才是真实的自我。
——崔慧君
与诗结缘是一个人灵魂至高无上的幸福,是具有归宿性的幸福。也许我们不能握遍此刻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手,也许我们不能一一注视历史上每一个人的眼睛,但赞颂阳光、月色、花朵和爱情的共同经历,让我们在缪斯的怀抱里,有了并肩的合影。
诗对语言是应该有所贡献的,它的贡献就是发现、挖掘、创造汉语的张力、弹力、活力、韧性和深刻性、幽默感。
——杨吉忠
从一滴眼泪里,读出一个大海。从一份从容里,诠释喜怒哀乐。我想用一种简单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源于生活深处的思考。我想在诗的中央静静地做一个美丽的女子。
——宋开颜
诗人应该清晰地认识自己,清晰地认识世界;努力拂去世俗遮蔽和尘埃,准确地把脉一株草的律动,说出一朵花的心事。
——张桂林
至于我,弓车,就用刚刚完成的一首诗作为诗观吧:
献出宝藏
看,他们纷纷献出了宝藏
最早的是麦子、杏
他们一同让芒种成为收获的节气
而大多选择了在秋天
梨、苹果,玉米、大豆、高粱
还有让我们保温的棉花
南方的椰果、边陲的葡萄、哈密瓜……
其实,纷纷献出宝藏的
还有野蓟、蓖麻、狗尾巴草、菟丝
这一类卑微的植物
比如蒲公英,用他的轻
悄悄地带走季节的沉
比如野菊,把星星布在大地之上
桑树最为直接,他的叶子
其实就是至为天然的丝绸
那么,作为享用者,我能做些什么?
我,只能歌颂劳动,歌颂庄稼
歌颂一切作物,歌颂一切植物
直到把心呕出来
作为一枚鲜红的果实,献给大地
献给劳作者,包括蚯蚓
让他在地下松土,让他知道有人欣赏而毫无怨言
感谢《时代文学》,给我们鲁西诗人们一个集中展示的机会和平台,不过,这次选发的只是一部分中青年的作品,还有一些优秀诗人因种种原因没有参与或者漏选,特此说明。
2010年8月29日于聊城运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