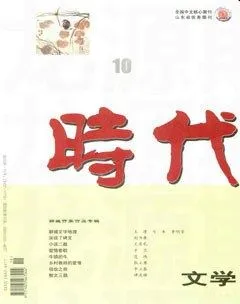鲁西小说界暗流涌动的创作局面
鲁西(聊城)由于地处省界边区,在整个山东文坛上,那个地方的小说创作给人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感觉,作家们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不易引起主流文坛的关注。其实,鲁西是一个文化积淀极其丰厚的地方,脚下躺卧着黄河故道和运河遗址,面前流动着《水浒传》和《金瓶梅》的生活场景,现代的两位文化大师傅斯年和季羡林就从那里一步步走出来。在这样一个地方,文学(小说)创作不会没有它施展本领并发展壮大的机会。这期“聊城文学专辑”中的几篇小说,虽然只是鲁西作家们创作道路上的一点点印迹,但透过它,也许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鲁西的小说创作其实是呈一种暗流涌动的局面,各种风格的作品都不乏精品力作,各种样式的努力都从来没有松懈。当我们合上这期杂志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听到了远方潮汐的隆隆响声?
扎实有力的现实主义写作
现实主义写作,不要说鲁西的作家,也是中国大多数作家的首要选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左建明、张方文为代表的鲁西小说家,很好地秉承了这一写作传统,给山东文坛贡献了一批闪耀着光彩的优秀作品,新时期的文学记忆里至今还跳荡着他们矫健的身影。
李立泰是这一写作样式的优秀继承者。不论是那篇给他带来广泛声誉的《最后一个和尚》,被《小说月报》选中的《抻炕》,还是那组更被频繁转载的《故里素描》(《中华文学选刊》、《短篇小说选刊》等),都对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呈现,人物置身在庞大幽深坚硬无比的历史境遇中,进行着或者演出着他们令人唏嘘感叹的悲喜剧。读他这种类型的作品,总是给人一种重温历史、体验现实的感觉,所以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朦胧的印象:作为作者的李立泰一定信奉文学大师那种“文学是历史秘史”的说法,并且用一篇又一篇精美之作进行着这种颇具庄重色彩的写作实践。当然,这样来说李立泰,好像还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他在忠实地摹写历史和现实的同时,似乎更为讲究叙事,更为追求境界的高远,这也就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柳青,而更为靠近沈从文,比如他那篇《腰窝镇西郊》,简直就是另一篇《边城》,在不大的篇幅中写尽了腰窝镇的现实状况、世态风俗和人情世故,活脱脱一幅惟妙惟肖的社会风情画,让人有一种阅读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的错觉。这种风格的作品,在李立泰的文学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他创作道路上的终极目标。这当然与他的审美情趣和对文学(小说)本质的理解有关,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变得更为轻盈,更为耐读,更有韵味,作者的立场也不再变得那么直接鲜明,一切交由人物自己演示,寓贬褒于看似随意的细节描写当中,这期专辑收入的小说便有这种特点和韵味。但让人吃不准的是,这种散淡冷静的写法是否会消解一定的深刻和力量?李立泰的作品不管数量还是质量,都像他文字上的功夫一样呈洋洋大观之势。
这种风格的写作者中还有赵一震。我最先读到的是他的《故里三题》,写得那么简约、从容而老到,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讶,尤其是第一题《郭姑奶奶》,在极其短小的篇幅中,赵一震用他形象的文字,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了一桩动天地、泣鬼神的旷世爱情,令人叹为观止。赵一震还不止于此,更把这个故事置于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不经意间就给这个“三角恋”赋予了深刻的含义,其轻松的写作姿态给人以深刻印象。《尼龙袜子》也是写爱情的,赵一震同样一点儿也不煽情,甚至还更写得平实散淡,但其余音绕梁的效果足以让读者回味再三。赵一震的大部分作品都有这种特点,尽管写得不动声色,态度尽量深藏,但文字间透出的对历史的拷问,对社会的批判,还是呼之欲出。现在这个专辑中的三篇沿袭了他这种风格,但较之以前的作品写得满了些,可能也透出了他的某种变化。赵一震有意将这类作品写成一个系列,显露出他在创作上执着的追求,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范玮的前期作品当然更有这种笔记体小说的特点,其成名作《老元和老田》(《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就已达到圆熟完满的程度,其后的一系列作品如《黄瓜园》、《槐花》、《护秋》、《武功·玩笑》等等,像一幅幅黑白相间的中国画,虽没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却更似天边残云、树梢临风,仅仅是一鳞半爪的呈现,便尽得风流,读后令人有三日不知肉味之妙。范玮在笔记体小说上的探索,可以说继汪曾祺、何立伟(前期)等之后,将这一派小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境界的高远、语言的考究和气势的掌控,都不应该是他这个年龄的作家所能达到的。
在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中,王秀礼的作品大大增加了批判的力度,所使用的语言像坚硬的石头一般沉重,且充满随时碎裂、爆炸开来的暴力色彩,这在他以描写为主的作品《老桥》和《挽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两篇小说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关联,但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会感到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描写的都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也即“三角”关系,在这种较为老套的构思中,王秀礼却赋予了它们强烈的时代关系,所呈现出的不再仅仅是伦理和道德,而是更为重要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是人在历史夹缝中和现实砧板上所进行的挣扎和哀嚎,所迸发出的人性光辉一如黄昏时分地平线上如血的残阳,既让人感到艳美又使人心怀惊恐。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在这两个颇有些雷同的故事框架中,王秀礼便传达出了决然不同的寓意,读起来却又让人体会到异曲同工之妙。我不知道在王秀礼的写作中,这种刚烈强硬充满力量的作品,是否就是他惯常使用的写作风格,因为我同样读到过他另一种类型的作品《北村的月夜》,差不多通篇都是叙述,但对所反映内容的批判力度同样强烈。杨林鸿基本沿用着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比如他的《一人办公》,他的《舒服》,大约与他长期在机关工作的体验有关,一些不为外人所熟知的官场情态,都被他信手拈来,惟妙惟肖地加以再现,传达出了官场复杂、黑暗的社会环境,置身其中的人心性的变态和良知的泯灭。这应该是杨林鸿的写作优势,但由于与写作对象靠得太近,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他的想象力?比较起来,他那篇字数不多的《蝙蝠》,仅仅使用了一个场景,就将一个人孤独时分所产生的幻觉精彩绝伦地表现出来,已经很有些表现主义小说的特点了。看得出,杨林鸿是个多面手,很多领域都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所以也便诱惑得人们予以关注。
为了写这篇评论,我设法找出了刘书康的一些作品来读。我很庆幸这样集中读他的小说,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鲁西的文坛上,居然早就存在着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这种感觉不仅源于他那独特的经历,更为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卓越品质和纯粹精神而敬佩不已。不论是他的《繁衍》(《小说选刊》选载)、《疯恋》还是《出逃》,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阅读期待。在我看来《疯恋》一篇堪称经典,作品一上来就写一个老人面对他躺在炕上的结发妻子絮叨不已,还喂她吃喝,还与她同眠,以至于几天过后(作品结束时),我们才从前来阻劝他的人口中得知,他的老伴其实已经得绝症死去了……但作品通篇没有一点哀伤气息,有的只是老人对他与妻子美好岁月的回忆以及力图使这种美好继续下去的努力。作品写得感人至深,读后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误读了碑文》同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力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刘书康居然从一个纯属个人而且带有性色彩的视角来述说那段宏大的历史,不能不说是一个有些冒险的选择,但这样一个冒险却又被他如此完美地予以完成,足见出了刘书康不凡的写作功力。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改造妓女的故事,我们已经见得不少了,至少留在记忆中的还有苏童那篇《红粉》,但与苏童不同的是,刘书康的妓女改造故事,被他更多地赋予了个性解放的“狂欢”色彩,也即更多地从性的角度来表现由下贱妓女到尊严女人的漫长、复杂而又痛苦的历程,并与轰轰烈烈的社会发展接合在一起,从而使这种改造脱离了狭隘的悲喜剧色彩,而有了一种正剧的庄严肃穆感,加之作者使用了一连串与性有关的人物、情节和场景,又把这种颇富正剧色彩的气氛推向了欢乐并抵达到“狂欢”的境界。当然,刘书康如果仅是这样解说历史和社会,还似乎显得过于达观甚至浅显了,作品最后,残缺不全的碑文的出现,才又把这种看起来有些无节制的狂欢拉回到严峻的现实中,个人的行为淹没在了宏大的历史和严酷的时间中,凸显出难以逃避的谬误和荒诞,由此作品在狂欢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一种高超的“反讽”效果。对于刘书康所作出的努力和达到的成就,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研究,是令人惭愧的一件事。
丰富多彩的现代小说实验
上世纪六十年代,约翰·巴斯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枯竭的文学》中,认为传统文学的形式与技巧已经走到了尽头。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观点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了,但他主张对文学形式进行实验和创新,却给许多作家以有益的启迪。就中国当代文坛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较为年轻的作家不甘心传统写作,广泛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勇于创新,大胆试验,开创了一波又一波实验(先锋)文学的新局面。
尽管山东文坛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较为保守,但毕竟也有不少作家在不懈地做着这种努力。作为鲁西作家的于兰先在散文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近年来又转向了小说创作,如江湖侠女孙二娘拎着李逵的两把板斧杀上了文坛,其靓丽的姿态令人眼前一亮,《墙外》、《红线》、《美人鱼》、《有关一只狗》等一篇篇富含现代艺术特色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桃花雪》打乱了事件的时间顺序,将故事情节拆开了重新组合,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里,续写了中日两个饱含母性的女人漫长一生间的仇恨和斗争,尽管时间跨度巨大,但于兰写得紧密圆润,气韵充沛,见出了现代小说的艺术魅力,是传统小说手法所不易达到的。作者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让自己笔下这两个人物穿越仇恨,最终达成了和解,也表明了她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所渴望得到的一个结局,虽然它可能与事实真相并不那么一致,但却透出了于兰“让世界充满爱”的良苦用心。《陈苹、白脸女人和乐四季》是我更为喜欢的一篇小说,在这个分成三段式的作品里,于兰更把重点放在了“如何叙述”这件事上,通过三个看起来彼此关联不大的故事,叙写了一个叫乐四季的人由于童年记忆的影响而搞糟了自己的生活,并最终导致生命毁灭的故事,留在潜意识中的阴影竟然如毒蛇一般追随着他,让他欲摆不能,不光摧残了他的精神,还毁坏了他的肉体。这样看来,三个故事在主题上又是彼此关涉的,甚至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小说很好地利用了“苦瓜”这一象征物,串联起三个故事,同时它自身所具有的寓意也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我们盼望于兰把现代小说这把板斧挥得更高,在萎靡而守旧的山东文坛上砍出一片天地来。
范玮的笔记体小说本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但他说变就变,毫不客气地抛弃了掌握到娴熟地步的创作技巧,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正式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创作实践,至少执意求变的勇气先就令人敬佩,而转变后的作品,诸如《住在树上的人》,诸如《刺青》,诸如《孟村的比赛》,诸如《乡村催眠师》和《桃镇之行》等,也正在以一篇比一篇成熟、一篇比一篇完美的姿态呈现出来,其变化之大让人瞠目,也给波澜不惊的山东文坛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些全新的作品,不论叙述角度,语言个性,甚至主题立意,都与他过去的小说全然不同,由于大量使用了夸张、变形、魔幻等手法,作品由平面变得更为立体,语言由简洁变得更为多彩,寓意由深刻变得更为丰富,标志着范玮的写作真正由“知性”走向了“智性”。熟悉范玮前期作品风格的读者可能会觉得难以适应,甚至会觉得他丢掉了那些如影随形的传统技艺未免可惜,但范玮自有他自己的追求和野心,所以这种脱胎换骨似的转变在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孟村的比赛》可看作他转身以后的代表作,小说的语言诙谐生动,叙事新颖独到,既有第一人称表层叙事,又有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通过视角的转换弥合,穿梭于往事和现实之间,分蘖衍生出出人意料的丰富品质。养猪故事——两男一女的爱情故事——尊严与救赎的故事——更是一个人自我博弈的故事,在虚虚实实中显得意味深长。孟村的养猪比赛其实是窥察心灵隐秘的考场,执着与痴迷,作弊与逃避,理智与情感,尊严和救赎,都通过梦一般的村庄,梦一般的人物和梦一般的故事得以充分体现。《乡村催眠师》更是给人一种全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与前者比起来,这篇作品将故事情节做了更大程度的稀释,但却最大化地注重了细节的分量,加之叙述语言的“狂欢”性质,使这篇小说不同于那种佶屈聱牙的所谓“现代派”作品,让读者充分享受到阅读的快感,显示出范玮对小说技法把握的缜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先锋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现在我们不还能断定范玮的这种探索能走多远,因为在整个中国文坛,先锋实验文学其实已呈秋风落叶之势,在市场经济大潮无情的冲击下,主流文化向世俗社会做出了缴械投降的姿态,真正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已属凤毛麟角,在这种大环境下,范玮要想把这条道走通,非有顽强不屈的毅力、挑战权威的勇气和敢打硬仗的素养和心态不可。
应该说,张立勇很早就开始了对现代小说的写作实践,如果他能顺利地写下来,会是那波“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员。在这种探索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猎》,不是他的《琉璃井》,甚至不是他发于海外华文刊物上的《客来客往》,而是他那篇还没引起多少人注意的《情之蹂躏》。在这篇构思巧妙的小说中,一对生活不那么如意的夫妇在看电视,而电视上演的也是一对不如意的夫妇的故事。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彼此关联,互相弥补。在这样一个富于“新小说”特点的构思里,张立勇填充进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一对夫妻因为日子清贫、地位卑微和性爱障碍而不如意,另一对却是由于生活富有、思想空虚和感情疏离而不和谐。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对互相对比、互相映衬、互相补充的夫妻涵概了现实社会中几乎所有层面上的痛苦和烦恼。由此,张立勇也就不很吃力地写出了生活里那份无处不在并让人难以承受的沉重和困惑。小说给读者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电视里的男女在表演,生活中的男女在看电视,我们(读者)在看小说,也就是说,作者其实不止写了两个层面,他还暗含了第三个层面,也即我们作为读者的这个层面,作品的意义也就不觉间朝一个更宽泛的范围里漫溢出来,使它的外延显得无限大。张立勇的几乎每篇小说都有出人意料的构思,写起来(同时读起来)却又如行云流水,有一种驾轻就熟的轻松感觉。这篇《乡村教师的爱情》也有这样的特点。张立勇早就练就了先锋小说的技巧和功力,只待某个爆发期的尽快到来了。我们满心期待。
现在说一说王涛的创作情况。王涛当然就是我自己,由自己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那么合适,但鉴于“鲁西小说”这个范畴,我身为其中的一员,也只好不揣冒昧,来进行一下自我反省和自我写照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向他人坦白自己的机会,获得了批评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和提高。据我所知,王涛一向致力于现代小说的写作和探索,这从他发表在《时代文学》杂志上的《枣树行》、《野草莓》、《温柔之乡》等篇什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王涛还是有点自己的小追求,当然也是囫囵吞枣地“借鉴”现代派艺术技巧的一些尝试,曾经把诸如荒诞、变形、抽象、魔幻、象征等等手法往作品里塞,目的就是尽力把作品写得不像现实中的那个样子,制造一点陌生化的效果,作品也果然有了些怪异、神秘的模样(参见谭好哲:《神秘出意味——王涛小说艺术谈片》)。这样的作品让一般读者觉得别扭,自然也就难以接受了。另外,王涛还对“地域”这个概念有错误的理解,执意把自己笔下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安置在一个叫“乌龙镇”的地方(参见谭好哲:《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而这个地方在鲁西平原上又绝对找不到,其实人家福克纳早就说过了,他的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就真实地写在美国南方的版图上,王涛即使模仿一下都力不从心,所以能把小说写成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在当年《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还选载过他一两篇小说,对他也是一个不错的安慰了。好了,关于王涛,就说这么多吧。
以上对鲁西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做了一些简要分析,从中我们看出,鲁西这片浸淫着齐鲁赵晋文化遗风的边地,这个诞生过名作和大师的地方,还是顺应了现代文明的大潮,很好地滋养了一批属于自己的创作者,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如乌以强、武俊岭、老土等,都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写到。总之,尽管鲁西这些创作者还有待成熟,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气象已经让人倍感欣喜了,只要他们足够努力,并得到山东乃至全国文坛的重视和支持,这种暗流涌动的局面就一定会变成波澜壮阔的巍巍大观。让我们做好准备,拭目以待吧。
最后说明一下,鲁西小说界所包含的这些创作者,所追求的风格不尽相同,但为了写作的方便,我勉强把他们分成两大块,自然便显得捉襟见肘,暴露出这种简单归纳的莽撞和荒谬,加之读到的作品有限,实在难逃以偏概全甚至张冠李戴的嫌疑,希望被误评了的同行们不要太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