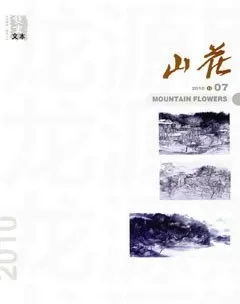“五四”爱情诗刍议
一 冲国爱情诗的古典形态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从远古的《诗经》开始,爱情就一直是文学最重要的题材和主题之一,爱情不仅是民间歌谣反复吟唱的内容,而且,在文人笔下,也花样日新,层出不穷,产生了求偶诗、思妇诗、香奁诗、弃妇诗等,关于爱情的想象和书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并且,和中国的文化、心理、历史、礼仪诸方面相适应,中国古代的爱情诗逐渐形成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传统,主张发乎情,止乎礼。这种主张和儒家中庸的道德理想与中和的审美理想相一致,成为中国古代爱情类文学作品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汉儒把《关雎》解释成“后妃之德”,虽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也止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正体现了“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诉求。虽然这样的解诗法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却表达了汉儒对爱情诗的期望和规范。
但是,爱情毕竟是男女之间一种十分强烈的情感,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够选择平和中庸的诗歌情感和形式相匹配,所以礼教并不能完全规范和限制爱情诗的发展。自居易的《长恨歌》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呼声,李清照在《一剪梅》中也感慨“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而元好问则有“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喟叹。在诗歌以外的文学样式中,《西厢记》、《桃花扇》、《红楼梦》等也都以歌咏爱情著称。但这些作品却无一例外地因为越过了封建爱情的樊篱而一度成为“禁书”。
由此,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两类反礼教的爱情文学作品:一是在儒家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在统治阶级无力控制人们思想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直抒胸臆的爱情作品。例如,汉末出现的抒情诗,晚唐出现的艳词,晚明出现的文学思潮,等等。而另一类则是民间歌谣,汉代乐府民歌、南北朝乐府民歌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在文人诗的领域之外开拓出爱情诗的另一片天空。但就所谓的文学“正统”而言,对于前者,封建卫道士常常持批判的态度,而后者,则定义在主流文学之外,成为下里巴人似的通俗作品,从而被驱逐出主流文学的领土。
为了与封建“正统”思想相适应,描摹爱情的作品须以婚姻作为基础,这才是台乎礼教的爱情。汉代《陌上桑》中罗敷就用“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婚姻来反对使君野合式的爱情,虽然说《陌上桑》是一首讽刺诗,但在这首诗里我们依稀可见婚姻的约束力。唐代张籍诗中的“节妇”之所以“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节妇吟》),正是用婚姻来拒绝爱情的绝妙例子。在婚姻这一外壳之下,很多诗人都写下了优秀的爱情诗篇,这些诗篇表达了爱情生活的各种体验:或男女相恋,或夫妇相随,或妇女见弃,或行旅相思……但是,在中国古代,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爱情和婚姻常常是分离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婚姻生活中,不是先有爱情,而是先有婚姻。在这种模式之下,现代爱情可能就仅仅是一种愿望和奢侈品。
二、‘五四'’爱情诗的思想资源
朱自清在评价中国古代爱情诗时曾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没有。”。这指出了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写作实际。在中国古代,男女双方在婚前往往没有自由交往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恋爱,相互欣赏,互相倾诉爱意或者赞美爱情便无从谈起,诗歌也就无从写起。朱光潜经过对中西诗歌的比较,认为“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这正说明了中西爱情诗歌的基本差别,朱自清显然是根据“五四”时期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爱情观念来评价中国古代爱情诗,从而得出“中国缺少情诗”的结论的。
我们知道,“五四”新诗运动的现代性,一方面是“诗体大解放”,另一方面则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核心就是个性解放,是人性的解放,这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思潮“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成为滋生爱情和爱情诗的丰饶土壤,成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反对封建礼教的利器,借用西方的现代爱情观念来反对封建婚姻成为当时普遍的现象,这在诗歌中也有明显的例子。
西方现代爱情观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只有有了爱情这个基础,婚姻才会幸福和甜蜜。所以黄婉在《自觉的女子》中才大声地质疑:“我没见过他,/怎么能爱他?”这种声音在中国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诗人胡适虽然缺乏诗情,但是他根据Sara Teasdale的~Overthe Roofs》翻译的《关不住了!》却诗情洋溢,这首诗被他称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首描摹爱情的诗章突破了传统爱情诗“中和之美”的樊篱,表现出飞扬的激情和想象,不仅是“诗体大解放”的典范,而且还有“思想解放”的魅力。
“五四”时期对爱情诗的更大突破还在于,在诗人的爱情诗中不乏对女性美的大胆欣赏和对爱的欢愉的直接描绘,他们既歌唱“情”,又赞美“欲”,突破“男女之大防”,将“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抛诸脑后。郭沫若在《venus》中写道,“我把你这张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为甘露!”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湖畔诗社的少年诗人汪静之在《西湖杂诗·十一》中则写道,“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悔煞不该出家呵!”诗人们之所以敢挑战爱情诗的传统,显然和“五四”的思想启蒙有关,正是由于西方现代爱情观念的引入,由于封建枷锁被打破,人性得到了解放,爱情得到了正名,所以诗人“才敢‘坦率的告白恋爱’,才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出情诗,才敢毫无顾忌、理直气壮地写情诗。”现代爱情观念的引入,不仅扩大了中国爱情诗的表现领域,而且进行了人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表现出“五四”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
三、“五四”爱情诗的文学评价
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部个人作品集《尝试集》收录诗歌八十余首,其中有十多首是爱情诗,不可谓不多。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认为“这时期的新诗做到‘告白’的第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情趣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在此不妨将这首诗引用一番,“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但他总劝我莫再想他。/他常常怪我:/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你要是当真爱我,/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朱自清对这首诗的艺术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但是,从纯粹的诗歌的角度看,这首诗充其量只是分行的散文而已,温文尔雅的胡适在他的《尝试集》中写不出爱情生活中那种执著的追求,热烈的相思,勇敢的抗争,读者读到的只有对爱情的哲学探究和理性思考,可以说,胡适的这些诗不过是“五四”时代爱情观念的传声筒。
除此之外,郭沫若的《venus》、黄婉的《自觉的女子》、鲁迅的《爱--之神》、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俞平伯的《怨你》和《占有》、刘大白的《邮吻》、康白情的《窗外》和《疑问》等爱情诗虽然成就不一,风格各异,但或因图解爱情,或因数量有限,在“五四”时期影响并不大。直到“专心致志”写情诗的湖畔诗社的年轻诗人出现,爱情诗写作才出现了根本的改变。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多描写对自由恋爱的向往与追求,敢于向传统的道德礼教开战。汪静之在《贞节坊》中就宣告,“贞女坊,节女坊,烈女坊——/石牌坊上全是泪斑 /含泪地站着,诉苦诉怨:/她们受了礼教的欺骗。”同时,湖畔诗人也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求和陶醉,表达爱情中男女细腻的内心世界。汪静之在《不能从命》中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此诗一反男尊女卑的传统,尊重女性,提倡爱情男女平等,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应修人则模拟女性的口吻在《花蕾》中写道,“你这样儿爱惜我,/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啊,/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这首以花喻人的诗,从男女青年的本能出发,喊出了女VRYywO2ClQRObQHfQzY9EdOlD0uuUKXxBGX18B2to+A=性也渴望爱情的呼声。
“五四”时期,湖畔诗社最早的几位诗人除应修人外,都还是杭州一中的学生,与他们的年龄、经历相一致的是,他们的爱情诗也表现出天真质朴的特色。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湖畔诗人涉世未深,未曾经历风雨的磨炼和捶打,所以他们表达出了爱情的热烈,却没有感受到爱情的缠绵;他们善于直率地表达爱意,却不善于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所以,后来新月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林徽因等人的爱情诗克服了湖畔诗人的“稚嫩”,将爱情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结语
康白情1929年在《草儿在前·四版重读后记》中说:“七八年前,社会上男女风俗,大与今日不同。著者虽也曾为主倡男女道德解放的先驱,而鉴于旧人物的摈斥,尤其是新青年的猜忌,竞不敢公开发表。”从这里可以看见“五四”爱情诗的处境,也可以看见“五四”爱情诗的贡献。但“五四”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挽救危亡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无论是梁启超1902年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还是鲁迅的小说写作,以及“五四”时期广泛兴起的“问题小说”潮流,都是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五四”诗人大多有爱情诗问世,但像湖畔诗人那样致力于情诗创作的,还绝无仅有。
1979年,汪静之在《回忆湖畔诗社》中还认为湖畔诗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革命诗,而爱情诗比较多。”所以五卅运动后,湖畔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应修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汪静之1926年放下教鞭“投奔革命”;潘漠华1926年南下武汉参加北伐军先遣部队;冯雪峰则于1927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能用宽容的眼光看待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创作。比如朱自清就认为,“文人的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的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一个重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的核心;赞叹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他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因此,在评价“五四”爱情诗的时候,既要考虑它进步的思想意义,又不能脱离历史语境,随意抬高或贬低它的文学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