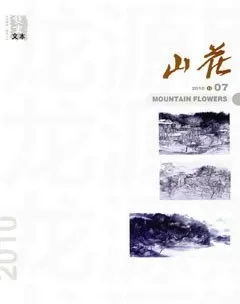论济慈的生命意识与诗歌创作
叔本华曾说:“生存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时间不停地在压榨着我们,使我们喘息不过来,并且紧逼在我们身后,犹如持鞭的工头。俏若在什么时候,时间会放下它持鞭的巨手,那只有当我们从令人心烦的苦悲中完全解脱出来。”这段话用来阐释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短暂的一生或许再恰当不过了。济慈生于1795年,亡于1821年。他6岁时弟弟爱德华夭折,9岁丧父,14岁丧母,22岁失去弟弟托姆。父母去世时不到40岁,弟弟托姆去世时不到20岁。母亲和托姆均死于肺结核病,这是济慈的家传疾病,济慈本人15岁时就开始受到它的侵扰。因而他深感生命的脆弱与人生的短暂,他说:“静静想想吧!生命不过是瞬息:/是从树顶落下的渺小的露滴/所走的险境:是印度人的睡眠,/正当他的船冲向凶险的悬崖,在芒莫伦西。”(《睡眠与诗》,由此出发,济慈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对于生存与死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思考。
一、淡忘苦难,享受生命
19世纪的英国社会矛盾复杂尖锐,人们生活在困苦与不安之中。济慈曾称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是“极可恨的土地”和“骇人听闻的国家”。(《给芳妮》)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马厩主家庭,在短短的一生中,他遭受了太多的人生磨难:亲人或死亡或离散、经济拮据、居无定所,无耻文人的恶毒攻讦、爱情的痛苦、疾病的折磨,等等。他说:“人生下来就是一种‘受罪的可怜虫’,注定要像森林中野兽那样遭受痛苦和不幸,像他们那样担惊受怕。”。但是,济慈总是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对于坎坷的人生持一种甘之如饴的态度。他曾这样劝告人们:“将你的哀愁滋养于早晨的玫瑰,/波光粼粼的海面虹霓,/或者是花团锦簇的牡丹丛;/倘若你的恋人对你怨怼,/切莫争辩,只须将她的柔手执起,/深深地,深深地啜饮她美眸的清纯。”(《忧郁颂》)在济慈看来,人生越是短暂,生活越是残酷,我们越应该享受生命,他说:“给我妇人、醇酒和鼻烟,/直到我嚷道:‘够了,住手!’/你们也如此照做不误……。”他想“要依次游遍整个欧洲,看看世界上许多王国,领略其富裕堂皇”。他渴望灵肉合一的爱情,醉心于美人的“甜嗓与蜜唇,纤手与酥胸”;“明亮的眸子,完美的体态,柔顺的腰”。(《白天逝去了》)幻想能“枕卧在美丽的爱人的酥胸”,“听着她轻柔的呼吸”而酣然入眠。(《灿亮的星》)他喜欢美酒佳肴:“唉,要是有一口酒!那冷藏/在地下多年的清醇饮料,/一尝就令人想起绿色之邦,/想起花神,恋歌,阳光和舞蹈!”(《夜莺颂》)叶芝在《自我上帝》一诗中这样写道:“没有人能否认济慈对世界的爱,/记住他那悠然自得的幸福,/他的艺术是快乐的,但谁知道他的内心?/想到他时,我便看见一个学童,/他把脸和鼻子贴在糖果店的窗橱。”
作为诗人,济慈总是要让自己的眼光穿透现实的黑幕,聚焦到美好的事物上。在他看来:“一件美好事物永远是一种欢乐:/它的美妙与日俱增;/它绝不会化为乌有;而是会使我们永远有/一座幽静的花亭,一个充满美梦,/健康和匀静的呼吸的睡眠。”(《恩狄芒·一件美好事物永远是一种欢乐》)为此,济慈提出:“诗之惊人之处在于一种美妙的充溢,而不在于稀奇少有”。所以,他要将自己诗歌创作的起点确定在“花神的国度”。在那里,一望无垠的草坪上趴着安静的小鹿,点点野花悄然绽放,鸟儿在花丛上方飞来飞去,时儿落下与小花嬉戏。(《睡眠与诗》)由于生活给予济慈的美好与欢乐实在太少,因而他不得不从希腊文化传统里,从想象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与素材,所以他所建构的艺术时空往往既充满了阳光、清露、鲜花、硕果等,给人以唯美的享受,又呈现出古典韵味和想象之美。s,A,布鲁克曾这样评价济慈的诗歌创作:“除了作品中的几小段之外,并且直到他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济慈对现实,对整个人类,对有关人类思想的政治运动,对人类的未来,对自由、平等、博爱,都没有多少兴趣。他只关心美。
二、超越自身,咏唱生命
由于家传的肺结核病,济慈在15岁那年曾吐过血,那时他就有了死亡的预感。此后,在本应风华正茂的岁月,济慈的身体却…天比一天衰弱,死神总在身后像影子一样追随。在离去世还有3年的时候,学医出身的济慈就已经在屈指计算自己的死期了。可见,疾病与死亡一直是济慈心头无法驱散的重压。他说:“我的心灵是脆弱的:无常/重压着我,像不情愿的梦/每件神工的玄想的极峰/都在告诉我,我必将死亡,/像仰望天空的一只病鹰。”(《初见爱尔金石壁有感》)为此,他厌弃一切没有生气与活力的对象。他兴致勃勃地去参观彭斯墓地,但是却感觉很不好:“城镇、墓园、落日、云彩、树木、圆丘、看上去虽然美丽,但冰凉——奇异……。”(《拜谒彭斯墓地》)因为他看不到生命的迹象,同时也想起了自己不远的死亡。他曾宣称:“哦,孤独!假若我和你必须/同住,可别在这层叠的一片/灰色建筑里……”(《哦,孤独》)灰色的建筑死气沉沉,无形中对生命构成了压力,他迫不及待地要从中逃出来,去寻找和呼吸生命的气息。
但是济慈很少顾影自怜,也很少怨天尤人。由于比一般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他往往超越了自身的存在,用优雅的旋律去咏唱生命的颂歌。他歌唱小鸟、蜜蜂、鲜花、青草等大干世界里欣欣向荣的生命,就连小溪、星星、大海这些没有生命的对象,到了他的笔下也都充满了生机。尽管任何一个生命的存在都体现为个过程,都与人一样存在生老病死,但是从济慈的笔端所流露出的景象却往往是:麋鹿在林间跳纵,巨鹰在蓝天翱翔,鲜花在草坡上开放,仙女在海浪中歌唱,处女春心荡漾等,所有的对象都活力四射,生命之花开得极为艳丽。秋天是万物萧索的季节,但是,济慈所描绘的秋天却是以金色的阳光、红色的苹果、绿色的树叶、紫色的藤蔓以及五颜六色的花朵所织就的绚丽图画,是由小蜜蜂嗡嗡的声音、榛子炸开的声音等混合而成的生命乐章,充满了成熟的韵味。(《秋颂》)济慈偶尔也写到生命的凋谢与死亡,这时,他就显得无比的哀婉与忧伤。从总体上看,济慈很少冷静地站在各种生命形式的对面,而是要调动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等自身全部的感觉,去拥抱对象,感受对象,和对象实现生命的碰撞与交流,因而,他的诗作中总是蕴涵着丰富的感觉信息。在《幻想》一诗中,既有雏菊、紫堇、野百合、偷窥的田鼠和蜕皮的蛇等视觉信息,也有收割者的歌谣声、云雀的婉转声、谷穗的沙沙声等听觉信息,还有美酒的浓香、鲜花的芬芳以及雨后清新的空气等嗅觉信息。在接受这些信息时,读者往往如临其境,留连忘返。为此,乔治·桑塔耶纳曾将济慈誉为“最耽于声色的英国诗人”。在和大千世界各种生命形式拥抱交流的过程中,济慈真切地感受到了宇宙间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美和力量,显得更为乐观与坚毅。在他眼里,蛔蝈与蛐蛐交替歌唱,“大地的诗啊永远也不会停歇”(《蝈蝈与蛐蛐》)。他真诚地劝告人们:“不要悲哀吧!哦,不要悲哀!/到明年花儿还会盛开。/不要落泪吧!哦,不要落泪!花苞正在根的深心里睡。”(《仙灵之歌》)
三、憧憬死亡,定格生命
由于长期处于向死而生的状态,济慈对于死亡不仅失去了应有的恐怖感,反而觉得有些亲切。在社会的黑暗、生活的重负、情感的折磨、疾病的纠缠等一座座大山的压迫下,济慈有时连喘口气都觉得有些困难。在某种意义上,死亡对于他确实是一种最好的休息与解脱。所以,年轻的济慈经常憧憬死亡。他说:“倘若我能在这个午夜里停止呼吸,/看见尘世里华而不实的旖旎灰飞烟灭。/诗歌、浮名与美人固然香浓味劲,/但死更浓更劲——死是生的最高补偿。”(《今夜我为何发笑》)他还说:“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而现在,哦,死更是多么富丽:/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夜莺颂》)不过死亡的诱惑虽然强烈,但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无法试验也无法重复,无从逃避也毋须强请求。于是,济慈便迷恋上了死亡的两个姐妹:一是睡眠,二是类似于吸毒后的迷幻状态。在济慈看来,好的睡眠所带来的休憩、宁静、平和与温馨是任何享受都难以比拟的。他说:“哦,静谧午夜中温馨的抚慰者,/请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合上/我们喜爱幽昧的眼睛,挡住光线,/让我们融入神圣的遗忘——/甜蜜至极的睡眠啊,如果你愿意,/就在唱赞美诗中让我进入梦乡……”(《致睡眠》)而济慈所向往的迷幻状态则接近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使其在瞬间体验到生命的极致。他说:“我的心在痛,团顿和麻木/刺进了感官,有如饮过毒鸠,/又像是刚刚把鸦片吞服,/一会儿,我就沉入了忘川河水。”(《夜莺颂》)
在憧憬死亡,沉湎于睡眠与梦幻的同时,济慈又总是担心梦醒美去,担心死亡将一切都化为虚无,执著地要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他曾醉心于一只精制的希腊古瓮。瓮面上是一圈装饰性雕刻,栩栩如生,有葱茏的绿树、欢快的乐曲、年轻的恋人和喧嚣的祭祀仪式等。虽然画面所展示的生活片段早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但是由于它们借助了“瓮”这一特定的载体,作为美的瞬间定格了下来,从而能与岁月共存。(《希腊古瓮颂》)布鲁克斯认为它所蕴涵意义在于:“快乐的凝聚时刻要比流动的现实世界更有生气,只因为是凝聚的。”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济慈特别执着地要抓住十分有限的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使他人生中一些美的瞬间凝聚下来。济慈所选择的道路是诗歌创作,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可以保证他衣食无忧的药剂师职业。他从事诗歌创作总有着非同一般的急迫感,总担心他的生命也许等不及他的笔搜集完他蓬勃的思潮。(《每当我害怕》)只要几天没有写出满意的诗句来,就变得焦躁不安,一味地责备自己懒散和无所用心。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他不愿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上天能他多活一段时间,使他能够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以确保他在诗歌史上不朽的地位。
海德格尔曾说:“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双眼。诗人不是行动,而是作梦。”如上所述,济慈一生虽然充满了痛苦与磨难,但是他栖居在这个世上的方式却充满了诗意;他的生命虽然尚未开花就已经开始凋谢,然而他的梦却永远年轻。约翰·济慈对生命与死亡的体验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同时也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科技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济慈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xKYT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