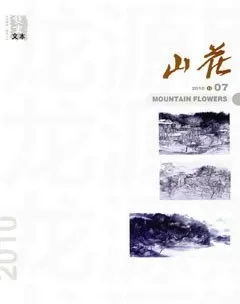外祖母究竟怎么了?
1.引言
17世纪英国文坛曾经出现一种新的文学题材——性格特写(character-writing),也被称作“散文人物”(essay charater),大多出自当时的英国散文家之手,常见于短小精悍、笔力雄健的散文之中,旨在刻画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性格。特写中的人物性格单一,缺少变化,且形象不够丰满,犹如一幅独立的肖像画(杨理达,2006:64)。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变化,这一文学题材也在不断地演变和补充。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还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散文家,如托马斯·卡利尔(1795--1881)、约翰·拉斯金(1819--1900)以及托马斯·亨利·哈克斯雷(1825--1895)等。他们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一道揭露抨击社会阴暗面,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及各种主题的演讲稿,将英国的散文与文学评论发展到一个新高点,“散文人物”也以更加成熟的形象在一些大作品中出现,如狄更斯的《波兹特写》(Sketches by Boz,1836)、萨克雷的《势力者》(Books of Snops,1848)和艾略特的《泰奥弗拉托斯之类的印象》(Impressions of Theophrastus Such,1879),尽管他们的创作角度与风格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共同关注的是广大百姓的生活与命运,像小说一样,他们在作品中同样表达了对不人道的社会机构、堕落的社会道德及大面积的贫困与不公的愤慨之情。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对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唤醒了公众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的意识。
与他们同处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Jefferies,1848--1887)是英国著名作家、散文家和博物学家,以擅长描写乡村生活景色而闻名英国文坛,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描写自然和乡村生活的重要作家。在其自传《我心灵的故事》中,他描述了他要与“实实在在的宇宙”和谐共处的渴望以及“大地之声在我身心中穿越”的感受。足可见理查德·杰弗里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渴望。理查德·杰弗里斯是农家子弟,从小喜爱山水,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为他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着真实的感情,文字大多不落义理,不夹议论,有出尘之致。题材多为自然风物、乡村生活,观察敏锐,笔墨浓而不艳,细腻入微,可与哈代小说里的乡村氛围相媲美”。(虞建华,1995:200)
《捡橡果的孩子》(The Acorn-Gatherer)是理查德·杰弗里斯的散文名篇,讲述的是一个生父是酒鬼,生母活活饿死,孤苦伶仃与老外婆相依为命的非婚子靠捡橡果卖钱度日的故事,贫困的生活和悲惨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文章中那灿烂的阳光、清脆的鸟叫、潺潺的小溪和旷丽的原野使人似乎嗅到了清香的大自然泥土的气息,然而读完全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使读者心灵有所震撼的却更多的是那个没有名字,“眉头紧锁——展不开的皱纹像橡树皮上的裂缝”,经常与乌鸦嬉闹,以爬树摘橡果为乐,不断挨打,最后又溺水并被大家遗弃的十来岁男孩,和那位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大声祈祷、衣着整洁的外祖母的形象。他们在瑰丽的大自然中过的却是艰难困苦、受尽折磨的残酷的乡村生活。该篇散文中的人物也像优秀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其内心世界令读者生疑和好奇:清新干练的肖像描写之下,其内心又是怎样的复杂与矛盾?
2.外祖母生活的压抑与释怀
《捡橡果的孩子》这一散文中“外祖母”的外表和性格描写可谓惟妙惟肖,同时,对人物一举一动的刻画又透出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尽管“外祖母”是散文中的人物,依然有人物素描的痕迹,但对外祖母生动、逼真的描写使其更加接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散文中所渗透的外祖母的内心世界颇具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异化感(alienation)、焦虑感(anxiety)和绝望感(dQspair)(李维屏,1997:54),
2.1夹在责任之中
故事中的男孩是非婚子,这使外祖母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以没有教养好自己的女儿,没有尽好母亲的责任而背上精神压力。孩子的父亲是个酒鬼,无所事事,不能养家糊口,结果“姑娘饿死了,据说是活活饿死的”。因此,为了不再继续受到责任和精神的进一步折磨,无奈之下,老太太替女儿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责任,否则他不仅会饿死,而且自己还要背上另一个社会和道德的“罪名”——不照顾年幼的外孙。“他的衣服不比麻布片好多少,但缝补洗刷得干净整洁。谁都会说:‘家境不好,但照料还挺仔细。’”从对男孩的衣着打扮描写可以看出,外祖母对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的照顾也算是尽力了。而散文中对外祖母的外表描写是这样的:“一位腰背挺直的老妇人正走过缺口,肩上扛着柴捆,手提一根结实的烧火棍。她一身整洁,拿劳动妇女来说也算得上穿着体面。”说明外祖母在生活中是个勤劳而又有个人尊严的人。但是夹在对女儿和外孙这两个社会有非议的人之中,她还是试图用外表的干净整洁来掩盖内心的焦虑、自责与不安,来洗刷自己“没有教育好女儿”的罪名。这在随后对她的描述中可以得以验证,“她面色严峻,带着比大多数她那一类人优越而又难以说清的气质。”一个“难以说清的气质”勾勒出散文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这种独特的刻画人物的方式为读者的自由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突出外祖母心中的愤懑和积压已久的不安。
2.2排斥与被排斥
女儿非婚生子,这有悖于宗教伦理的行为等于向全村村民的宗教信仰发起了挑战,也必将遭到全村村民的反对、唾弃和排斥。而女儿死后,与其有血缘联系的男孩自然也是不符合宗教道义的野孩子,将外祖母推向了被排斥的行列。外祖母要找回自己的尊严,竭力维护自己在村中体面存在的地位。无疑在心中,一方面排斥着这个男孩,认为他是“世界上没有再坏的孩子了:这个坏蛋已不可救药”,另一方面,自己参加宗教小团体,通过自己对宗教的狂热追求来为找回自己的心灵,为自己赎罪。这个宗教小团体在原文中用的是“seet”(异教)一词,而且祈祷的地方是在自家农舍而非教堂,这些足以说明她受到主流宗教的排斥。因此,“在她的农舍里,一周举行两次祷告会,她在他们中间大声作祈祷,”她的“大声祈祷”显然有着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之嫌;另外,从对外祖母的描摹刻画中也可见一斑,“宗教信仰使她凌驾于他人之上。我敢肯定她的信仰绝对名副其实。她甚至愿意带着那张严厉的面孔,穿着这身布衣衫舍身殉教”。竭力反衬出她想得到集体认可和社会承认的心理,想回到“正常人”的行列中去,同时也是心理被扭曲的再现。正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因大年祭祀活动不让她参加,就虔诚地到庙里捐一个门槛“赎罪”,以此寻求心理的安慰。
2.3迫害与被迫害
受到宗教的排斥,社会的非议,村民的闲言碎语使外祖母和男孩处在憎恨一切却又相互被憎恨的旋涡里。为了寻求自身的存在和自尊,他们当然会反抗。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以淘气的行为进行反抗的结果就是将外祖母和自己带入迫害与被迫害的恶性循环中。
外祖母认为,榜样、规劝和棍棒都改变不了这个男孩的心。外祖母在道义上的管教和内心的愤恨使得她“久而久之,她不再因为一时的某种怒气,而出于习惯要揍他一顿,就像汲水灌壶一样,已成为家常事了”。恶性循环中,外祖母对他的管教毫无用处,认为他像以前一样难以教化,因此对孩子开始进行迫害,关在小屋里一天不给吃饭,作为他违反教义和训教不改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在精神上更是难以想象地施加压力,甚至是一种对幼童的摧残。星期天,按《圣经》的要求,基督徒要到教堂守安息日,而小男孩却是另一番情景:“每星期天,经过这里去教堂的人都可以从窗前看到孩子坐在外婆那本打开的(圣经)前。他必须在那儿坐着,门锁着,在棍子的威胁下,学习那页经文。”老太太说:“他是不识字,但我也要叫他看着这本书。”迫害孩子给上教堂的村民看,实际上是向村民宣誓和表白,证明自己是正统和刚正不阿地信守道义之人,其实这正是自己受到社会和宗教压迫的反抗形式,只是这一反抗是通过压迫孩子而体现的。被追害中的孩子,失去了自尊,失去了生存权,最后在并不深的河水里因钓鱼线缠绕胳膊而溺水身亡。从家失踪后外祖母没有寻找,过路的村民看到了也没有打捞,漠视地离开。小男孩死的价值在后来的体现就是:像一个稻草人一样挂在那里成为违反社会宗教道义的反面形象给后人以警示。外祖母焦虑、绝望的内心从此平静了,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以此来作为精神上的解脱,同时更安慰自己的心灵。这种释怀方式是内心自私的表白,是社会环境造就的结果,是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异化感”的伪装,是想得到社会承认、想受人尊重的需要。
3.结束语
《捡橡果的孩子》寄托了作者对穷人家孩子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一个孩子的苦难却是无数农村儿童的生活缩影。散文中的外祖母是一个古板、教条、盲目的农村老妇人,在宗教、社会道义和村民的窃窃私语中忍受着指责、非议,并遭到排斥,更因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而失去了对社会和周围环境的判断力,在舆论和古老道德的约束下失却了应有的情感。在压力下变得冷酷,在内心的矛盾和不安中变得泠峻和偏执,从而以迫害孩子来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以求找回自己的尊严,而不是竭力抚慰孩子受伤酌心灵使其有正常的生活,或是正视问题的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在孩子几天不归的紧要关头,外祖母选择的是与广大村民站在一起,对孩子是永远的放弃,试图来抚平自己的伤痛,致使男孩彻底成为无辜的受害者而失去生命。文中的男孩不仅仅被他的外祖母所遗弃,更是被社会所遗弃,是邪恶势力作用的结果,是蒙受冤屈的象征。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外祖母试图用打压的方式使其回到“正常人”的范畴之中,其实是希望自己回归村民大众的“正常”眼神中。恪守古老教条的村民和外祖母成为了犹大,当然他们出卖的不是耶稣,而是同情心和良知。其实,无论是小男孩还是外祖母,他们都受尽了心灵的折磨,性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所不同的是一个失去了生存权,而另外一个却在挣扎着捍卫自己在社会这个集体中的个人尊严。
理查德·杰弗里斯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工业化进程推进的时期,当时生活在英国乡村社会下层的人们生活非常艰苦,道德和宗教也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冲击而被异化。外祖母和小男孩一样没有名字,因此,可以想象他们应该是乡村生活中的一类典型人物的代表,作者通过对“外祖母”这一散文人物的描写,倾注了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之心,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无情地批判了当时堕落的社会道德,以期唤醒公众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人物的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文中引用小说中的原文均来自虞建华教授对The Acorn一6a—therer(《捡橡果的孩子》)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