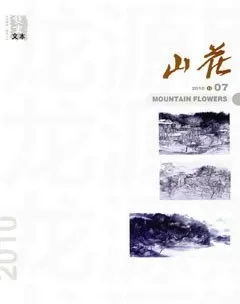熟香入木
白桦
站在裸露青色岩石的陡峭山坡,拨开纷披杂草(鞭蔴、冬青、西藏点地梅……),我扭头努力北望。我以为我会望见遥远北方寒凉辽阔的俄罗斯,望见猎人、野禽和林中木屋,以及滚烫茶炊。但是不能。努力探看的结果使我感觉自身如同爬虫卑微。我的眼前依旧是青藏高原宽广无际的蓝天和层叠绵延的幽微群山,莹白的雪依旧挂在七月峰顶,山谷的夏季风送来清凉和草药的芬芳。如同羽翼伸展的俄罗斯原野,在我的目光之外绚丽:矢车菊和铃兰刚刚开放,葱茏的黑麦田泛着涟漪,湖边灌丛里到处是红草莓和蘑菇,高大橡树和榛树黑黝黝的矗立,无比雄伟,它们宽广多结的树枝在高空有着清晰的轮廓,苍鹰和红隼飞翔不止,树底下红褐色的松鼠和雪兔机警敏锐。转个背,白桦林在俄罗斯九月的阳光下发出白丝绸般的柔和光泽,午后诡秘的牛毛细雨洒下来,整个白桦林潇潇不己……弥漫紫色云雾的草原和白桦林,它们长时间沉浸在黄昏的金色光晕和清晨的寒冷中,并长久茂盛在我的想象中。朦胧向往(那是我唯一可以明确感知的一个存在),以至让我淡淡的思绪整日笼罩在一层冬日阳光般的惆怅中,仿佛我曾经真的漫步在那一片白桦林中,抚摸过白桦树光滑细腻的树干,谛听过白桦树叶亲切的絮语,而今却远离,只留下缕缕挂念和牵绊。
翻遍家中零散的几本书,书页里无处不是俄罗斯白桦树散发的清芬(是不是当年的父亲也曾经迷恋文字中的俄罗斯,或者,俄罗斯的文字?):春天的早晨,寒鸦在白桦林里苏醒过来;夏天,白桦树的阴凉下是潮湿馨香的空气;冬天的白桦枝在厚雪的压迫下垂到地面,形成雕花的拱门;而秋天,那是白桦蜕变成蝶的骄傲时刻,金黄的白桦树叶如同浓墨重彩的油画。少年的清凉光阴在几页重复的阅读中踮着脚尖走去,它的灰色大氅扫着高原的林木和流水。夜晚,从密集排列的文字中抬起头,我看见高原黑蓝夜幕上缀着寓意隐秘的星座图案,仙女、牧马、射手……精致图案,闪烁不定的清辉,我如此逼近它们,仿佛它们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宇宙,而只是来自北方那片清朗的白桦林。
释然于这份迷恋,犹如我原谅自己拔下蚂蚱的一条后腿,看它在九月的山坡弹跳。清贫静寂的乡村生活,煤油灯,崎岖山路,漫长荒寒的冬天,日复一日的寂静,幽暗房屋,七月里蒙着冰雪的山峰,纠葛的荆棘,河谷流水潺潺,黄蜂嗡嗡,大人繁忙,少年寡淡。唯有俯下身去,找出仓库里那一本本发黄残破的旧书,吹去封面上呛人的灰尘以及蛛网,打开潮湿卷曲的一页,我才可以钻出空旷却又逼仄的童年时光,望见村外山花烂漫的丰饶。
没有更多可以阅读的书籍,我便穿越幽深茂密的森林,给守林的邻居老人送去他简单粗糙的饭食。林间遍布高大云杉,它们的枝叶交织出另一层天幕:墨绿、厚重、阴沉,它们是这森林的主人。但老人曾经告诉我,这森林最初的主人是那白桦。白桦生在山洼,先是猛长,成林,然后懈怠,放慢速度,耐荫的云杉乘机而入,持续生长,以至覆盖白桦,夺取阳光。这场缓慢的生长过程,如同千米长跑,如同,一些成功后面的潜规则。现在,我看见虬曲的白桦长在云杉的阴影里,挣不到一缕金色阳光,如同一些退居下来的老人,赢弱,隐忍时光。它的周边是纠结的灌木,金露梅、山玫瑰、沙棘,低矮杂乱。蜿蜒的林间小道野草茂盛,棕色的朽叶下面,探出瘦弱山花和壮硕的褐色蘑菇。鸟声沉闷,在林间寂静而又喧响。我听出来水分自叶脉、根系、土壤和爬虫纤细脚底的流动声音。
幽暗、逼仄、潮湿,漫溢树木清香的童年木屋,我如此熟悉那些树木发散的浓郁气息:云杉、白桦、刺柏、冬青、高山杜鹃。走进木屋,如同走进树木紧密细致的年轮深处。白色桦木搭建的木屋,它的内层墙壁已成烟火色,表面布满疤痕,生锈铁钉悬挂起简单生活用具;漆面斑驳的搪瓷缸,鞭蔴锅刷,褪掉色彩的破旧毛巾,粗黑牛毛绳,盛着青稞面的暗久布袋,桦树皮缝制的小筒内插着筷子和铁勺。搁起的木板上放着煤油灯盏,棉絮捻出的灯芯又粗又大,小罐菜子油,小罐粗盐,它们是唯一可以用来调剂生活的奢侈物,有着豁口的白色粗瓷大碗,它的釉面在杂乱阴暗的角落发出微光。从树根截成的矮凳上,我可以看见停滞的生命脉络。夜晚,老人用干燥起皱的白桦树皮引火,灶内火光将木屋映衬得昏黄温暖。毕剥声中煮茶。砖制黑毛茶和盐、溪水,将它们熬成黑红色,如同牛血。佐以白桦清冽的芳香、马匪、狼、旱獭和月熊的故事。山风袭来,松涛起伏,夜鸟啼叫,河水奔腾,木屋犹如悬挂树梢,摇摆不定。我瞅着窄窄一扇白桦木门板,仿佛看见门外蹲踞的黑色鬼怪,它流水一样的长发纷披下来,山脉成为它指缝里裸露的骨骼。老人握着茶缸,在灯影里转个身,此刻他的眼神无比慈爱:到了冬天,晚上在白桦树干上开个洞,第二天白桦汁会结成棒冰,拿了舔着吃,又香又甜。我于是在童年的想象中微笑。
刺柏
站在刺柏树下,我以为自己完全可以捏住一只麻雀的翅膀,只要一伸手,就如同一伸手就可以捏住红漆面柜上的鸡毛掸子一样,但是不能。于是我抬头探究,在繁密的刺柏枝叶间,但依旧看不见它们的身影,只听见它们近似挑衅的啁啾。我想它们是可以看见我的。我们处于如此不同的境地:幽暗与光亮,却怀揣如此不同的目的:它们在幽暗中光亮,而我在光亮中幽暗。
刺柏早已老去,树身矮小,总也高不过黄土夯筑的南墙头。针型细叶浓密葱郁,其间夹杂锐利小刺,红褐色树皮纵裂脱落,常有黏稠树脂流出,仿佛浑浊老泪,历经沧桑。树形优美,枝条箍成圆锥形,紧密有序,是极其严谨自律的一棵。刺柏树中四季都有麻雀来往。它们在每日日出前20~30分钟内就会集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演说活动,群情激奋,仿佛要拯救什么,但往往有始无终。大多时间,麻雀在树叶间欢快跳跃、嬉戏,站在树身外的我看不见它们任何一缕飘忽的身影;由此我感觉到刺柏的悲悯情怀,以及他隐约的偏袒,他敞开密不透风的衣衫,任它们在他肌肤骨骼内为所欲为。于是我有了些微茫的嫉妒(并不明晰的意识中,我将自己同小小的麻雀等同起来,争夺自然的庇护),天时于我并不公正。骤雨袭来,抑或冰雹乱砸,我在逃离的瞬间仍旧听得见麻雀们在树冠里清脆的说唱,仿佛刺柏枝间结满翠绿光滑的玻璃弹珠。
邻家姐姐说麻雀屎和些蜂蜜拌匀,擦脸,能防皴并使皮肤细腻白嫩。我容易相信这些善意的偏方。早间起来,到刺柏树下捡拾麻雀屎(以白里透灰者最佳,据说那是公雀屎)。那个时候我暂且忘却刺柏树身里隐匿的玻璃弹珠,只喜悦于刺柏树下厚厚一层雀屎泛着的灰白光芒。那是一缕承载希望的光芒,有着让灰姑娘成为公主的力量。
刺柏长在花园里,父亲常叮嘱我们,不可将洗脸水泼洒到刺柏身上,说刺柏树性子高,受不了人的浊气,会死去。一日我偶尔看见纸面上高冠博带的古人仰面长啸,便觉得刺柏树其实也是位朝饮兰露夕餐菊英的高士,他耳目洞明,心思铮亮,操守坚定,品质高洁,他从不现身,但我们的言语行为均在他的透视之中,我们唯有时刻严格自律他才可愉悦欢欣。我于是追加给自己一种隐性的力量,警醒自己:时刻,我都要,如同松柏。
阴历初一或者十五,父亲早早起来,到院里摘些枯萎的刺柏枝叶下来,揉碎,放进白色陶瓷大腕内,燃起烟来。碗不能随便放置,一定要在干净的高处,譬如有着墨绿苔藓的院墙顶上。烟是孤烟,细小的一缕,灰中带些幽蓝,烟升起来,仿佛巧舌,舔噬小小院落:土木结构的低矮房屋,雕花的松木窗框,有着烟熏味的板壁,藏着太岁的幽暗角屋,便是在阳光下也无比阴暗的厨房,种植刺玫和罂粟的花园……袅娜,如同鬼魅。我在浓郁的刺柏香气中醒来,睁开眼,清冽的早晨挂在纸糊的窗格上,我看不见天色与云影,也看不见房屋东边青杨树枝上的鹊窝,但是高原的天光云影全透过薄薄的纸面,亮晃晃的存在。翻个身,在麻雀啁啾的寂静中,我嗅着刺柏的浓香重又睡去,仿佛多年后孩子抱着她的毛绒玩具睡去。
除夕夜,父亲急于清洁房屋以及香熏我们。从河边捡来几块拳头大小的圆白石,埋在火堆里烧红,睡觉前(那总是到了黎明)将石头放进搪瓷盆里,上面撒些刺柏碎叶,浇些食醋。“噗嗤”一阵,烟和蒸汽喷吐出来,混杂着刺柏和醋的奇特香气。父亲端着盆子沿着墙角低低熏过每间屋子,熏过我们,熏过鸡圈猪窝牛马棚,然后投到屋外去,父亲说如此一熏,来年人畜便不会生病。爆竹声零星响起,我带着新年的气息睡去,心里疼爱并喜悦与那个熏过的自己,仿佛雨后草木,一身清洌。
一天,我翻阅图齐的《西藏宗教之旅》,记住如下一段文字:焚香,是藏区民间宗教中最为独特的一种仪轨活动,这其实是一种净化和赎罪行为,人们认为本处会使人身上产生一种特殊的软弱状态,是些污秽、斑点和阴影,人在这种状态下容易受外界入侵,人们于是通过向四处扩散的香烟,使自身及其周边事物得以洁净。同时藏区的人们还认为人类耕种土地就意味着一种打乱了事物原有状态的新秩序的出现,人们耕种或掀石必须得到人类公共文明生活的第一批创建者的帮助,因此人们要在掀石耕种前举行焚香活动,以求赎罪。
我想着父亲是有简单的宗教思想。以至于现在的我,也对熏香有着癖好。我时常地要在屋子里燃些刺柏的桑烟出来,让它们熏过各个房间,在此之前,我将屋子扫除干净,然而我总觉得屋子里是有霉气的,刺柏桑烟可以使屋子洁净。我在市场上遇见各类香,龙诞、百合、檀香、印度香,以及名目繁多的精油,点燃它们,仿佛撞上别人厚重滑腻的舌苔,感觉窒息。而我住在有着刺柏熏香的房子里,仿佛住在森林里,格外安心。
头花杜鹃
覆盖白雪的高山顶上(积雪厚密均匀,发散耀眼白光,山顶巍峨高耸),头花杜鹃如同栽毛地毯,平铺,宽展:革质小叶翠绿重叠,繁密不见孔隙,淡紫色花瓣盛开期间,花瓣素朴淡雅,有着柔滑的丝绸质地,抚过去泠然作响,仿佛月光凝结。花香新鲜、持久。手指始终不曾折一枝花朵下来(我怕看见花瓣里无辜的眼睛)。脚步穿梭其间,牵牵绊绊,不能大步流星……总是走不出繁花似锦的断续梦境。梦中内心,缠绕恐惧、担忧,如同缠绕渐次勒紧的藤蔓。原来便是梦中,也识得高山孤绝,四周布满深渊,并无坦途,而人一心想着的,是要平安走下山去,离开冰雪。午夜醒来的寂静中,常会发觉梦之荒诞:头花杜鹃原是不会在白雪中粲然绽放。只是梦中情形,极其逼真,仿佛头花杜鹃深植在大脑的褶皱处,丛丛茂盛,那一片一片花瓣盛开,遮去诸多细胞及其他东西的过程,缓慢清晰,仿佛脑壳在那瞬息间简化成肥沃土壤,只供花开。
资料说头花杜鹃只生长在甘青两地海拔2500~3600米的高山草原或灌丛中,是香精油植物和药用植物,目前只用于中药,作为香精油还尚未开发。看后让人存些期望。只是资料中的头花杜鹃如同失去体液的蝴蝶标本。而它在细碎黏稠的高原民间,有着烟火青草味的名字:香柴。
突兀耸立的青藏高原,它的山峰之上,冰雪长久覆盖,四季并不分明。南方已是溽热夏日的六七月间,山花(并非姹紫嫣红,总是简单的那几种)才可开放。高原的夏季风始终带着冰雪的清凉,以及草药的气息。夏季风沿着山脉走向吹拂,所到之处,枝叶花朵依旧静谧,并不喧嚣。我们常在这个季节到高山上去,跟随大人,砍柴或者放牧。砍的柴通常是些冬青、鞭麻和香柴。冬青有着柔韧的革质叶子,叶子宽大,花朵洁白,有着奇异清香。鞭麻会开出两种颜色的花朵,金色和银色(青海湖畔的金银滩由此得名),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鞭麻有着调节气温的功能,也不曾知道,塔尔寺绛红色的墙壁主要是由鞭麻砌成。冬青柔韧,不易砍断;鞭蔴矮小,需要连根拔下。香柴青绿色的细茎碰着镰刀便会咔嚓一声断去,仿佛娇嫩的脖颈。香柴长在灌丛里,植株不高不矮,光滑脆弱。有时香柴花满坡开放。大手笔。仿佛紫气缭绕的湖泊。将香柴背回家,摊放在空地上暴晒。厚重的高原阳光,金黄、燥烈。水灵灵的花朵在阳光下逐渐失去香气,干燥、枯萎,褪去颜色,仿佛一个玉人在尘埃中逐渐遁去身形。大把大把的香柴在灶内燃烧,噼啪作响,火焰热烈,香气弥漫。于烟熏火燎的厨间偶一回头,看见门外的细碎花朵,散落一地,仿佛小小的花之遗骸,极尽幽怨。
我总是要记起那个时刻。残灯如豆,母亲在昏黄的光晕中幽幽回忆,她的叙述如同屋外高寒夜空,跌落,继续跌落,没有斤数的沉重,说:“天不亮起身,要赶在日出前翻过山去。香柴从不在低处生长。”我如此熟悉那座海拔为4000米的山峰,青色山石陡峭光滑,不生长任何植被,上山下山只有一条窄小沟槽,是砍柴人用身体蹭出的唯一道路。煤油灯的光晕打在报纸裱糊的屋顶,在那里晕染出乌黑有着毛边的图案。屋里流淌着浓重的煤油气息,它们在母亲鼻孔描出黑圈。“在山顶,绑好香柴捆,我转过身,把绳子套到肩上,试图背起来,但是一鼓劲,眼前金星乱冒,于是靠着香柴坐下,停一会儿,再试,总是无法挣扎着站起来。”停顿,我看见沉重柴捆下一个瘦弱身影的挣扎,于饥饿。我甚至看见柴捆下痉挛的胃部纠结成黑色硬团,不断涨大,横亘天日。
“天黑的很慢,星星总是不出来。”……“下山时人和香柴捆一起贴着石头往下蹭,柴捆滚动起来有危险,不能放到人前面,也不能拉到人后面。”叙述停顿,我的身体被绳索吊起,吊起,所有的脏器沉重下垂。“一整天没吃东西,饿极了,只好将香柴花摘下来吃。”母亲接着说。
多年后的一个下午,我用花朵泡茶喝。在这之前,我曾经用玫瑰花瓣做馅饼。将新鲜的玫瑰花瓣晒干,用红糖拌匀,放进玻璃容器中腌上一段时间即可。出锅时掰开馅饼,玫瑰花瓣仿佛刚刚凋落,咬上去如同咬在带着清芬的肌体上,有着疼痛的叫嚷。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起母亲。在后来,当我将玫瑰花苞、茉莉、金银花和白菊一起放进玻璃杯,续上热水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想起母亲。那一刻,我只是被一些词语诱惑(那些精致、优雅,需要与这个时代以及女人有所关联的词语),那么慌张地需要摆脱过去的简单粗糙,如同想要摆脱我植物一样拙朴的年少记忆,如同,一条来自森林的根系,要摆脱山涧。
多年前的回忆在那个夜晚就那样戛然而止。灯火熄灭。漆黑。我记起那晚屋外星空,三星、启明,它们拴在一根根黝黑的细线上,悬垂。还有群山,它们围绕,如同黑色牛毛绳编织的栅栏。我感觉到夜间河水溅起的微小水滴,如同流星,坠落脸颊。我知道它们来自大地深处,我想着母亲也来自大地深处,而且我想着大地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多么残酷。它到处张大的幽暗、凄厉的饥饿之口,如同那个年代的林木,它们没有过错,而只是一种过程,它们也许会引渡我们学会用尊重细致的态度珍爱这大地上的事物,但我们只学会了害怕和慌张。如同母亲咀嚼的香柴花和我做馅饼的玫瑰,它们有着同样沁人的芬芳,但我已经和母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