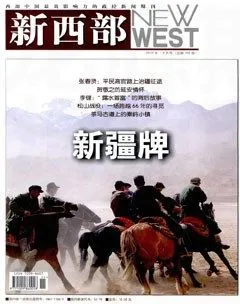贺敬之的延安情怀
你或许不知道他曾经官至文化部代部长,但你肯定知道他的著名诗篇《回延安》。其实,从《翻身道情》到《南泥湾》。从《白毛女》到《西去列车的窗口》。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每一部红色经典,都已深深镌刻在一代又一代普通百姓的心中。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16岁那年奔赴延安的决然选择。
汽车行驶在前往延安的公路上,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沟沟峁峁沐浴在和熙的春风中。
一面大墙上,一排醒目的大宇“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跳入眼帘。车内的乘客几乎异口同声地吟诵起来:“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延安到了!窑洞、延河、南泥湾……我极力想寻找贺敬之《回延安》的感觉。却怎么也无法找到。是啊,没有经历过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享受”过这片土地带给自己的苦与乐,怎么会有老人家那样刻骨铭心的情愫和牵挂?
不远处,巍巍宝塔山高高矗立着,不知它是否还记得70年前,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风尘仆仆地向它走来的身影?
漂泊路上
1924年,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今山东枣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他的父亲却开明达理,送他到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1937年,正当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兖州简师时,日本人发动了侵华战争,简师被迫南迁。贺敬之因为年龄小,只好退学回家。
可是,贺敬之实在想继续上学,便四处打听简师的去向,却没有结果,只是听说山东的学校都流亡到了武汉。于是,他决定自己寻找母校,就和4个伙伴千里迢迢来到了武汉。
此时武汉已经属于战区,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停课了,学生们都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贺敬之便积极加入进去,和同学们一起办墙报、搞演讲、编排一些救亡的戏剧。
贺敬之自小酷爱文学,读了很多书,有时也写一些诗文。在武汉时,他又拿起了笔,在《朔风》、《中央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北方的子孙》、《失地上的烟火》等作品,成了学生圈里颇有名气的小才子。
1938年,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贺敬之随着学校的师生们经过陕南,来到了四川梓潼。
在流亡的路上,许多同学随身携带的一些书籍和刊物,成了贺敬之宝贵的精神食粮,只要有时间,他就看书,从中了解到红军长征和共产党在延安的情况。一本由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更是让他看得欢欣鼓舞,上边有周而复的小说,反映延安是怎么开荒的;有关于延河的散文和诗歌;还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招生广告。“我要报考鲁艺,我一定要考上鲁艺!”贺敬之激动万分。
1940年4月,天气乍暖还寒,贺敬之收拾好行囊,和3个同学再一次踏上旅途。他说:“这一次不是流亡,而是奔赴我们心中的理想国——延安。”
一路上,贺敬之他们感到政治空气很紧张。为了避开国民党的盘查,他们4人决定两人一组,分头行动。为了保持联系,他们还确定了联系暗号,无论走到哪里,就在路旁别人不注意的地方,画一个草书的“神”字。
走了一天,贺敬之和同伴都能看到另一对伙伴留下的“神”字。然而,快到益门镇(宝鸡境内)时,突然没“神”了,贺敬之和同伴只好停下来等,可好几天过去了,也不见伙伴的踪影。就在他们焦急不安之时,突然远远地看见一个人扶着另一个人向他们走来。原来,他们走了一条斜路,又生了病,耽误了行程。
经过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抵达西安,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室的大门。1940年“七·一”这天,贺敬之和同伴们登上了前往延安的汽车。
圣地岁月
“一到延安,那就兴奋得不得了了。”80多岁高龄的贺敬之说起当年到达延安的情景,依然是那么豪情满怀。
贺敬之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灿烂的、一个光芒万丈的世界。“感觉就是像我的许多作品里讲的,像到了家,到了真正的家。”
那个年代,数以万计怀揣理想的热血青年,历尽艰难来到这个西北小城,贺敬之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可是,他又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到了延安,贺敬之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跃进》,正是这组诗,显现出他在诗歌上的才华,使得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他。
而且,在鲁艺不长时间,贺敬之就以《五婶子的末路》、《小兰姑娘》、《黑鼻子八叔》等诗作崭露头角。接着,他又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延安火热生活的作品,比如秧歌剧《栽树》、《秦洛正》;诗集《朝阳花开》、《乡村之夜》、《并没有冬天》、《放歌集》、《笑》等。
在延安,贺敬之见到了他所敬仰的胡风,而且他的作品也很快在胡风主办的《七月》上发表,如胡风编选的“七月诗丛”《我是初来的》,贺敬之便是主要作者之一,有5首诗被收录其中。他的诗集《并没有冬天》也被胡风收进由他主编的《泥土诗丛》。直至解放后,胡风也一直在关注着贺敬之的创作,曾致信对他的诗大加肯定:“你的反映农村的诗,很少有人能写成这样,这使我想起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
然而,贺敬之后来的“逆运”和“坎坷”,也与胡风有着直接的关联。这已是后话。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毛泽东于2日和23日接连做了两场报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这两篇报告就是后来被文化界屡屡提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
座谈会结束没几天,毛泽东便亲临鲁艺,又为师生们作了一场演讲。
“5月30日,毛主席到鲁艺来,是我先看到了他。”很多年之后,贺敬之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一张小桌子,旁边有一个座位。可毛主席始终没坐,一直站着讲话。我坐着小马扎,在离他很近的地方。”
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鲁艺很有成绩,也发展得很大了。但是,我看你们还是个小鲁艺。小鲁艺的学习很重要,但是,你们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人民群众。”毛泽东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鲁艺的师生们深深折服。贺敬之说,当时毛主席提到的一个问题,让他印象格外深刻。“就是关于洋包子和土包子的问题。说的是我们要大量吸收外来干部,但是我们不要轻视地方干部。不要以为一切洋包子说的都是好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应该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毛主席说,其实往往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不够的。”
《讲话》发表后,根据地掀起了新秧歌运动。1943年到1944年,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也单独写了一些秧歌剧。这个时期,贺敬之创作了不少歌词,传唱至今的歌曲《南泥湾》就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为慰劳三五九旅而创作的。而他创作于1943年的《翻身道情》,则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由于这首词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这个“误会”恰恰证明了作者深入生活的功底。
不过,延安时期的贺敬之创作上的最高成就并不是《南泥湾》,也不是《翻身道情》,而是歌剧《白毛女》。
贺敬之说,创作《白毛女》是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周扬和张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并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要将其转化为艺术作品,却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
《白毛女》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人作曲,1945年初完成,同年4月为中共七大代表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是,“艺术上是成功的,是适时的。”此后,《白毛女》在解放区各地陆续上演,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据说,一些地方演出时还出现过战士和群众要枪击或痛打黄世仁的场厩,为此,上级作出规定,观看《白毛女》演出时,不准带枪,以免出现不测。在解放战争中,“为喜儿报仇”同样成为解放军战士最普遍的口号。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白毛女》以鲜明的主题和感人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歌剧。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又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舞剧等。1951年,电影《白毛女》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
重回延安
抗战胜利后,贺敬之离开延安,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1947年,他参加青沧战役,立功受奖。1949年初,随解放大军进入北平,不久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并进入中央戏剧学校创作室工作。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年间,文坛上却鲜见贺敬之的声音,他也几乎没有发表过新作品。原来,进城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弱,1951年春天,他被确诊为肺结核,一直养病。
不过,身体状况只是贺敬之淡出文坛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创作上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1950年,贺敬之曾全身心投入过歌剧《节振国》的创作,但一位领导认为该剧本有严重问题,“我自己感到迷惑,觉得搞不下去了。”贺敬之回忆说。
这一年,贺敬之在《人民戏剧》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谈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提出“向工农兵学习,进行自我改造,不应使自己等同于工农兵思想的感情,而应培养自己高于工农兵思想”的见解。这样的观点同样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受了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影响。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立场观点。
1955年夏天,身体康复之后赴德国参加“席勒逝世150周年”纪念活动刚刚归国的贺敬之一下飞机,就被反胡风专案组人员接走了,继而是严厉的审查批判,长达一年时间。
逆境之中,重压之下,贺敬之却显示出性格倔强的一面,他决心用创作再次证明自己作为诗人的崇高职责。
1956年3月,贺敬之陪同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这时我已经离开延安11年了,回去以后感觉很不一样。”贺敬之回忆说,他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要他出个节目,他便答应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
那天晚上,贺敬之在窑洞里走着唱着,一边流泪一边写,写了一夜,结果感冒了,嗓子说不出话来,写的诗也没有在晚会上朗诵。后来,这首诗被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走,发表在了《延河》杂志上。
这就是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诗篇——《回延安》。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朴实无华的语言,真挚动人的感情。让《回延安》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一首难得的经典作品。在这首诗里,贺敬之用了不少陕北方言,如多次出现的叠音词“几回回”、“树根根”、“羊羔羔”、“白生生”、“一口口”等,抒发自己对母亲延安的眷恋之情。
此后数年,尽管贺敬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和迫害,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放声歌唱》、《三门峡歌》、《十月颂歌》、《雷锋之歌》等,成为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情牵西部
也许是因为在四川、在延安度过了自己人生最难忘的岁月,让贺敬之对广袤的西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为数不多的经典诗作中,与西部有关的不仅比重大,而且影响也很大。
1959年7月,贺敬之第一次到桂林,就创作了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山水诗”的《桂林山水歌》。诗中写道:“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水几重呵/山几重/才绕山环桂林城/是山城呵/是水城/都在青山绿水中……”如此如梦如幻的描写,难怪会让那么多人读罢诗篇,便要收拾行囊直奔广西……
之后,贺敬之三次到桂林,每次都有佳作问世。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首他亲笔书写的赞美阳朔的诗作被悬挂在醒目之处“东郎西郎江边望/大姑小姑秋波长/望穿青峰成明月/诗仙卓笔写月光。”
1963年夏天,贺敬之赴西北采风,年底在新疆阿克苏写下了长诗《西去列车的窗口》。1964年1月22日,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呵/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你可曾想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
有人撰文说,《西去列车的窗口》是“新中国西部开发之强音”,是当年反映知识青年支边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的影响力和作品的思想激情相得益彰,使之成为那个年代一首气势磅礴的进军曲。“可以说它的问世,推动了整整一代人奔向边疆的进程。”
直到今天,在老知青、老支边战士的聚会上,也常常有人激情满怀地朗诵这首诗。导演郭碧川说,他当年也是因为朗诵这首诗而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演员的。而且正是这首诗,让他与西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主演和导演的多部影片都与西部有关,比如《杰桑·索南达杰》、《西部之恋》等。
当然,在贺敬之的心中,让他最牵挂、最思念的还是延安。
1978年,贺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来又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务。虽然文化界的拨乱反正任务繁重,而且还要时不时地出面平息各种思想纷争,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延安。
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时,他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顺访了延安。返回北京的路上,他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干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作者注: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2001年5月,76岁高龄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贺敬之感慨万千;40多年前一道闹过秧歌的老邻居大多已经过世,他们的后代,当年扎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也已经年过半百,手里牵着小孙子来看望“老鲁艺”。时光如白驹过隙,物是人非,只有诗歌是不变的。贺敬之在自己诗歌人生的起点上,再次吟诵自己的诗句,顿时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2004年7月4日,正值《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行期间,主办方邀请贺敬之、魏巍等部分曾经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老延安”座谈。贺敬之深情地说,不管哪次回延安,都像是孩子回到母亲身边一样,感到无比亲切和激动,“我永远都是一个延安人!”
2010年4月9日,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共同发起的首届“金葵花”中国歌剧艺术成就大典之“终身成就荣誉”在京揭晓,86岁的贺敬之与郭兰英、乔羽、郑小瑛等19位艺术家获此殊荣。
如今,贺敬之老人和夫人、著名作家柯岩在北京安静地享受着他们的晚年生活,力所能及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闲暇时读读报,练练书法。许多人并不知道,书法一直是贺老的爱好,他写的字幽雅清丽,气韵生动,而且汉隶、魏碑等均有造诣。
而在千里之外的延安,许多人还在期盼着,老人家在有生之年,还能回一次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