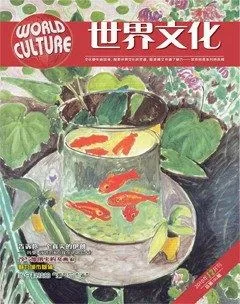埃德加.斯诺\\鲁迅及《活的中国》
微微泛黄的纸张诉说着岁月沧桑的记忆,暗红色的封面彰显着中国独有的气韵——它就是1936年8月由英国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的首本英文版《活的中国》(Living China)。该书一经推出,就受到西方文艺界的热烈好评。纽约的雷纳尔一希区柯克出版社也于第二年在美国再版了此书。伦敦《英国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评论称:“我们能接触到的来自中国的书太稀少,因此,这部现代中国小说的译作具有历史性意义。此书的编者是生活在北京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这就使它具有更加不同凡响的意义。斯诺先生为西方文明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造成的深刻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解读,为文艺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做出了卓著贡献。”它为当时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建构了一座精神桥梁,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和妻子海伦·福斯特倾尽五年心血为中西文化交流献上的一份珍贵礼物。
《活的中国》是一部中国短篇小说翻译著作,由斯诺先生亲自撰序。正文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鲁迅作品,收有《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和《离婚》等7篇短篇作品。第二部分题名为“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共计收入14位作家的17篇作品,它们是:柔石的遗作《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自杀》和《泥泞》、丁玲的《水》和《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在“大连号”轮船上》和《第三支枪》、林语堂的《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郁达夫的《紫藤与茑萝》、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佚名的《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断》,以及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这些短小的故事,把真实的中国人刻画得入木三分,它如同一部感人肺腑的纪录片,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中国社会变革中最艰苦的岁月。
译者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1928年,斯诺刚刚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还是个年仅23岁的青年。他不远万里来到这个东方国度只为一时新奇,憧憬一段刺激的冒险旅程。然而,在采访路途中,他亲眼看到因特大旱灾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遍及各处的精神麻木、奄奄一息的人群。作为一个出生在富裕、开放社会的美国人,他为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他开始关注中国,并试着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活的中国》序言中他曾提到:“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这片“沸腾”的热土深深吸引着他,原本计划短暂的访问变成了长达13年的驻留。随后,在新闻采访工作中,他逐渐接触到了一批中国文化的精英和精神领袖。其中,与鲁迅的会见更是直接促成了《活的中国》的编译。
说到斯诺和鲁迅的结识,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中国学者姚克。如果说鲁迅是斯诺“了解中国的钥匙”,那姚克就是帮助斯诺找到这把“钥匙”的领路人。姚克的英语极好,在东吴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戏剧专业时,常用英文投稿给上海英文报刊。1932年,他经宋庆龄介绍进入中国首家英文杂志《天下》月刊担任编辑,为上海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和天津《北华周报》撰稿,向国外人士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还把西方《茶花女》《巴黎圣母院》和《双城记》等文学名著译成中文,传播给中国读者。1932年底,斯诺为了把中国人民的苦难境况和革命文艺介绍给西方,打算把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于是经友人介绍结识了姚克,两人一见如故。姚克是个语言天才,又通晓中国历史典籍;斯诺洞察力极强,在目睹中国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之后,领悟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为了让斯诺更加了解这些根本性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姚克建议他阅读一些新文学作品。斯诺很快也感受到,研究中国人为自己写的作品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条捷径,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作品更是“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公平的证据”。
事实上,斯诺早在1931年得知鲁迅的大名后,就着手筹备编译一部他的小说集。从1932年冬天起,他在姚克、杨刚等青年作家的帮助下,开始编译鲁迅的小说。而他与鲁迅相见的机缘也得益于姚克。姚克虽和鲁迅年纪相差23年又4个月,却因深谙中国古典文学而备受鲁迅青睐,并成为他的知交好友。为了提高作品的编译质量,斯诺于1933年2月21日,在姚克的陪同下,与鲁迅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位中国大文学家所独有的不凡气度使斯诺大开眼界,他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的开头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初见情景:“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极其炽灼而感人……这是一双机敏、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极富有感情又卓具理智。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问题,话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气韵的声音回答了。”斯诺对鲁迅的钦佩和崇拜之情是显而易见的,而鲁迅对这位美国朋友似乎也颇有好感,“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他在给一个友人的书信中说道。
斯诺原本只是想编译一本鲁迅的短篇小说集,但1933年11月5日,鲁迅给姚克写信时提议:“现代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择一本,每人_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于是斯诺采纳了鲁迅的建议,决定在《活的中国》第二部分收入一些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在选择具体篇目时,斯诺对那些语言漂亮的一概不感兴趣,他欣赏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即使文字粗糙些也没关系。在翻译时,斯诺强调“不要好英文,而要尽力贴近原作的思想感情或内在涵义的轮廓”。斯诺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他的译作,即便欣赏不到原作的风采,至少也能够了解“达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有时甚至能够看见它的灵魂。”
翻开《活的中国》的封面,一张颇具鲁迅神采的照片映入眼帘。这张照片是1933年5月26日姚克陪同鲁迅一起到南京路雪怀照相馆拍摄的。当年,斯诺撰写完《鲁迅评传》后,想要一张鲁迅的近照。经姚克转达后,鲁迅提供了一些照片让他挑选,但姚克认为这些照片“远不能体现先生的性格和神韵”,于是提议考虑重拍一张,得到鲁迅首肯。那天下午,鲁迅共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鲁迅和姚克两人的合影,这也是鲁迅先生一生唯一的一张与别人的单独合影;另一张则是鲁迅的单人半身像,此照片先是被斯诺在美国《亚细亚》1935年1月号上发表《鲁迅评传》时一起刊出,后来才于1936年底印在该书的扉页上。
除了编译者斯诺亲笔写的序言和正文的24篇翻译作品,《活的中国》的附录中还收入了斯诺当时的妻子海伦·福斯特专门为此书撰写的长篇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作为一个中文水平不高的外国人,斯诺能够顺利完成《活的中国》的编译,与妻子的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写序时还尊称海伦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海伦在着手写这篇论文前,还特地让斯诺去拜访过鲁迅,因为文中所要探讨的许多问题,需要鲁迅来亲自定夺。于是,1936年5月3日,斯诺由姚克陪同,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再次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鲁迅表达了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他对中国左翼文学创作队伍的一些看法,海伦1936年6月写《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这次会晤记录。这篇论文第一次刊出并非在《活的中国》中,而是发表于伦敦的《今日生活与文学》杂志上,为随后《活的中国》的出版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在选编《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斯诺和许多中国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透过中国现代小说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累累伤痕,还包括这个民族倔强而高傲的灵魂。《活的中国》的编译是在鲁迅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它是向外国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成果,是认识旧中国的现实和展望新中国前景的开端,更是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初系中国情结的有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