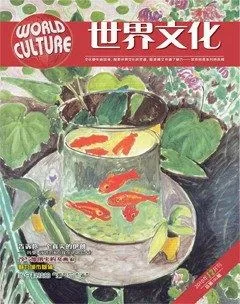追忆谢甫琴柯
最初听到谢甫琴柯的名字,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从父亲自前苏联带回的《谢甫琴柯画册》上。那时年纪还小,只记得他是19世纪乌克兰著名诗人、画家。待我们捧读戈宝权译的《谢甫琴柯诗选》,并渐渐走近他,已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记得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曾满腔热诚地推介了拜伦、裴多菲等一批19世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即“反抗”)诗人,说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而“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实际上谢甫琴柯也应属“摩罗”诗人之列:“别等待/等待自由——徒劳!/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来?/我的人民啊/快举起所有的棍棒/还有那,乌克兰宝刀!/那时候,自由——才能来到!”读读这些惊雷与号角般“叫喊与反抗”的振聋发聩的诗句,能不“心神俱旺”,热血沸腾吗?
谢甫琴柯1814年3月9日生于乌克兰基辅省一个叫麦瓦茨的小村庄,祖辈都是农奴。他只活了47岁,却当了27年农奴;被充军流放了10年;剩下的13年过得也如他所说,是“用链子拴着的狗”一样的“自由”生活。那时的乌克兰不仅受到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还受到列宁说的“最残暴的亚洲式的农奴制度”的压迫。在农奴主眼里,他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他自幼聪颖、伶俐,乌克兰民歌和美丽的原野又滋养与激发了他的艺术天赋,放牧间隙他注意搜集民歌和描摹自然风光。农奴主发现他的艺术才能,把他带到彼得堡,想把他变成一株摇钱树。1838年著名画家勃柳洛夫器重谢甫琴柯的天赋,又同情他悲惨的身世,用卖画筹得的2500卢布巨资,帮他赎身,并送他进美术学院深造。
有了“自由身”的谢甫琴柯更加发奋地学习绘画技巧,并开始了诗歌创作,1840年他的处女作《科布查尔》(乌克兰民间流浪歌手的统称,多系盲人)为他在乌克兰和俄国赢得了广泛声誉。在莫斯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本谢甫琴柯的《科布查尔》,那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最爱读的书。他在跃马挥刀战事倥偬中,也将它带在身边,每每思念乌克兰乡土,都会吟诵谢甫琴柯的诗和哼着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汹涌澎湃/狂风怒吼,落叶纷纷/你看那月亮苍白暗淡/在乌云后面徜徉不停/就像扁舟飘在海上/随波起伏时现时隐。”由于经常翻阅,封面和边角都已磨损,后来缠绵病榻,这本诗也—直放在他的枕边。
1841年谢甫琴柯创作的《吉卜赛占卜师》在彼得堡画展中为他赢得第三个奖项的同时,他的以18世纪乌克兰反对波兰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诗《盖达马克》,也为他带来更广泛的声誉。他的名声也传到沙皇耳中。那个年代能被沙皇召见,是难得的宠幸,而谢甫琴柯对此却不以为然。相传其余被召见者步入召见大厅,都无一例外地躬身向沙皇致敬,唯独谢甫琴柯一动不动。沙皇问:“你是什么人?”他不卑不亢地回报了姓名。沙皇说:“我是一国之君,举国上下谁见到我都要躬身行礼,你为何这般无礼?”他回答说:“是你要见我,不是我要见你。如果我也像其他人那样垂首躬身,你如何看得清我呢?”这传说真伪无须细细考证,人民爱戴他、敬仰他,他们都知道他在权贵面前,从来不是“恭顺的奴隶”:“有一天,我走在涅瓦河畔/那时正半夜更深/我一边走,一边思忖/如果奴隶们不那么恭顺/这些被玷辱的高楼/就不会立在涅瓦河滨/人们就会变得亲如姐妹、弟兄/可现在,这儿只见无数眼泪和苦痛/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神灵/是一群猎狗的看管人在霸道横行……”沙皇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群猎狗的看管人”。
1847年刚刚赎身做了10年“自由人”的谢甫琴柯,又由于在长诗《梦境》中讥讽沙皇暴政和参加秘密政治社团而被捕,并被发配到偏远的乌拉尔山的奥伦堡服役,沙皇尼古拉一世亲批:“严加监管,禁止写作、绘画。”然而枷锁与酷刑都无法摧毁他的意志。透过牢狱的小窗,他凝望夜空,在小纸片上写着对故乡的怀念:“田野、山峰沉入黑暗/一颗星出现在深邃的远天/我禁不住悄悄流泪/星儿哟,此刻你是否也出现在乌克兰……”他把这些纸片藏在靴筒里,后来集印成诗集《在囚室里》,这些诗还有一个别称——靴筒诗。后来,他又转赴曼格什拉克半岛羁押,直到1857年才恢复自由。
虽说恢复了自由,却依旧受着监视,流放与苦役又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晚年他唯一感到宽慰的是有机会同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同时代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家们交往。这些人和谢甫琴柯一起,一直在为他的兄弟和妹妹解脱农奴身份而奔波。1859年,谢甫琴柯拖着病体回家乡看望妹妹雅琳娜,途中他曾写过《写给妹妹》这首诗:“……我一面走,一面思量/仿佛走进梦乡/我看见一座春光明媚的花园/山丘上有一处小巧的住房/好像少女穿上了嫁妆……/樱桃树下坐着我的妹妹/她是个神圣的、受难的女郎/目不转睛地盯着德聂伯河/把我这不幸的人盼望/她看着我的小舟从浪花里浮起/漂着,漂着,却沉入无底的汪洋/我听见她在呼唤:‘你在哪里,哥哥呀!’/我从梦中惊醒/依旧满怀悲愤/妹妹仍在服着劳役/我呢——还在囚禁……”那时,整个俄罗斯都是“没有上锁的牢狱”,即使是“自由人”,不同样在囚禁吗?!
1861年3月10日,谢甫琴柯刚刚度过他47岁生日的第二天,便在政治迫害与物质生活窘困中离开了人世。就在他去世不久,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他未能看见沙俄统治与农奴制度的垮台,但他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他在那首著名的《遗嘱》中说:“当我死后/请把我葬在乌克兰辽阔的草原上/让我能望见广袤的田野/能望见德聂伯河边的峭壁/和听见河水的喧响。”他呼吁:“起来!砸开镣铐/用残暴的敌人的血/把我们的意志浇灌!”他预言总有一天“河水把敌人的血/从乌克兰身上冲洗下来/冲入蓝色的大海”。并深情地期望,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乌克兰人民,“在伟大的自由的新家庭里/请别把我忘记/常用亲切温存的话语/把我追忆。”他死后,友人根据他的遗愿,把他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在德聂伯河岸边的卡尼夫的僧侣山——后改称谢甫琴柯山。
谢甫琴柯是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上生长的一株大树,他深深扎根在人民中间,用他的诗歌倾吐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斗争,表达他们对自由、对光明和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与他们肩并肩地同黑暗专制统治奋战了一生。他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创建了乌克兰文学语言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是乌克兰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早在1921年茅盾先生就将谢甫琴柯的《狱中随想》译成中文,并将他列入《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推介给中国读者。此后,他的作品不断被译成中文,深受中国广大读者欢迎。戈宝权、梦海、蓝曼、高莽、魏荒弩等翻译家都译介过他的作品。1961年为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又编印出版了他的三卷文集。父亲应约在他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做报告时,一改通常的“年表加空洞概念”的枯燥模式,而是用“亲切温存的细语”,和听众一起“追忆”这位乌克兰的农奴诗人。报告的结尾更出人意料地用诗来呼应谢甫琴柯的嘱托:“……在你离开我们一百年的时候/不仅乌克兰人/不仅全苏联人/都不会把你忘记/都在用你所愿望的/‘亲切温存的细语’/把你追忆∥而且啊,在这儿,在你曾关切过的中国/也在用‘亲切温存的细语’/把你追忆//春风呵,托你带着这/‘亲切温存的细语’/掠过蒙古沙漠/穿过贝加尔湖/越过乌拉尔山/送到德聂伯河畔/送到塔拉斯耳边……”有作家曾评论说,这样的报告就像是感受到从乌克兰草原上“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
如今,又五十年过去,中国人民依旧怀念谢甫琴柯这位伟大的诗人。前不久,翻译家高莽在乌克兰驻华使馆受乌克兰总统之托,为表彰谢甫琴柯为乌中两国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授勋仪式上的发言中,还提到谢甫琴柯生前对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给予的道义上的关注与支持。谢甫琴柯不仅生活在乌克兰人民心中,也生活在中国人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