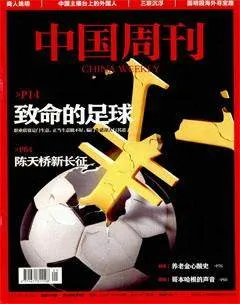昆曲推手白先勇
从青春版《牡丹亭》到新版《玉簪记》,白先勇用个人声望、非商业化演出和青年观众的锁定,给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烙上了时尚的印记,也烙上了白先勇的印记。
2009年12月15日晚,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昆曲《玉簪记》大幕徐徐拉上。兴奋的观众们把最多的掌声给了最后出来谢幕的白先勇,掌声慢慢停下,所有人都期待他说些什么。
“我们要感谢可口可乐北京公司……”白先勇放慢语速说道。压力
谢幕前的三个小时里,舞台上清丽的小道姑陈妙常一唱三叹,诉说着对身份的无奈,以及对俊俏书生潘必正的思慕之情。“松舍清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怎奈凡心转甚。”
舞台两侧的显示屏上,不断地把这古老的唱词用中文和英文展示着。观众中,有一些外国人,但英文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他们。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看着英文才可以完全通晓唱词。原因很简单,唱词更接近古汉语,而英文则已经翻译成白话文。
和白先勇2004年推出的青春版《牡丹亭》不同,新版《玉簪记》是一部轻喜剧,剧中惹人发笑的台词不时进出,场内笑声一阵阵。
几百年来,《玉簪记》不知道演出过多少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这出戏神摇目眩,被那些笑点逗乐。这—晚,昆曲从书本上活了过来,又有人为她叹为她笑了。
为白先勇而来,然后被昆曲折服,这正是白先勇希望见到的景象。而在演出的最后,热情的年轻观众把声势最浩大的掌声给了白先勇,他们站了起来,息了掌声,渴望听他说些什么。
白先勇当然有特别的东西可说,比如,当他说,戏中的古琴声来自“九霄环佩”——唐肃宗登基时曾奏响过的乐器时。观众们掌声一片。可是,他仍然要首先要说,‘‘我们要感谢可口可乐北京公司,感谢北京大学…”
观众发出轻轻的笑声,那是一种善意的笑声。大师台上做一下广告,对大批手中持20到40元低票价的学生们来说,只是个有点好玩的事情。
这好玩的事背后,对于白先勇而言,实在是一系列的压力——整个戏剧的运作,不是以商业为目的,票房一定入不敷出。资金的来源,几乎完全来自白先勇的募集。
“我一个作家,以前写书出书从不求人,现在却要撂下面子,四处托钵化缘。”白先勇笑着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用尽了人情支票”,才从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台湾朗讯科技公司等处,筹得资金近3000万元。如今,这些钱已经差不多用完,而可口可乐北京公司的赞助无疑雪中送炭。
不过,更大的压力,来自昆曲的式微,这让这个年逾70的老人,从台湾来到大陆,寻找最好的年轻演员,给昆曲注入新的活力。新的活力
白先勇找到的年轻演员是俞玖林和沈丰英,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记》的男女主角。
2003年,白先勇选中他们时,两人不过20出头,在昆曲界还是籍籍无名。
现在,他们站在白先勇身边和他一起接受热烈的掌声。
他们依然还记得自己曾经的困窘时光。
1998年,两人从苏州艺术学校昆曲定向培养班毕业,进入当时在全国六家昆曲院团中还属末流的苏州市昆剧院。由于技艺突出,院里让俞玖林搭伴比他大15岁的名演员王芳唱生旦戏。即便如此,俞的演出机会也很有限。
“从毕业到后来担纲青春版《牡丹亭》,中间的几年里能有机会唱完全场的,也就两三次,而且还都是在大型的戏曲艺术节上,汇报演出用的。”俞玖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段岁月,他大部分时间是闲着,练练功,或者是被院领导拉到周庄的古戏台去,唱几段折子戏,帮助景点吸引游客。
那是一种似乎无法摆脱的困境。
昆曲从顶峰下行,已经几百年了。宋元以后,昆曲曾一度达到高峰,但其倾向闲雅的风格,也让她开始慢慢失去更多的观众,被更热闹的京剧取而代之。
刚刚辞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经评论昆曲式微的原因说,“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是欣赏意境的好。”
1949年后,京剧还有过一段因为现代剧而出现的中兴,《沙家浜》、《林海雪原》的京剧版直到现在仍然有生命力。昆剧的古雅,导致几乎没有现代戏的成功,等到人们发现昆曲不宜新编,应该专注经典时,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开始萎缩。
在流行文化横扫一切的时代,昆曲,这个在戏曲中都有些曲高和寡的剧种,似乎很难有出路了。
俞玖林还是会常常想起那段无所事事的青春岁月,他说,那时他和一帮同学经常待在单位宿舍里发呆,看窗外高而蓝的天空,即便像他这样不愿多想未来的人,当时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平静。
《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戏剧评论家姜志涛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力较强的北方昆剧团的忠实戏迷一度只剩下几十人,而且还都是老年观众,“演出时,只看到台下稀稀拉拉的几个白头发……听到有观众去世,演员们都要感慨半天,来看戏的人又少了一个”。
与此同时,知名的演员也开始流失。与白先勇一直保持合作的苏州市昆剧院当年就面临这样的窘境,院长蔡少华说,最惨的时候,连院里最好的昆曲演员—全国戏剧“二度梅”得主王芳,都跳槽做起了化妆品生意。
1980年代时,演出团体和剧场均由政府全额拨款,还不存在“入场费”问题。1990年代初剧场改制,演出单位很快面临场租问题,若实行低票价,将无法收回演出成本,将票价提高,又会使观众越来越少。
在大陆,昆曲的延承,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台湾的方法
就在俞玖林和他的同学们呆望着宿舍外的天空时,白先勇在台湾开始了自己的尝试。
白先勇是白崇禧之子,幼年时,他曾经亲眼看过梅兰芳出演的昆曲。昆曲的曼妙身姿从小在他心中扎根,结出果实还要等到几十年后。
白先勇青年时留学美国,几张昆曲的黑胶唱片曾经是他思乡的背景音乐。
1982年,由白先勇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游园惊梦》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首演,剧本由白先勇本人亲自执笔,包装运作团队也都是他找来的一帮朋友,演出效果空前轰动。
这是一出带有感伤色彩的剧目,主要叙述一位由大陆迁居台湾的昆曲名伶,在某一天晚上与故旧重逢,有人建议她清唱昆曲《游园惊梦》,进而唤起了她当年在南京时的一连串记忆,沉浸在“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氛围里的故事情节,颇能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
但话剧毕竟只是话剧,做一出真正的昆曲,这一念头开始在白先勇心底悄悄萌生。
在台湾,仍有很多人喜爱昆曲,可是,那里没有一流的演员。
1987年,白先勇回到大陆,在上海观看了昆曲名家华文漪主演昆曲《长生殿》。多年以后,他跟《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起那次经历时说, “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十年“文革”并没有割断传统艺术的血脉,曾经离场的昆曲老艺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舞台;担心的是观众老化。而且稀少,面临传承的危机。另外,昆曲剧本的删减也不尽如人意。
1988年,白先勇将《游园惊梦》带回大陆,女主角改用华文漪,巡回广州、上海和香港演出,同样获得了成功。
这一过程让白先勇直观地看到了国内昆曲发展的业态,他对昆曲传承的危机感更浓烈了。“当时就想做点事情,但苦于没什么好的方法。”他所能做的,无非是把大陆名角请到台湾去,跟当地的昆曲艺人做一堂合作演出,或者是办—个大陆昆曲艺人的表演专场,再就是发表—些昆曲知识绍介的文章,在公共媒体上推广昆曲。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个很偶然的相遇让白先勇找到了解决昆曲传承问题的办法。2002年底的一天,白先勇受邀到香港一家中学讲授昆曲知识,他想找一些昆曲演员来做现场表演示范,主办方找来了苏州市昆剧院的几个青年演员,其中一人就是俞玖林。白先勇对几个年轻演员的表演非常欣赏,言语之间流露出愿意帮助培养之意,被苏昆院长蔡少华看在眼里。2003年初,白先勇受邀前往苏州,又相中了沈丰英等几个演员,一出青春版《牡丹亭》的计划由此开始。
白先勇先是动用之前结交昆曲艺人获得的资源,请来浙江省昆剧团的名小生汪世瑜和江苏省昆剧团名花旦张继青,指导俞玖林和沈丰英的唱腔和身段,自己则组建编剧团队,在忠于汤显祖原著的基础上,对《牡丹亭》唱段做适度删减。之后又从台湾找来灯光、美术、舞美、服装、舞台设计等团队,对青春版《牡丹亭》做全方位立体包装,力求整出戏既保留古典韵味,又不失时尚感。
历时两年多时问的精心打造,2004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终于在台北上演。之后是大陆、香港、澳门、韩国、美国、英国,以大学校园为基地一路巡演下去,所到之处,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
沈丰英和俞玖林,在出演青春版《牡丹亭》后双双获得“梅花奖”,在年轻观众眼里,他们是头顶光环的明星。非营利演出
回过头来看,用年轻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把昆曲带入大学校园,并不是多了不起的壮举,为什么获得成功的人是他?
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委员王蕴明认为,除了白先勇本人在大学生群体的号召力之外,能够调动各方力量协同出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举例说,以前昆曲界人士排演新戏,即便是用新人担纲,也很少具备像青春版《牡丹亭》那样的宣传效应,也就很难引发轰动。
白先勇本人却一再强调,是昆曲艺术本身的美吸引了大家,“如果观众是冲着我来看的,恐怕也就能撑个一两场,再来演就不会有人看了。”
王蕴明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北方昆剧团团长一职,谈及将昆曲艺术引入校园,他说,当年他也曾多次带年轻演员到北京高校去,做一些公益性质的演出和讲座,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磨练新演员,同时也能向大学生传授些昆曲知识。”但是因为缺乏活动资金,类似的活动规模总是很小,不像白先勇这样,闹很大动静。
事实上,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汜》的确耗资巨大,尽管多数参与其中的大牌艺术家并不求与市价相等的物质回报,但只算服装道具制作、剧场租金、市场推广等工序,都需要耗费不菲的投入。与此同时,演出多半是在大学校园里进行,票价也远低于市场水平。
白先勇说,他从来没想过要靠推广昆曲来赚钱,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记》的运作,多半是在靠募集来的资金在维持。
得到可口可乐北京公司赞助的500万元后,白先勇开始试着把募捐方向转向大陆,然而向大陆企业“化缘”更为艰难,因为大陆企业资助文化事业,不能获得税收上的减免。
王蕴明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国内昆曲院团往往依赖政府拨款,而一旦政府的支持力度减弱,去大剧院商演又赔钱,院团负责人就只好拉着演员们到处跑场子,演出质量也就很难不变得粗糙,昆曲艺术由此越发陷入没落的循环。
剧场之外
既然一出青春版《牡丹亭》已经起到了吸引年轻观众、培养年轻观众的目的,为何又再做—个新版《玉簪记》?
白先勇说,现状与他的预期还有一些距离,昆曲传承不是简单把观众吸引过来那么简单,还需要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真正产生兴趣。
这一点俞玖林有切身体会,在入行之初,昆曲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项安身立命的江湖技艺,在白先勇一遍一遍的讲解之下,他开始逐渐领会古典曲辞的优美,以及剧中人情感表达的点点滴滴,再后来,他也觉得昆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也让俞玖林目睹了观众在欣赏昆曲水平上的差异。“台湾观众对戏更熟悉,有些人甚至是拿着昆曲曲谱来看的,你出一点小差错,他们都会放在眼里。”同时,戏里一些幽微含隐的桥段,也更容易得到那里观众的共鸣。反观内地观众,虽然早已不像前几年那样“台上唱大戏,台下演小戏”,但给俞玖林的总体感觉还是“看热闹的居多”。“就像中间隔了一道门,台湾的观众都在门里边了,我们这边还立在门口往里边瞧,想进来还没进来。”
为了再拉观众一把,真正把他们领进昆曲的门,白先勇在新版《玉簪记》上演同时,推出了一份庞大的“昆曲传承计划”,具体内容包括定期举办国际性的昆曲学术研讨会和昆曲文化周,在大学开设经典昆曲鉴赏课程,建立昆曲影像保护数据库、组建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等等。
目前,在大学开昆曲课的计划已经得到北京大学的响应。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明年开春北大就将开设昆曲鉴赏选修课程,包括白先勇在内的文化界人士和昆曲专家都有可能过来给授课,学生选修该课程可获得学分,校外的昆曲爱好者也可以前往旁听。
白先勇笃信这一方式对昆曲传承的贡献,他说,台湾教育界、文化界和昆曲艺人在推广昆曲上存在共识,可以经常看到文化名^在公开场合讲昆曲、推昆曲,昆曲艺人也会深入校园,给学生做—些公益性质的演出,因此整个昆曲氛围比大陆浓郁。
他希望组建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等几项计划能陆续得到支持, “大陆文化界和艺术界也应该形成合力。”
在各种场合,白先勇说得最多的除了昆曲传承,就是昆曲复兴。在他看来,中国的昆曲和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一样,都是民族文化中至情至美的东西,“尽管它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周杰伦一样流行,但却不应该没落、消失,”白先勇说,再过十年五四运动就一百年了,中国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复兴运动, “如果真能复兴,我希望昆曲能在其中。”
但也许这一天不会在他手里完成。白先勇说,这几年的昆曲推广工作耗费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各种约稿已经让他的 “文字债”欠下一堆,另外写父亲白崇禧的传记《仰不愧天》,也计划于明年年底写完, “再做一段时间,我可能就会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学创作中去,毕竟那是我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