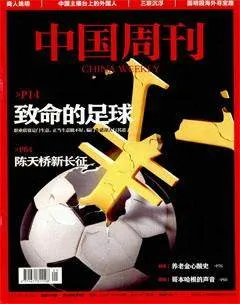武松拳头下的女人
武松杀嫂,迭配孟州牢城。中途经过有名的十字坡,进了有名的人肉包子店,碰到了有名的母夜叉孙二娘。那孙二娘雷人的很,上身穿着绿纱衫儿,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还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头上黄烘烘地插着一头钗镶,鬓边又插着些野花。
见武松等人采,便倚门迎接: “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时,好大馒头!”
施耐庵施大爷的文字开始暧昧起来。
而武松呢,刚刚撕开并割破嫂子胸脯的他,面对着孙二娘敞开的大胸,便流氓起来。
孙二娘去灶上取一笼馒头来,放在桌子上。两个公人拿起来便吃,武松却取一个拍开,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妇人嘻嘻笑道: “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
武松道:“我见这馒头馅肉有几根毛,一象人小便处的毛一般,以此疑忌。”
对一个陌生的妇人,能说出这种话来,梁山没有第二人。因为,这种话,第一要会说,第=要敢说。
武松在市井长大,会说,不难。难在敢说。为什么难?因为有两关:第一,敢于作践妇人;第二,敢于作践自己。
敢于作践妇人,对武松,也不难。潘金莲以后,武松不会敬重任何女人。敢于作践自己,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像个流氓,这是大难。要知道,武松极端自爱,这样的人,竟然这样作践自己,我只能说:武松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
接下来,见妇人不搭理,武松又问道: “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那妇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时,你独自一个须冷落。”
这样的馋涎声口,比起王英,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调戏的技巧,则远在粗鄙的王英之上。王英只有性,没有风流。武松有风流,却并不付之于性。
只是,孙二娘哪里是男人的性对象呢,她是男人的噩梦,不是春梦。她眼中的男人,也不是男人,而是牛肉:胖壮的,是黄牛肉;癯瘦的,是水牛肉。——肉欲倒是内欲,却是嘴上的肉欲,不是……她缺少性自觉和性爱好,她不会对男人有性爱的感觉。
她去里面托出一镟浑色酒来,武松悄悄把酒泼在僻暗处,虚把舌头来咂,装成喝了的样子,两个公人被麻翻了,武松随即也仰翻在地。
两个大汉来抬他去后面的对人间,他挺着,抬不动。弛要孙二娘来搬他。
施大爷将暧昧进行到底:孙二娘脱去了绿纱衫儿,解下了红绢裙子,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真好孙二娘!
武松呢,就势抱住孙二娘,把两只手一拘拘将拢来,当胸前搂住,却把两条腿往孙二娘下半截只一挟,压在孙二娘身上。真好武二爷!
孙二娘杀猪也似的叫将起来。这武二爷和孙二娘,天造地设,一对“二”男女。
这武松,打虎凭力气,杀嫂凭正气,制服孙二娘,凭流氓气。
武松要去打蒋门神,在大树下见到蒋门神,他却又不打。蒋门神的店里,柜台里坐着一个年轻妇人,正是蒋初采孟州新娶的妾。这小妇人生得俊:眉横翠岫,眼露秋波。樱桃口浅晕微红,春笋手轻舒嫩玉。武松看了,醉眼朦胧,径入酒店,在柜台相对的座位上坐了,不转眼看那妇人。
我们已经知道,武松特别善于调戏妇女。他的这种功夫,乃是家传:教会他的,就是他的嫂子潘金莲。
那妇人瞧见武松不怀好意色迷迷的眼神一直看着她,她只好回转头看别处。
武松道:“过卖,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这种语言,鲁智深说不出,林冲说不出,李逵也说不出。
鲁智深说不出,是天性中的高贵使他无法这样贬低自己。林冲说不出,是家庭的教养使他不能这样糟践自己。李逵说不出,是根本不懂男女风情。
“杀才!该死的贼!”妇人一直忍到现在,这时却不能不骂了。不骂,她成了啥了?但一骂,她就上了武松的当了。
武松早就等着这一声,便把那桶酒往地上一泼,抢入柜台里,一手接住腰胯,一手揪住云髻,隔柜子提将出来往浑酒缸里只一丢。扑通一声响,可怜这妇人被直丢在大酒缸里,头脸都跌破了,在酒缸里挣扎不起。
然后,武松大战闻讯赶来的蒋门神,大获全胜。可是,总觉得他前面,胜之不武。事实上,武松一生的功业,除了打虎,都和杀女人欺辱女人有关。那景阳冈上的老虎,说不定也是母老虎。
这样概括武松,似有损武松形象。——没办法啊,他在《水浒》里,就是一个专门让花容失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