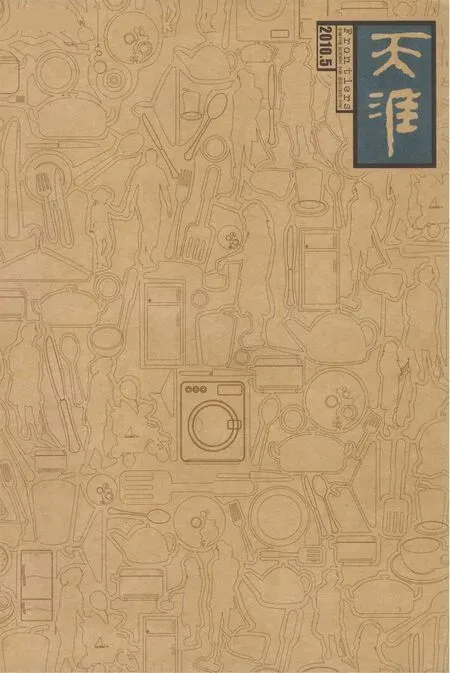乡村的声音(外二篇)
张怀帆
乡村的声音(外二篇)
张怀帆
那时是月夜,整个村庄都在安睡,我躺在土炕上,微闭着眼睛。我在听着一种鸟叫:黄杠!黄杠!叫声遥远却清晰,柔弱却坚定,像平静的呼吸,又像单调的钟摆。它仿佛就在我家对面的山上,又似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只鸟,为什么在月夜里独自啼叫?它是在为那片山冈、树林还是月亮?会不会也为了我?它想给我说什么?不然为什么把我叫醒?月亮亮光光地映进窗纸,我突然觉得它会不会是一个人的魂魄?但是那声音平静极了,丝毫听不出它的心思。那叫声柔弱,就让我起了相思,就让我慢慢地生起了忧伤。我还想,它在唤起我心里沉睡的某个部位,或者曾经种植下的某个深深的遗忘。那么,是不是我的前生跟万籁俱寂的月夜有关系?跟一个山冈、树林有关系?这其中有过怎样凄婉的故事?为什么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那么,让我随着叫声上路,越过窑洞、烟囱、畔上的枣树、门前的小路,越过小溪、田地和庙宇,沿着鸟的叫声,沿着月亮的足迹,去找寻丢失的记忆……而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在鸟的叫声中沉沉地睡去。
还是夜晚,风一遍一遍地敲击窗棂,甚至故意把院子里的某个农具撞倒以发出声音。我的父母,因为白天的劳动已经疲惫得只有鼾声,所以它只把我叫醒。而我也想,它来就是为了叫我的。它在院子里,发出了粗重的喘息,又像一个男人焦急的步子。它有什么急事?叫我去干什么?可我为什么又躺在炕上,不为所动?这股风,它来自哪里?放下大路不走,偏偏要拐进我们这小村,又偏偏要叫醒我。它到底想要我做什么?电线呜呜地响,星星也许都被吹落。它那么焦急,可我没觉得有什么事急着要做。我没敢出去,不担心它是强盗,而是怕被它掳去,到我不熟悉的地方。我能听见,它从我家院子离开,再没绕弯,直接到高处去了,到了很高很高的地方,再没了声音。我一直惶惑,这个家伙,它半夜闯来,到底要对我说什么?肯定非常非常重要,可我就是不能明白。第二天,我发现门前的一棵树被它掳倒了,它携带走了树身上的什么?那棵树能替代我吗?
有时在夜晚,村子里的狗疯了一样地朝一个方向群追而去,集体发出愤怒的咆哮,有的还像被石块击中一样发出疼痛的尖叫。不,深夜里,这样的小村不会来外人,狼更有几十年不见了踪影。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抓住我说:快睡、快睡!我闭上眼,听着那叫声,同仇敌忾,势不两立。它们肯定在咬一个确定的对象,而那个对象也必定是强大的,不然不会对峙那么长时间。那么,到底是什么?我常常会想到是一群鬼魂或幽灵,它们曾是这里的先人,但却再也回不到他们的住处。而这些狗,更像村庄的捍卫者,它们警醒、灵动、团结,誓死保卫着这个小村。它们相信,活着的人更重要,而游魂,最好不要打扰小村的宁静,还是远离曾经的故园,去开拓属于自己的家园。第二天白天,村庄的狗各自安静地卧在院子里,不像昨晚发生过追捕和战争,而且并没有哪一只狗身上有任何轻微的伤。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敬畏和说不出的震撼。这样的追捕还发生过多次,每一次,我都无法平静。后来当我在外上学,在一个傍晚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所有的狗都追了过来,冲着我狂吠,我突然感到悲哀,我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失去故园、漂泊的人?
村庄的后半夜,窑洞凉下来,只有鼾声;村子的土墙,土墙上搁置的农具都睡了,村子周围的树也一动不动,也许只有离村子不远的水井,还在汩汩地泛出清泉,发出清澈的响声,但村子听不见,村子里的狗都睡了。一只公鸡却醒了,它引颈发出长长的啼鸣,随之,此起彼伏,整个村子都是公鸡的啼唱。这遍啼唱对鼾声不发生干扰,最多引来几个翻身和几句梦呓。之后,又出现了长时间的安静。第二遍,一只公鸡又叫了,村子里的公鸡又都此起彼伏地叫了。这时,北斗星正在村子的上空,银勺子一样亮晶晶闪耀,树木已稀疏地露出了剪影。但还没有叫醒村庄,牛打了一声鼻息,又睡去了,狗把一只耳朵贴在地面,继续它的梦。撕开的缝儿又合上了,还是囫囵的黑夜。第三遍,公鸡们又叫了,这一次,启明星已出现在东边的天空,庙宇上空有一层光辉,树木出现轻微的抖动,有的公鸡从架上飞下来走在院子里拍打着翅膀伸长脖子啼叫,再不容缓的意思。而第一个尿盆倒出了围墙,听见一瓢水落地和盆子放在墙根的声音。黑暗破壳了,生出剥去鸡蛋皮儿一样清新的早晨。那只公鸡,它为什么在半夜里啼叫?天还黑得厉害呢!那群公鸡,它们为什么都赶快响应?它们啼叫的时候到底是醒着是睡着?它们像为一个村庄唱诗,又像在招魂。它们要从黑夜里叫回什么?如果没有这群公鸡,村庄将静寂得多么可怕啊,村庄将黑暗得多么可怖啊!因了公鸡们的啼叫,村庄升起了烟火气息,村庄有了吉祥,村庄也有了魂魄。后来,当我住在城里,半夜里,我只听过警笛尖锐的鸣叫,我的魂魄丢失在乡下,会不会被一只公鸡唤回到我出生的村庄?
有一天晚上,我和哥哥牵着牛,准备把它们拴进一间废弃的窑洞,因为风起云涌,山雨欲来,牛待在窑洞里会比待在漏水的棚下更舒适安全。就在我们走到坡底的时候,我俩同时听到了不远处一个妇人啼哭的声音,哥哥一下就听出了,是大婶。只哭了三声,再也没有了。哥哥拽起我的手就往家里飞奔,而没有拴住的两头牛也跟着我们跑了回来。我俩都处在极度的惊恐之中,并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任凭父母怎么安慰都不能平静。果然,过了不多日,我的大伯在挖窑时被塌下的土掩埋致死。对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当我和科学一起讥笑迷信时,我的心情仍无法释然。我宁愿相信,永远有科学解释不清的事情,比如灵魂。而心存敬畏,未必是无知和胆怯,因为人在大自然之中,实在是孩子。
还有很多声音被我听见:夜晚,在村子小路上走的时候,一只猫头鹰在不远的地方阴阴地叫,像个阴阳怪气的老人;月光下,村庄外的半坡上,一只狐狸的叫声像妇人的啼哭;门前坐着的时候,一只老鸹冷不丁丢下一声飞远,像黑色的预言;黄昏,一只狐狸偷袭进村时,像谁拉了警报,满村的鸡叫;早晨,一只喜鹊在枣树上喳喳地欢叫,这是村子里最受欢迎的声音。我还看见,一头驴子在田野里,突然引颈长吼,像吐出胸间长久积聚的郁闷;一群羊,在山坡,咩咩地你呼我应,青草们仿佛因此翠翠地向外生长;一头牛,火焰一样行走在山里,发出一声长哞,庄严且深沉;从后山上来的风声、从云堆里爆出的雷声,从半天里斜过来的雨声;春天来临时,河流冰裂的声音,很远的地方塌方的声音;从头顶上擦过的像外星人一样的飞机的声音,一颗星星滑过天空陨落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带着某种不为我知或不为人知的信息,可它们却无一例外地被我听见。这说明,它们曾试图让我明白什么,或者通过我已经完成了它们的表达。而我因此在我并不知道中改变了吗?
多年以后,当我生活到城里,我的一只耳朵因为中耳炎失聪,对城市的声音,我也更像是聋子。我偶尔能听到我内心的声音,并和多年前的鸟叫、风声或者狗吠联系起来,因此写一些分行的文字。我还被留下一只耳朵,是不是为了听那个已经遥远的乡村的叫声?
乡村的死亡
羊有一双天使的眼,它看着我时,目光那样纯净。二伯把它从羊圈的羊群里轻易就逮住,他蹲下,抓起它的一条腿,夹在自己的腿弯间,一只手把搪瓷杯子伸在它的腹下,另一只手顺势就挤起它饱胀的奶。两天前,它生了一个羊羔,但是羊羔没站起,死了。在挤奶时,它一点反抗也没有,非常安静地配合。而我看见了它的眼睛:不,不是逆来顺受的,也不是悲哀温柔的,而是澄澈见底、纯净安详的。在喝那杯温热的奶时,我想,它食草,饮泉,前生也许是口衔圣草的仙者。后来,它在山里失足跌落,瘸了一条腿,被隔离在一根电杆旁。我看见它依然安静地吃搬来的树叶、割来的草,我走近它时,它抬起头看我,还是那双眼睛,丝毫看不出忧伤。再后来,它被抬在案上,我那时已满心难过,但只听见它孩子般地叫了一声,再没有声音。它的眼里,一滴泪水都没有,还是那样安详,它是知道自己的生命和命运的,它走得那么安静。
猪电锯般地大叫,撕心裂肺地,扯开嗓子拼尽气力地,充满抗议和坚决不屈地。这是年关,一头猪走到了尽头,它被我的父辈兄长们用绳索费力地拉倒、艰难地抬上案子。整个村庄都是它尖锐的叫声、村庄十里外都是它的叫声。前一天,它还在圈里,自在地掘自己翻了又翻的污泥,我走在它跟前时,它只抬头看了我一眼,就又兀自翻掘。它睡在圈里,从来不望天,它的眼睛大而空洞,它的眼睛里没有云彩,这让许多人认为它的目标在现世。但我觉得,人误会了猪。它有与众不同的梦,它沉浸在自己的梦里,它的梦一定五彩斑斓,不然它不会那么喜于安睡。它吃食时眼睛都会闭起,并发出愉快的进食节奏,那个梦肯定是悠长的,甚至不可打断的。看猪的眼睛会觉得人类没法跟猪沟通,可这怎么不可以理解成猪不屑与人沟通呢?为了梦,它所求太少,对外在的环境要求简陋到无法再简陋。它安睡的姿态更像上帝的作品,人类学不来。那么,它的大叫其实并不是怕死,而是对梦被打断的强烈抗议和对梦的顽强捍卫。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梦?
牛从悬崖边跌了下去,因为拥挤和灌木遮蔽道路后踩空。我听到了一声巨大的轰响,与此同时,我觉得那一瞬时光凝固、万籁俱寂,只有那声“轰隆”的巨响。待我走到它跟前时,它还没有死,艰难地喘着粗气,像一个落难的英雄。父亲急匆匆赶来了,蹲在它的身边,用手抚摸它的头部,就在那一瞬,我看见它的眼泪滚落出来,眼里说不清是留恋、哀伤还是与知心人永别的揪心痛苦。我永远记住了那个眼神和像豆子一样滚出的泪水。与父亲相依为伴十几年的黄牛,是父亲懂它,还是它更懂父亲?但我确信有一种交织的暖流,是友谊、爱、尊重、平等和相互的感恩,甚至远远比这些复杂。在临走的那一刻,它也许等待的就是父亲,它的一生几乎就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父亲就是它最亲的人。它停止了粗重的喘息,躺在那里,再也一动不动。第二天,我看见一群牛在它跌落的地方用腿使劲刨着,掏肝掏肺地嚎叫——不是干裂的,而像来自很深很深的地方。是悲恸、祭奠还是质问?那声音是通向地的、传向天的,甚至穿透宇宙的。我感到电闪雷击般地震惊,感到穿透前胸后背的震撼。许多年了,那声音还历历在耳。但我还是觉得不懂牛的心灵,它的如大山般的坚毅、静默,如大河般的坚韧、深沉,如大风般的昂扬、雄武。它在卧倒时那一声粗重的叹息,它在高原行走时那悠长的沉思,它踩进黄土地时那圣灵般的背影。它的那一行滚热的泪又像硫酸一样蚀进我的身体、血液里。在牛开天掘地的叫声里,有一种更辽远的声音。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看见父亲撇下手中的农具,惊慌失措地跑出院子,这是我从未见过持重的父亲跑步的姿态。我赶快尾随追赶,看到出事的地方已围了一圈人,喊叫声乱作一团。原来大伯在挖土窑洞时塌方了,大伯就埋在土里。大家七手八脚、手忙脚乱地总算把他从土堆里刨出。他满脸、满身裹着黄土,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这时,我的姐姐——他的女儿刚从井路上赶着毛驴驮水往回走,还唱着歌,对于刚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大家把大伯抬在炕上,靠在一摞被子前面,人们轮流呼唤着,但他始终不能被叫醒过来,头直往下磕。最后猛地抽搐了几下,再也不见动静。我在一片哭声中惴惴地离开,仿佛有一个可怕的影子跟在我的背后。
大伯走了,我已确信了这一点。就在昨天,他还斜靠在我家的土炕上,和父亲一起抽烟、说话,还用他宽厚的手摸我的头,他的话我还能听见,他的笑容我也能看见,而明天和以后将再也看不到、听不见。我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和不安。我原来看到的动物的死亡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逼近我的心灵,我第一次感到了危险、惶惑和生命的无常。
我是在黄昏时跑回家的,一路上,我都觉得背后跟个要抓住我的影子,而那个影子是确定的——大伯。我一次都没敢回头,头发直往上竖,生怕他的手落下来,生怕他叫我,并从后面拽住我。
晚上,我坚定地要父亲和我一起睡,并把头藏在被窝里,煤油灯也不许吹灭。但还是紧张得厉害,我觉得我是藏不住的,他一下子就会找到我并把我带走。我使劲地摇父亲,生怕他睡着。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我一眼没合,满脑子都想着大伯临走时的抽搐,那张灰蒙蒙的脸。他的话语和笑声都不再温和,面目也不再和蔼友善,而是狰狞可怕,随时要抓一个小孩跟着他去。而那个小孩必定是我,因为他就跟在我后面。
很长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克服我的恐惧,并半夜半夜失眠。夜间,我不敢迈出院子一步,白天也不敢走村子以外的任何的路,大伯家,更是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并且不论白天晚上,总觉得身后跟着一个影子,而我没有一点勇气去回头看。有一次,在驮水的路上,远远地瞄见了大伯的坟和冷簌簌的花圈。也就在那天,我终于病倒,发烧,虚弱,一遍遍地说胡话……
我为什么如此惧怕死亡?在以后,我多次想过那段惊恐无助的经历。我到底惧怕什么?是大伯的死让我看到了生命巨大的虚无?不对,那会儿还是懵懂的孩子。是恐惧死亡本身的残忍?好像也不是,大伯走时面相并不狰狞。有一点很清楚,我是怕死。那么,这种恐惧应是来源于生命本能,是不能接受生命还没有展开的短暂和死后的空无所寄。那阵子,我感到父亲并不能强大到可以庇护我,可以让我躲过死亡的追击。我感到自己像个软弱无助的孤儿,而死亡无所不在又无比强大。事实上,当我多年以后,再次想起死亡,我同样会感到无比恐惧和万念俱灰。那么,其实并不是生命强大了使我不惧死亡,而是对死亡已经麻木。的确,还有什么比死亡更荒谬更让人恐惧的事情?人类的智慧从来没能解决这个巨大的不安,绝大多数人也只是自欺欺人地遗忘、搁置。倒是孩子,更清醒,更敏感,从而更像生命。
大伯用镢头挖窑洞,也挖倒了自己。他临死时对自己的命运一概不知,他生前也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将飘向何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和大伯一样。但是,不论羊、猪、牛还是其他动物,他们仿佛比人更懂得死亡,比人更懂得命运。
我怎么能像羊一样安详,像猪一样做梦,像牛一样大爱深情?
乡村的过路人
他拄着一根探路的拐杖,一个人独自走在山路上。他要去哪里?那是春日的下午,阳光亮堂,一树一树的花朵就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开放,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一座庙宇,庙宇上空的天瓦蓝瓦蓝,庙宇前一块红布在随风飘扬。他知道这些吗?在放学的路上,我本该是要去摘山杏的,它刚生出来,有酸涩的苦,但又有新鲜果子的爽口。那么,他为什么又让我看见?他以很慢的速度向前移动着,拐杖的速度却飞快。他的头顶,刚飞过一只老鸹,但没有叫。我什么时候已在他经过的路口站了下来,我也是一个孤独的孩子,怀着说不清的惆怅,我是在等他吗?在他经过的时候,他略略停顿了一下,我看见他长长的眉毛在飞快地舞动,一刻不停地。他眼睛的视觉是否就分散在这些飞舞的眉毛里?好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眉毛传导进他的感知里。他不是一个凡人,我当时就这么想,事实上他的头抬得很高,始终面向天空,他的气宇一点不像我平时见到的人,尽管他衣服褴褛。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些眉毛让他看见了另一些事物?他的瞎会不会和他的眉毛有关?我确信,他知道天机,那些眉毛就是导线,而知道天机的人是要瞎的。这么想时,我感到安慰,又有几分敬畏。但他要去哪里?谁在召唤着他?我站在路上,看见他幽灵一样慢慢地走远,转过一个弯,不见。
挑担的货郎走进我家的院子,他的手里摇着拨浪鼓,很快就吸引了全村的孩子。玻璃盖的两个箱子里,尽是些稀奇的小玩意:彩色糖豆豆、各式各样的蝴蝶夹、精巧的风车、造型别致的转笔刀、会唱歌的小玩具、会翻跟头的小人、戴帽子的铅笔,七星瓢虫在抖动的小木盒、嘟嘟吹响的塑料喇叭……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怎么会有那么多新鲜玩意儿。他从哪里来?那个地方肯定是童话王国一样美丽的地方。但是,村子里的孩子叽叽喳喳一番后,没有一个孩子能买得起其中任何一样东西。而父母也都说,看了就行了。那个货郎好像并没有失望,他只请求住下来。我爸爸爽快地答应了,许多孩子都希望住在他家,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我妈妈还特意给他做了面条,我们家招待领导的那种白面条。也许是作为回报,他在第二天临行前,给我喂了一个糖豆,许多孩子都眼巴巴看见他把糖豆确凿无疑地放进我的嘴里。我妈妈站在门口笑盈盈地,像告别一个亲人。货郎还没走远,小伙伴都围过来,不停地问:甜吗?甜吗?那个味道,只有我知道。
村子里来了一个照相的人,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他围定,这件事有人听说过,但还没人见过。他的机子用一块红布盖着,立在我一个爷爷家的院子里。机子对准的背景是北京天安门,那个大家都认识。他拿出一张别人的照片给大家看,天呀!那真是不敢想像的事情:毛主席像就在头顶,而自己分明就坐在天安门前。还是我爷爷聪明,他跟那个照相的商量,给全村人都照,但价格一定要最低,折合成粮食算,由村上的毛驴运送到乡上。照相的人愉快地就答应了,而经我爷爷一倡议,全村人都响应了,大概一张像就是一升豆子,家家都能拿得出。照相的说今天光线不好,就先给我爷爷照一张,其他人明天早晨一大早照。我爷爷高兴得眼睛都笑没了,他搬来一个方凳,坐在“天安门”前,手都不知往哪里搁,摆弄了半天才放好,但脸最终还是僵的。就在照相的掀起红布的一瞬间,我惊然发现框子里我爷爷头朝下、是倒着的!这一发现使我无比惊悚,原来他是巫者!他拉起绳子,捏了一下手里的软皮球,我觉得那一瞬我爷爷的魂魄就被吸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村子里的人像过节似的早早来到我爷爷家,而我爷爷的照片已经洗好,正被争相传看。一点没错,我爷爷“到”了天安门,毛老人家就在他的头顶!但我又为我的发现找到一个确凿证据:我爷爷照片的底片,在脸的部位,是一团血色。吸血鬼!我暗暗想。但村子里的人都争着往板凳上挤,他们的脸上显出幸福的光彩。只有我一个人没照,我找借口说,我长大要到真正的天安门呢!
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他背着个帆布包,手里拿着个硬纸板。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我们村子垴畔的一棵大树下埋头写着什么,见我过来,赶快把纸板反了个面,把一支很别致的铅笔放在纸板背面。他面色清癯,戴个眼镜,穿着一件洗得亮白的的确良衬衫,衬衫兜里,别着一支亮晶晶的钢笔。他问我村子的名字、路的名字,说话像收音机的声音,我都一一告诉了他。我盯着他想,他一定很有学问,要是我的老师就好了。我问他是北京来的吗,他笑了笑摇摇头。他笑的时候非常好看,牙齿洁白,声音清脆。但我确信他从很远的地方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个纸板上写了什么?为什么不给我看?但我不敢再盘问,又想着我长大能像他这个样子就好了。他请我做一件事,帮他的杯子里倒一杯水,我接过杯子,就往家里跑。一路上看那个杯子,玻璃的,亮亮的,干净得一尘不染。回到家,爸爸看见杯子,问我哪来这么好看的杯子?我告诉他刚才遇见的人,他立即说,肯定是个特务。我不明白特务是干什么的,爸爸说就是大坏蛋。还说他肯定是来窃取什么情报,而且有个发报机就安在鞋后跟里。我一点也不以为然,又有点惊奇。我们村会有什么重要情报?不可能!他肯定是好人。这么对爸爸说着,心里已有些忐忑。但无论如何,我得赶快去送杯子,倒了一杯开水后,我惴惴地返回他坐的地方。他又在埋首写着,见我回来,笑眯眯地感谢我,但还是把纸板翻了过去。接过水杯后,他站起身要走。我赶快看了看他的鞋子,没看出什么特别和破绽,是我做梦都想要的那种“黄军鞋”。我鼓足勇气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很快回答我:绘地图的。然后招招手,走了。他走后,我低下头看他脚印的花纹,一道一道,很漂亮。
二牛家来了个画匠,要为他们家的新柜子作画,这在我们村还是头一家。听我爸说二牛的爸爸在山里挖出一个陶罐,里面全是金银财宝。我问二牛罐子里真的有财宝吗?二牛说他什么都没看见,还被他爸打了一巴掌。但二牛家有钱做新柜子,甚至还要给柜子上画画,这说明我爸的话是对的。木匠做柜子的时候,我就去过他家,柜子大呢,光刨花就堆了一地,我和二牛偷着抱了一堆放在磨道上边烧,火欢势得很。在木匠吃饭的时候,我俩还操起推刨试了一下,一推一个卷儿,木头发出清脆的声音,感觉特舒服。我们把墨斗的线长长地拉出来,在木板上绷直,用手指将线一拉一弹,一条直直的线就留下了。在木匠挺着肚子出来的时候,我们早已经逃远。这次画匠来,我又想去看。但柜子在家里,二牛说他妈不让外人进去看。我就一遍遍地探在他家门口,寻求机会。我没看到他们作画,但是见到了画匠:两个人,一个留着长发,一个光头,都衣冠不整。见了人我就没兴趣看画了,我断定二牛家请了两个二流子,不再想起这事。直到有一天,二牛来叫我,说他妈不在,柜子上的画已经画完了,漂亮得不得了。我将信将疑赶快跟着他去。一进门,柜子就在门口摆着,果然了得:一排柜子牡丹绽放,百鸟朝凤,猛虎上山,都光彩夺目、色彩绚丽、栩栩如生。我最喜欢的一幅画了一棵树,一匹马远远地站着。但这幅画在最里面,光线不好。听见我说喜欢这幅画,那个“长头发”赶快过来看我,他凑在我耳边说,只有这一幅是画。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但对他的长头发少了反感,我再看那个光头时,也不觉得难看。
我们村还来过好多人:有一个石匠,声若洪钟,嘴里一边唱一边抡铁锤,他为村上锻石磨,铸石碾,还为虎子家箍石窑。听说,他要是不高兴,就在碾子或磨上偷偷地錾一个小缺口,这个村子就会出不吉利的大事;主家要是伺候不好他,他就会在箍窑时在窑背上放进个纸人,这家就会出人命的事。我因此讨厌那个壮硕的家伙,刚好他也不喜欢孩子,他嫌我们闹,一凑过去就像轰麻雀一样抡起家伙假装打人一样把我们轰走。所以,我只看到他就那样独自一人唱着胡乱的调子干活。好在村子没出大事,虎子家也平安。还有一个风水先生,尖嘴猴腮,包里装着个罗盘,被村里请来看坟地。凡是和死有关的手艺人我一律躲避,但他的那个罗盘着实让我新奇,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像巫术,他怎么就都懂呢?听说,他看过的坟地,一般后代都会出一个县官,但不知他家出了几个?还来过一个算命先生,你只告诉他生辰八字,他就知道你家的大门开的方向、祖坟地的树是什么样子等等。我见他时,他正眯着眼,用手指飞快地掐算,然后一停顿,就告诉你问题的答案。听人说他看过麻衣相、透天记,知道人的前生后世,甚至知道世界的兴衰灾福,但他不知来我们小村干什么?最可怖的是巫神,坐在炕上好端端一个人突然一个跟头翻下地,唱起曲子来。彼时必是晚上,香火点起,黄裱燃了一遍又一遍,气氛已让我紧张。只见他暴跳起来,拎起锵锵作响的“三山刀”冲进院子,用事先准备好的盛灶灰的碗四处乱打,而分明,他在打鬼。这让我毛骨悚然,原来鬼就在村子里!最让我震惊的是他让助手用麻纸塞满嘴,又用鸡血和成的泥封上鼻子、嘴巴,然后绑在一扇门板上,埋进一个事先挖好的穴里。穴里只有一盆凉水、两只活鸡陪伴,待到时辰,他就在地下蹬脚边事先连接好的木杆子,在外面守候的人听见杆子上的铃铛作响,就赶快将人挖出来。我一直奇怪他在地下怎么呼吸着,十几个小时呢!待松绑,掏出嘴里的纸,他痛饮一杯凉水就清醒过来,随后在病人身体上方一番舞蹈和念叨,“招魂”就完成了。以后的许多天,我都处在恐惧中,但他的唱调被许多人学会并传唱,我也低声试了试。再后来,听说我们村我的一个叔叔,有一天也是突然一个跟头从一个土坡上翻下来,倒地就唱。我不知道他治好了几个人的病,但是他在四十岁时就死了,心脏病。
当然,最亲切、记忆最深的还是我的七叔。他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是我们村唯一梳偏分头的人、唯一镶牙的人。其实也只有他配,其他人留偏分头想必就不伦不类。我们村离学校二里地,有一半多路可以骑自行车,但先要推着车爬半道陡坡。其实走路也许更轻松,但他是老师,骑自行车就洋气,就有优越感,这是我想的。上坡时,自然有人愿意帮他从后面推,我就是最积极的一个。这样,等到下坡时,我就会被允许坐到后座,在山路上风驰电掣,飞一般的感觉。他的板书写得真好,龙飞凤舞,连写字的姿势也好看。他给我们念课文时,那颗镶了的牙就露出来。他掷粉笔头,精准如导弹,百发百中,谁要走神或打瞌睡,一准会被他的炮弹击中。他还会弹三弦、吹笛子。放学后,他回到家,往园子里一坐,满村子就都是他的乐声。而村子里的鸡也不叫了,牲畜都安静下来,仿佛都沉浸在他的音乐中。最风光的还要属过年,全村的对联都由他一人包了,大家拿上烟,带过滤嘴的,到他家排队等候。那时,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充满自豪感。他的笔一顿一挫,如龙游走,喝彩不断。而每写完一幅字,他也会用一只手扶住拿笔的胳膊,静静欣赏一下,偏分头看上去更有风度。当满村的窗棂上都添上他写的对联后,他面前的过滤嘴香烟也可以收一盘子。而这时他走在村子的路上,头也会抬得很高……那时,我所有的梦想就是将来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但我小学还没毕业,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学生大多都回家放牛种地去了,学校只好解散,民办教师的他便只好回家务农。而我幸运地被父亲转入乡上上学,离开了我的村庄和学校。多年以后,当我在外上学回家过年时,才知道他在山西的私人煤矿里挖煤,因瓦斯爆炸身亡,留下了七婶和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找到了他的坟头,孤零零一座,坟前是一片空地,近处有一棵树,身子黑黑,枝丫空疏,一只乌鸦落在上面,等候我的祭品。我点燃了一支过滤嘴香烟,仿佛又看到了他的那颗镶了的牙。回到村上到他家,他住过的屋子好像比以前更低更暗了,那把三弦还挂在墙上。那年村上的对联,都由我写,他们说,我的字,很像七叔写的……
张怀帆,作家,现居西安。主要著作有诗集《一个人的小镇》、散文集《提着萤灯行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