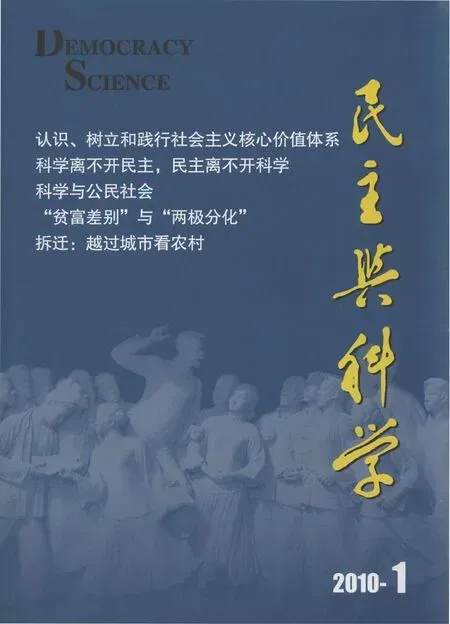“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
■邵道生
“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
■邵道生
邓小平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第229页)他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第139页)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警告?显然是针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现象而去的。
但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似乎生活在真空里一样,认为我国目前只存在“贫富差别”,不存在“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他们说:“必须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有一个根本的定性的认识,它绝不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而是共同提高后的差距”;有的“主流经济学家”说西方经济学的基尼系数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有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还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不是拉大了,是缩小了……
这是一很有意思的、而且是值得研究讨论的观点。
(一)不要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现在有些“学问家”也不看看是什么时代了,还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譬如说,究竟是谁规定了“两极分化”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又是谁规定了在社会主义(尤其是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便是有哪一位“老祖宗”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能不能修改?其实,从社会学的概念来说,“贫富差别”是一个大概念,它“差别”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差别”到没有节制的发展,就是“两极分化”。所以“两极分化”实际上“贫富差别”中的一种,是“贫富差别”极端的表现,在“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这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鸿沟”,更不必用“阶级标签法”去标定哪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哪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再也不能用过去阶级斗争用惯了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来套用现在的一切,凡是丑陋的都是资本主义的,都是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我们社会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有这样一批“理论家”,他们并不是钻到火热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去研究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是用刻板的、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的概念去封杀各种新现象、新问题,把任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放到现有的天平中去衡量,去评价,用已有的理论去解释所有的新情况、新特点。譬如,有一段时间有的“理论家”就禁止用“失业”这一概念,而只准用“待业”,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社会主义国家只存在“待业”的现象。
表面上看起来,“理论家”们玩这种“概念游戏”是在“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党性崇高”的表现,而实际上呢?它阻止了人们进一步去研究、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譬如,过去禁止“失业”概念的应用对“待业”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什么忙都帮不了;而现在“失业”这个概念的“恢复”应用,也损害不了我们社会主义哪怕是半根的汗毛。说到底,这是根深蒂固的“左”字在作怪。就以“两极分化”来说,难道提出在我们社会里出现或存在“两极分化”的人,硬是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过不去”?硬是要出我们社会制度的“洋相”?恐怕不能这样说。相反地,那些忧心忡忡地提出“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人,并不赞同过去的“绝对平均化”导致“绝对贫穷化”的做法,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保持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为社会注入一点活力和生气,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心至少提醒人们思考以下这些问题: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超过了50%、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低收入国家时,有哪些人是富得特别快?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他们的“富”对整个社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劫富济贫”的措施和方法不让这些“为富不仁者”富起来?……我想,对这些问题多想一想、多提高一点警惕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二)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应该看到目前已经有这个“苗头”,就以专门描述财富差距“集中度”的基尼系数(它是指1%的人口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重,低于0.3属过于均等,高于0.4则属差距过大,超过0.45属差距过大,若基尼系数为0.5,则说明1%的人口占有了50%的社会财富)来说,1980年是 0.3左右,1988年是 0.382,1994年是0.434,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到0.456,1998年比1980年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1997年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表明,占调查户8.7%的富裕家庭占有60%的金融资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贫富差距也拉大了。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迅速增大,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目前已超过0.45。”“20年间,中国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跨入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速度之快世界上少有。”(《财经》2002年5月)国家计委的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40个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的国家与地区之一(有人则认为已经接近了国际警戒线)。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财政部最近给出的关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据中国民盟桂林市委刘桂萍先生指出:“这些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不同渠道给出的数据则更为惊人。比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由此可见,中国比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更严重。”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为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难度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些数据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它至少说明处于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贫富差别”是在扩大之中,它至少说明在剧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些地区已经出现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决不是耸人听闻),所以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三)怎样分析“两极分化”中的另一极——“先富裕起来的人”?
在“先富裕起来的人”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致富的人群,如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工程师,像已经站在信息产业制高点的CEO,像巩俐、伏明霞这样的大牌文艺界、体育界、影视界的明星……对这样的人,人们什么话都没说的,他们靠的是本人才能、本领致富,能说什么?他们在自己富的时候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国家积累了财富,也为他人的富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所以他们富起来是应该的。遗憾的是在“先富裕起来的人”中还有一群“暴富者”,靠的是权力,靠的是贪污贿赂,靠的是官商勾结,靠的是偷税漏税,靠的走私贩毒,靠的是贩卖人口、贩卖文物,靠的是机会不平等……总之,他们是一批靠“趁共产党还没有醒时狠狠地捞了一大把”的人,他们的富是坑了国家,是有更多的人走向了贫穷,是为富不仁。著名的贪官成克杰、胡长青,远华走私案中的赖昌星和湛江走私案的石油走私大王等,他们的财富何止是千万、亿万,而是几十亿、上百亿。这样的人是一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腐败分子、寄生虫、剥削者,是社会的蛀虫。有人会说,这是极少数,我也不反对,与十几亿中国人相比,的确是极少数,然而从这一“暴富群体”或“暴富阶层”所侵占的财富来说,则决不是用“极少数”这个词所能说明的。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研究,仅90年代后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数字是够触目惊心的了。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依靠腐败、欺诈、权钱交易等恶劣手段难道就不是“阶级斗争现象”?而必须指出的是,这部分恰恰是“先富裕起来的人”中的最重要组成,“暴富群体”或“暴富阶层”的出现,的确是“两极分化”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两极分化”中的“贫困一极”是怎么出来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两极分化”中的“贫困一极”是怎么出来的呢?原因很复杂,据我的研究“贫困一极”主要是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
一是被腐败现象“腐”出来的。在谈及中国的“两极分化”时我始终不忘的是以下三种“问题改革”:一是经过“国企改制”的“改革”我国社会结构中一下子“改”出了5500万失业工人;二是“农村圈地运动”的“圈地”一下子“圈”出了4000余万的“三无农民”;三是“城市拆迁运动”的“野蛮拆迁”一下子“拆”出了没有统计数字、但是数量惊人的无房城市居民……就这三种“问题改革”的结果来说,若是三口人为一家,一二亿挣扎在“贫困线”、“温饱线”的“弱势群体”就出来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而形成了“稳定的洋葱头”(或曰“金字塔型”)形态。谁之“功”?当然是腐败之“功”,不少“有权人”和“有钱人”靠了这三种“问题改革”变成了“两极分化”中的“富豪一极”。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如果80年代农村开始的改革还可以说是双赢的话,现在的改革,已经是到了一部分人的获利,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地步了。
二是被分配不公“分配”出来的。中国的分配很不合理啊!譬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在最近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中指出,目前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都认为工人、农民、农民工的获益很少,评价都排在最后三位。现在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普遍偏低。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的上限仅为平均工资的43%左右,平均水平则明显低于40%的下限。也就是说,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社科院报告: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但27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依然维持在美国的人均工资水平的4%,而当初与中国差距并不大的日本,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用了30年。”(吴晓宁:两极分化成因何在)想一想,如此低的工资怎能去“对付”难以承受的物价飞速上涨?怎能去“对付”越来越涨得离谱的高学费、高房价、高药费?“新的三座大山”是谁喊出来的?“富豪一极”是不会喊的,喊叫最重的是“贫困一极”。这个“喊”是有道理的,“不喊”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山西大同考察时说:“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新华网》2009年12月30日)现在经济是发展了,但是处于中国最低层的工人、农民却没有“过上好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贫困人口。”(《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9日)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过去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没有“过上好日子”,而当现在整个社会奔向“小康”时,这个没有“过上好日子”的标准就应该是奔向“小康社会”中的“贫困标准”。什么叫与时俱进?大概这就叫与时俱进。
(五)不要忘掉邓小平晚年的警告!
纵观世界社会发展史,发展永远是与问题相伴随的,没有出现问题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也是如此。所以,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的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是不赞成、不允许“两极分化”的出现,我们是鼓励“共同富裕”的,我们所主张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鼓励勤劳致富、知识致富、贡献致富,而不是靠腐败、靠官商勾结的“暴富”。但是,我们的不赞成、不允许不等于它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规定”只是一个“理论的假定”或一个“美好的社会期望”,它不可能也决不能“硬性规定”某种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或不产生。就以腐败来说,它的产生显然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格格不入的,它目前泛滥的严重程度显然是我们的社会所不希望的,但是,我们能“规定”或“禁止”腐败现象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发生或发展吗?这叫什么?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想,在思考“两极分化”问题上,也应该是这种思想方法去认识,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不能只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那种粉饰太平、会导致社会“安乐死”的错误思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