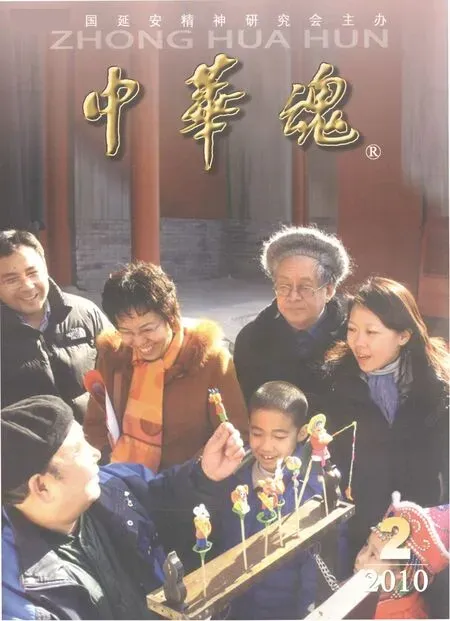吐胸中块垒掀笔底波澜
——读郑伯农《诗词与诗论》中的诗词
文陈辽
吐胸中块垒掀笔底波澜
——读郑伯农《诗词与诗论》中的诗词
文陈辽
当今诗歌领域,新诗和旧体诗词二分天下。写作旧体诗词的人数可能比写作新诗的人还要多。据我所知,江苏就有78个诗词学会,3500多个会员。他们一年间正式出版的和自费出版的诗词,大大超过了新诗在江苏的出版数量。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写作旧体诗词的诗人中,既有对旧体诗词素有造诣的诗人,也有写新诗已经出了名的诗人,更多的是学习写作旧体诗词并取得成就的新诗人。不曾想到,本来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的郑伯农同志,继出版《赠友人》旧体诗词集后,又在2009年7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诗词与诗论》,其中的“诗词”多为旧体诗词,而“诗论”论说的多半是有关旧体诗词的新见。原是文论家的郑伯农的旧体诗词创作与旁人的旧体诗词创作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原来,他将诗人和理论家“合二而一”,以旧体诗词作为他倾吐胸中块垒的载体,因此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掀笔底波澜的诗歌景观。
郑伯农的胸中块垒之一,是对现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的强烈的憎,这是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很少有人涉及的。在《满江红》中,他一腔愤怒,剑指“霸主”:“恃强凌弱,劫贫济富。颠覆制裁伸黑手,穷兵赎武逞凶酷”;“怨洒五洲,只争得普天动怒。”对“霸主”的“霸权主义”该怎么办?郑伯农的回答是:“附凤攀龙留耻辱,中华自古重铮骨。对熊熊烽火染寰球,勤温故。”“霸主”入侵伊拉克四年后,郑伯农又在《大国攻占伊拉克四周年》中揭露“大国”:“维和旗下灭公理,反恐声中树霸权”;“百万平民沉血海,一方热土化屠坛”;他预测:“不信灾星能永耀,乌啼月落看明天。”伊拉克人民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报载,“霸主”以伊拉克政府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但调查多年,始终未找到证据。结果调查人员发现,“100瓶装有炭疽病菌和其他危险病菌的玻璃瓶”,就在美国某“军事基地的一个地下室内”。郑伯农读了这一报道,不由义愤填膺,写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藏在哪里?》一诗,以怒涛般的诗句,谴责“霸主”:“先动武,后举证,/哪怕证据全无,/也要杀个家破人亡。/这就是世界霸主的逻辑。”最后,真相大白:“原来这个令人揪心的物件,/就在山姆大叔的后院里。/就在五角大楼的兵工厂里。”郑伯农将怒火倾泻在“霸主”身上的诗词,表达了世界民众的心声。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倒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西方国家兴高采烈,也有部分国人对此无动于衷。郑伯农的胸中块垒之二,则是对这一悲剧事件进行反思。他的反思结果,形诸笔墨,诗词中的波澜则卷向叶利钦、瓦文萨这类人:“易帜分邦入窘途,连年休克国荒芜”,“青史难逃众口诛”。(《祭叶利钦》)“彼岸深宫一线牵,狂潮送尔上青天。无情岁月鉴真伪,风卷尘埃下夕烟。”(《闻瓦文萨回老家》)在《苏共亡党十周年》一诗中,郑伯农作了更深入的反思,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倒台,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在朝臣变,风来燕雀嚣。”不少“朝臣”像叶利钦之流“变”了,歪风一来,他们嚣张了;“昏吏害非浅,叛徒罪更高。”二是因为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镰斧弃蓬蒿”;三是因为苏共的腐败愈演愈烈。“决堤迎祸水,放手刮民膏”。两首五言诗,寥寥四十字,却道出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主因,令人惊悚,发人深省。笔底波澜,将这些“昏吏”、“叛徒”卷到了民众愤怒的汪潮。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国际地位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有目共睹,举世称羡。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两种不应有的倾向:一是完全肯定改革开放中的一切,谁要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谁就是否定改革开放;二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郑伯农反对这两种倾向。他热诚拥护改革开放,《诗词》中有数十首诗词歌颂了、展示了、再现了改革开放的重大业绩;但对改革大潮中泛起的沉渣,他也予以尖锐针砭。这又是郑伯农的另一胸中块垒。他抨击公款吃喝:“山珍海味何时了,豪宴知多少。小楼昨夜又接风,公仆轻歌曼舞酒香中。”(《虞美人·有感于公款吃喝》)他严厉反对赌博风:“有权公款填充,无权家破业空。何日天公抖擞,重开朗朗世风。”(《清平乐·有感于赌博风》)2003年“九一八”前夕,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接待了来自日本的庞大“买春团”,团员有380余人。酒店竟组织了500名陪侍女郎,供其淫乐。郑伯农看到这一媒体报道后,拍案而起,写下《绝句三首》,痛斥酒店此举:“人伦国格弃尘埃”,“国耻今凭大款彰”;“雉馆青楼曾绝踪,谁播孽种满寰中。”矿难死人之多,中国第一。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为此多次采取措施,但矿难依然不绝。郑伯农以为,矿难之绵延不断,关键在于一些地方官只要所谓“政绩”,只要GDP(国内生产总值),而置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忍将骨血换财宝,发迹升官不觉羞?”(《又闻矿难》)再就是,一些地方,将矿山私有化;某些“公仆”,又挟权经商:“矿山衮衮化私产,公仆纷纷变股东。”(《哀矿难》)如此情况下,矿难怎能不接连不断地发生呢?郑伯农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他对于文艺界出现的怪现象,本着一个党员文艺工作者的良心,本着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总是彻底揭露,不留情面:有人“向钱看”,“直把文房当票房”;有人在评奖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虎啸龙吟谁脱颖,考官乃是状元郎。”有人专写床上戏,“窃玉偷香床上功,春情抒罢画春宫。”还有人对杀妻后又自杀的某诗人大唱赞歌:“杀妻自缢是诗星,血迹凭添显赫名。人命关天谁管得,满城风雨祭幽灵。”(《戏为六绝句》)对于那些不讲民族气节、一味颠倒大是大非的事件,郑伯农更是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2006年,一个抗日战争时期附逆的老文人离世,某些报章荧屏推出大量悼念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郑伯农在《杂诗二首》中写道:“新民会里寻常见,膏药旗前几度忙”;“媒体不知亡国恨,颂歌满纸吊狐獐。”2007年11月—12月,中等以上的城市热映《色戒》。但那是一部美化汉奸、诬蔑爱国志士的坏影片。只因得了某个外国电影节的奖项,便被捧上了天。郑伯农的胸中块垒,益加一吐为快。他在《看〈色戒〉》两诗中痛斥该影片:“人情魔力大无边,直令英雄爱汉奸。为国捐躯魂未散,谁将污水泼灵前。”“扬邪好去讨金奖,宣欲方能占票房。偌大文坛多异景,卖灵卖肉炒糟糠。”在当时对《色戒》的一片叫好声中,郑伯农是以诗词带头对《色戒》进行批判的文艺先行者。不久,《色戒》的反动性终于被揭穿,《色戒》热也终于冷下来了。
就这样,郑伯农的三大块垒,都化作了笔底波澜,伸张了正气,打击了邪恶,给人民大众进行了生动的、形象的、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教育。郑伯农在诗词创作中能够这样做,并非偶然。从他的一些致友人的诗词中,我们看到,他敬重的是“拍案鬼狐敛,挥毫泾渭分。”(《寄吴奔星同志》);是“板荡识忠言,疾风知劲草”。(《望海潮·哭别程代熙同志》);是“耄耋犹怀忧国志,登高放眼看沧桑。”(《读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序〉》)是“壮士犹歌抗敌曲,九州唱遍《自由神》。”(《破阵子·悼吕骥老院长》)是“文海有缘增浩气,壮夫岂肯耽风月。”(《满江红·读〈国家干部〉寄张平》)是“雷鸣电闪一声吼,浩气长留天地间。”(《王震赞》)郑伯农的诗词,正是对这些革命前辈、革命友人、革命文艺战士优长的继承和发扬!
难得的是,伯农的吐胸中块垒、掀笔底波澜之作,不但正气凛然,浩气盎然,而且正气中有诗味,浩气中有境界。它们基本上遵守旧体诗词的格律,但出于艺术内容的需要,有时又有所突破,一切都以能否内蕴诗味、中含境界为创作原则。郑伯农今年七十有二,但老当益壮,老有所为,我希望他于老年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执笔撰写理论文章的同时,继续撰写旧体诗词,对广大读者的思想启迪、认识现实、审美享受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