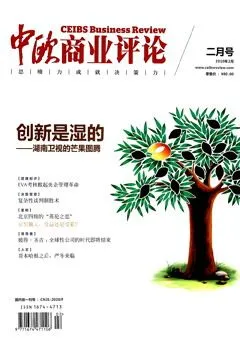哥本哈根之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到来之快、对全球传统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之复杂也许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问壁垒的破解、欧洲普世主义气候、王张的日益汹涌,都在暗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如何融入全球气候民,王,恐怕才是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资源空间的关键。新的开始,既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后的无奈结语,也是国际环境组织的愤怒呼喊。
事实上,就在令会场内外代表和抗议者精疲力竭、犹如无尽头马拉松式的哥本哈根会议结束之后几周,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征兆已经一幕幕呈现出来,无论大自然还是国际政治,仿佛“后天”已经提早到来:在无果而终的哥本哈根之后,一切都显得太迟,严冬已经降临。
失败与冲突
尽管许多中文媒体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不遗余力地为大会结果唱赞美歌,与全球媒体的失望形成鲜明反差,但是,只要将大会最终的寥寥几页政治声明与会前国际社会普遍期望达成的约束性文件相比,本次第15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失败昭然若揭,是任何言辞都无法掩饰的。
没有达成约束性协议,就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加速,气候变暖的趋势将继续恶化,留给世人应对危机及早转型经济与社会体制的时间越来越少。而随着自然灾害和治理危机的加剧,未来的全球气候政治也将充满紧张和冲突,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核心问题。
后哥本哈根时代,也是一个“后京都议定书”的时代。在2009年12月18日到19日的漫长黑夜里,在《京都议定书》终止前3年,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到来了。在遍及全球的种种异象灾害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冲突、不确定的全球气候政治格局正在形成。
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划分原则和现实壁垒悄然瓦解。将全球气候变化缔约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负有承担减排义务而后者不承担,是《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主体原则,也是中国立场的核心。但在哥本哈根会议1 3天进程中,气候变化受害国和倡导国的立场更趋激进,要求抛弃过时的“京都议定书原则”的呼声高涨,“基础国家”(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四国,英文首写字母组合为BASIC)的特殊责任成为焦点。
本次哥本哈根会议规模巨大却冗长耗入且无收获,一向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议程甚至会场之外,不能不说是划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
当北京迎来半个世纪以来最冷的寒冬,欧洲和北美暴雪狂飙,如果依旧避免谈论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悲剧性结局就显得过于虚伪了。这是“一个过时的“《京都议定书》原则”的恶果。不仅此,恰恰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之后的十余年间,全球碳排放不仅没有得到遏止,而且翻番性地增长,足以证明在这一划分原则基础上派生的《京都议定书》另外两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限额-碳交易原则”的失败。
因此,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京都议定书》失败的继续。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 s)将全球气候变化归结为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民主的失败,再精准不过了。
变化与新政
哥本哈根会议的交流本身给予了所有国家和组织一次机会,能够从中发现和表达自身利益,世人得以正视气候变化的迫切性,后哥本哈根格局也在13天的漫长博弈中孕育。
首先,最易受气候变化伤害的小岛国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对气候变暖的怀疑论调、对围绕补偿额度多少的争吵、对什么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喋喋不休再也无法忍受。来自图瓦卢等小岛国家的代表要求,当务之急是将防止气候变暖的承诺控制在1.5℃,而不是2℃。即使2℃,对小岛和非洲国家来说也是不可承受之轻。他们的声音首先打破了所谓发展中国家铁板一块的神话。
据世界银行估计,气候变化效应的75%~80%最终将落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身上,也就是干旱、洪水引起的饥荒、内乱和瘟疫。迅速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变暖,是所有地球国家的共同责任。但是,会议结果的最大受害者却是广大发展zC2Kfvvysh3EeZFU4AZQFg==中国家,他们未能从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及时获得3年过渡期的援助。
其次,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半程,新兴经济体的排放和减排责任逐渐成为焦点,取代了前一周的话语主题——气候正义问题。从“77国集团”和所谓“发展中国家”阵营内,包括“基础国家”主要成员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站了出来,表示愿意主动承担减排责任和援助义务,打破了人为却过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划分。作为美国之外的排放主体,新兴经济体的排放增加量成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主要部分,如果不承担相应责任,显然无法达成气候变化控制在2℃的目标。修改《京都议定书》的过时原则,将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减排责任反映到新的公约之中,迅速成为会议共识。
巴西总统卢拉的立场代表了这一共识。他一再表示,巴西将控制亚马逊森林的“去森林化”趋势,继续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且愿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更理解和支持美国国务9即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体系透明化的主张,反对大会仅以简单的“政治声明”结束的形式。
韩国总统李明博也表示愿意由韩国主办2012年第18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为推动气候政治做出贡献。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立场宣示,立即受到许多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赞扬,卢拉更被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称赞为“展现了全球领袖”的风范。
最后,本次大会的推动者、全球气候政治的领导者——欧洲国家,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最为失望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会议最后的漫长一夜,以“基础国家”为主的密室会议中,欧洲代表被排除在外;在中国代表声称将“自主减排”的同时,欧洲国家对大会最后声明拒绝将欧洲的“自主减排目标”列入文本感到极其不可思议。
这一切,只能强化欧洲早先时候提出的“全球气候新政”方案,即仿效全球金融危机治理模式,建立强有力的气候治理模式,结束全球气候政治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也是大会前流传的“丹麦文本”的主要精神。因此,这份欧洲近年来流行的普世主义的气候治理版本,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视为主权威胁并不奇怪。大会无果而终,无疑是欧洲多年来试图借气候政治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道路上的一次严重挫折。
但是环境/气候政治在欧洲内部已经真正“超越左和右”成为共识,将碳排放管理作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公共议题,超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鸿沟,建立全球团结经济乃至全球民主政治的基础,可能最终解决后冷战时代全球政治的全球化病症和意识形态真空。
至此,虽然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几乎让所有人失望,与中国代表团解振华“让所有人快乐”的承诺如南辕北辙,但可以说,后哥本哈根会议的全球气候政治的新格局已经出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悄然瓦解。
在欧盟之后,一向保守的美国有多名政界要人多次表达,美国的内部政治将不再会是减排障碍,将与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一道,重新成为全球气候政治的领袖。巴西和德国等国早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加速改革联合国的呼声再度高涨。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因其单独提出每年100亿美元援助并主动提高到150亿美元的姿态,大大增强了影响力。对会议最为失望的全球环境和正义非政府组织也发誓,哥本哈根是一个起点,他们将开展更为猛烈的行动,从碳排放大国内部的公民社会人手谋求变化。哥本哈根的失败促使全球气候政治主体正在重新凝聚共识。
挑战与机会
会议之前,如笔者的多篇评论早已指出,哥本哈根将是一个新型国际政治的舞台,国际社会的聚光灯将紧紧打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身上。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决定着会议的成败和气候变化的未来。如果没有最大碳排放国的参与合作,哥本哈根会议就不会产生期望性结果。
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夜,在透明度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愿意进行减排信息的“志愿交换”,为避免大会的彻底失败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但与各国对中国“可以做得更多”的期望相比,不能不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压力。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全球气候政治趋势以及如何切实推动国内减排转型,特别是在接受还是拒绝国际社会对排放“透明度”要求的选择、是否接受全球气候政治呼之欲出的世界政府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削弱,将是未来一年内,墨西哥会议之前,中国政府与社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国际挑战。
只是这一挑战来临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一些保守僵化人士的估计。在达成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变化公约之前,几乎每一天都是“哥本哈根”。会后几周,随着北半球大雪降临、南极冰川融化加剧,前述新全球气候政治格局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现实外交。
更准确地说,外交报复接踵而至。欧盟与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陡然增加:欧盟12月22日通过了延长对中国鞋征收反倾销税15个月的决定;在轮胎反倾销案后,1月6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钢丝层板征收最高达289%的反倾销税。同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了美国对台军售案,除了稍早通过的黑鹰直升机案,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Ⅲ型”防空导弹。这一计划大大出乎中方学者和军界的意料,显示其背后的政治考量。
气候变化的共识不仅受到世界政治家们的认可,也正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变革之快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伦敦的新能源金融公司(NEF)预计,2010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并未受到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太多的影响,将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全球的企业和政府投资将达2000亿美元,相比2009年的1300亿美元上升将近50%,也超过2008年的1550亿美元投资规模。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到来之快、对全球传统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之复杂也许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壁垒的破解、欧洲普世主义气候主张的日益汹涌,都在暗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其中,中国承诺的未来两年220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计划,相当程度上安慰了一度失望的欧洲和北美的清洁能源企业,特别是反应堆生产企业和垃圾焚烧与发电技术企业。承诺“自主减排”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由此产生的诱导需求的规模极其巨大,不仅包括清洁煤技术、核电生产、垃圾处理,也包括整个电网的智能化改造,后者已经成为中国大规模应用风能和太阳能的瓶颈。
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气候政治正在酝酿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无关石油而关乎铀。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连续布局,与加蓬、纳米比亚和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铀矿合作协议之后,世界铀燃料市场开始面临新的紧张。德国政府已于去年正式立法,改变了放弃20余年的核电政策,开始重新建设和发展核电。这一政策转向得到了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环保组织的支持,一向反对核电的绿色和平组织也改弦易辙,支持发展零碳排放的核电。印度政府则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搜索铀矿资源,与中国展开争夺。有限的世界氧化铀年产量将很快就难以满足暴增的核电需求。
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快堆技术(中子反应堆——编者注)和美俄两国日前达成的核武器裁军。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再度提出削减核武器,这一建议为美国核武库的武器级铀转化为民用核燃料打开了大门,为医保改革计划成功通过之后新一轮减排计划埋下了关键伏笔。但也因此,美国和欧洲将继续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上占据制高点,从而继续牵制中国的能源和外交。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到来之快、对全球传统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之复杂也许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壁垒的破解、欧洲普世主义气候主张的日益汹涌,都在暗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如何融入全球气候民主,恐怕才是决定中国国际地位和资源空间的关键。
作为碳排放量仍在持续增长的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2010年的气候压力已经像铁幕一样压来。在对2010年年底墨西哥第16轮气候变化会议上提出确定承诺之前,中国必须在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否则将难以应对全球气候政治的众多变化。在减排问题上,中国企业界也应该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