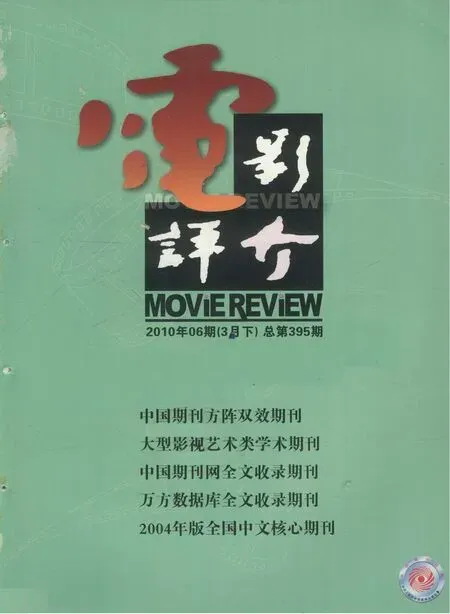浅析《风和日丽》中无法释放的“恋父情结”
艾伟似乎钟情写作成长小说,尤其倾心于讲述男孩的故事,而父与子的原形又是经常表现的母题。近作《风和日丽》是其又一部成长小说,不同的是,这是一部讲述女孩成长历程的长篇小说。
小说中,艾伟细致入微地传达了主人公在成长历程中面临的种种精神之痛。杨小翼的生父是战争年代中赫赫有名的尹泽桂将军,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他被迫抛弃了杨小翼和她的母亲杨泸。“私生女”的称号让幼小的杨小翼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好奇与忧郁,她从五岁开始就不停地追寻自己的身世和血缘,穷其一生来寻找和等待父亲,为此一生命途多舛,在亲情、爱情和婚姻生活中遭受种种痛苦,却始终没有与生父正式相认。父女之间的纠缠与冲突,杨小翼成长历程中铭刻的父亲情结以及这一情结给她造成的成长创伤贯穿了整部小说,可以说,“恋父情结”是本文所凸显出来的重要母题。
弗洛伊德将“恋父情结”称为“厄勒克特拉情结”,其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女儿厄勒克特拉因母亲与其情人谋杀了她的父亲,故决心替父报仇,与其兄弟杀死了母亲。弗洛伊德借此来说明儿童性心理的特征,恋父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每个女孩在她童年和少年时,对父亲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种崇拜感,但是大部分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恋父情结慢慢地会转移,会投射到应该和她在一起的异性身上,而另一些无法淡化这种情结的人便会形成心理暗疾。女性在幼年时就能隐约体会到父亲在家中崇高的威望,他不仅是一家之主和权威,而且“家庭是通过他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他是那广大、艰难和不可思议的冒险世界的化身,是超越的象征,是上帝。这就是女孩子在父亲那高高把她举起的有力臂膀中,在他那她紧紧依偎的坚实骨架中,所具体感受到的。”[1]因此,父亲对女儿的态度关系到女性一生对自己的评价,父亲的行为方式也左右着女性对异性的最初认识。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如果父亲有喜爱女儿的表示,她就会认为从中得到自身存在的极为有力的证据;这样她就有了其他女孩很难具有的优点;她可以藉此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她或许一生都在极力追求那种失去充实和宁静的状态。”[2]
杨小翼不停地“探寻其中之谜”,甚至去搜索、推测可能是“爸爸”的人。刘云石的出现让她“相信那就是爸爸”。父亲的缺席使她比同龄人更强烈地渴望父爱。刘伯伯的形象让杨小翼一厢情愿地不断强化自己相信生父就是他,这使存在于杨小翼身上的恋父情结开始由潜意识向意识转变,出现“崇父”、“恋父”的倾向。所以,当她听到妈妈和刘伯伯的传闻时,“内心充满骄傲”;当她撞见妈妈和李医生的私情时,对妈妈充满轻蔑、憎恨,对刘伯伯满怀同情。
后来杨小翼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并见到了生父。酷似母亲杨泸的杨小翼引起了将军的注意,将军对她表现出难得的温柔和热情,这让她“有了做女儿的感觉”。但当杨小翼装扮成母亲的样子站在将军面前公开真相时,却遭到了生父的冷酷否认和拒绝。 “寻父”的失败让她“深切地感受到被遗弃的伤痛”,转向“恨父”、“憎父”。尹南方的瘫痪让她感到自己“罪不容赦”。所有的爱和恨加深了她的“自我怜悯和深重的负罪感”。
西蒙•波伏娃认为:“要是女儿没能获得父爱,她或许终其一生都会觉得自己有罪,应受到惩罚;也有可能会在另外的地方寻求评价,而对父亲采取冷漠进而敌对的态度。”[3]《圣经》中记述:上帝发现亚当与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后,要他们为此受到惩罚。这是上帝给人的一种原罪,而生儿育女、听从夫命则是上帝给予女性特有的原罪,这也许是女人最初关于原罪的记忆。“古往今来,无论中外,自母系过渡到父系之后,男性就开始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拥有了表达自身的话语优先权。由此便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甚而认为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是女人份内的职责,男尊女卑的意识也日渐牢固。这种影响已内化于心,代代相传,不仅男人这么认为,女人也这么认为。”[4]杨小翼是母亲未婚先孕生下的私生女,作为天主教徒,这是一件违背教义的有罪的事。杨小翼带着原罪出生,生父的否认和尹南方的悲剧让她认为自己才是所有罪过的源头。来到广安后,杨小翼带着赎罪的心情找到少年时曾被她伤害的初恋对象伍思岷。带着负罪感和“母性的情怀”,杨小翼决定补偿伍家。同时,她重复做着“尹南方坠落永城”的噩梦,“梦是弗洛伊德揭示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基本途径”,是“了解无意识的康庄大道”。[5]这折射出杨小翼内心的原罪意识和因被父亲否决而使自我求得满足的愿望受挫后的负罪感。嫁入伍家后,杨小翼的不幸又重新开始。最终这场婚姻以离婚收场。她又一次被彻底抛弃了,她的苦心付出不但没能赎罪,反而让她觉得自己的“罪过”加深了。
无父无夫无子,这一切让杨小翼身心疲惫,痛苦不堪。此时的她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渴望被爱,渴望找到心灵的港湾,渴望有一位刚强勇猛的男性能保护她、疼爱她。她内心透出的恋父情结使她所渴望的恋人不再是伍思岷之类年轻帅气,具有野心和个性的人,而是年纪颇长,沉稳内敛,人生阅历丰富,融丈夫与父兄为一体的男子,如刘世军。刘世军始终像父亲一样照顾她,包容她,保护她。 “在他的抚摸中,她的心变得非常宁静,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孩子,在父亲的怀抱中”。此时的杨小翼把对父爱的渴求自然而然地转嫁到与之最为亲近的刘世军身上。她把父亲的形象特质与伴侣的外化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潜意识中父亲形象在意识中的一种曲折表达。杨小翼缺失的父爱在刘世军身上得到了补偿。但是从伦理道德和良心上讲,他们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而分手又使两人痛不欲生,几经分合,“自我”战胜了“本我”,“现实原则”战胜了“快乐原则”,曾经沧海的杨小翼获得了大难后的平静,这件事给她的感受完全是正面的,温暖的。她开始真正领悟生命的意义,开始女性的主体性建构,继续着成长之旅。新时代的到来,使她的事业也步入了黄金时代。
但儿子的意外失踪使杨小翼崩溃了,她“无端地认定天安的失踪将军要负责任”,潜意识中的“恋父情结”恶化成“审父”。如果说她第一次到北京期望与将军相认却被将军冷酷地拒之门外,还酿成尹南方的悲剧,对将军的怨恨“使她变成了一个审判者”,那时的审判她是脆弱而底气不足,更多地是产生被遗弃后的自我怜悯,意识到“她确实是有罪的”。那么,儿子出事则让她终于理直气壮地找到了机会审判他,折射出她内心深处彻底放逐父亲的冲动,她怀着“强烈的弑父冲动”,要“把革命者从神坛上拉下来”。她一生都在等着和父亲相见,而当将军终于要见她时,她却决绝地拒绝了。她对父亲因爱成恨的心理彻底爆发了。
此时杨小翼的意识里是拒绝承认其父,甚至是排斥的,但在潜意识中是不排斥父爱的,甚至是渴望获得的,这样她的意识与潜意识产生了冲突,而潜意识往往构成了人的内心驱动。当她知道将军对天安的死也很伤心时,她意识到将军是她唯一的亲人了。但当她走近他时,将军又在他们之间筑起一道高墙,打破了杨小翼一厢情愿的温情。这激起了杨小翼内心的不平,她以审判者的气势步步逼问将军,最终失望地离开。尽管杨小翼在意识里“尽量不再恨他或爱他”,但在将军的葬礼上她潜意识中的“恋父”让她不禁失声痛哭。
《风和日丽》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所谓“成长”,“就是通过叙事来建立主人公在经历‘时间’之后终于形成了自足的人格精神结构——即‘主体’(生成)过程的话语设置”。[6]其中“父亲”这一角色有着非同寻常且不可或缺的意义。“随着女孩儿的进一步成熟,在女性体验到父亲的情感联系对其成长重要性的同时,她更会逐渐领悟到:社会要求女性的成长即是形成一种以被动性和依附性为核心特征的性格”,“只能被动等待别人— —特别是父亲的赞许来获得生存的合法性”,“女性只有通过对于父亲语言行为、精神人格的审视与反思才能获得自我的成长天空”,正是基于这种性别成长境遇的深刻体认,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注定会陷入从“恋父”到“审父”的情感演绎过程,因为“她们面对的既是亲情之父,又是文化之父,是面对女儿的父亲,也是面对女人的男人,这种父亲与女儿、男人与女人的纠缠不清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幽深难解的女性经验区域,使得女性陷入成长的痛苦与欢欣之中”。[7]弗洛伊德认为,恋父情结的根源是里比多(libido),受到压抑时这种情结会变成无意识的一部分,在无意识中影响人的行为,对人的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省察杨小翼的成长历程,父爱的缺席使她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恋父情结。虽然杨小翼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但母女俩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而母亲和李医生的私情更让杨小翼对母亲心怀敌意。父亲的缺席、身世之谜,不仅使杨小翼对从未谋面的生父产生一种无意识的依恋,也引发了母女间的一系列冲突,使她对母亲产生一种无意识的敌意,即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女孩常迷恋父亲,要推翻母亲取而代之的“爱父嫌母”的潜在愿望。从满心希望获得父爱的“恋父”到“寻父”、“恨父”、“审父”,这是其内心“恋父情结”的演绎过程,也伴随着她的成长。即使最终她都没有得到将军的正式承认,也断绝了再得到他的认同的想念,但是“她在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取消过‘父亲’的形象”,“这形象一直以某种方式作用在她的精神深处,成为她潜意识的依靠”。“父亲”在杨小翼的成长历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引导着她的命运。正是潜意识中对“父亲”的热爱和渴望,她才远赴北京寻父。虽然怀着被将军无情拒绝的愤恨,但她仍冒险救出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军并承担了因此带来的所有灾难。在将军将死之时,她仍满怀女儿对父亲的怜惜、悲痛之情。杨小翼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种由于父爱的匮乏所导致的“创伤性情境”,这决定了她从“恋父”到“审父”的过程中确立女性个体的成长历程。主人公逾越父亲而成长,一骑绝尘而去,用自己的方式孵化“良心”,而将军遗物中那张杨小翼儿时的照片证明她早已被父亲在心里接纳了。
“母亲走了,‘父亲’也走了,她没有孩子,一切都消失了”, 这个冬季风和日丽,杨小翼经历了从“恋父”到“审父”艰难的跋涉,完成
[1]西蒙•波伏娃著,李强选译:《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31页。
[2][3]西蒙•波伏娃著,李强选译:《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32页。
[4]王昭晖:《化不开的情结——张洁爱情观破译》,《钦州学院学报》2008年8月第23卷第4期。
[5]J•贝尔曼—诺埃尔著,李书红译:《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解析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45页。
[6]樊国宾:《主体的生成: 50年成长小说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页。
[7]高小弘:《“恋父”、“审父”与女性的个体成长——以陈染的小说为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7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