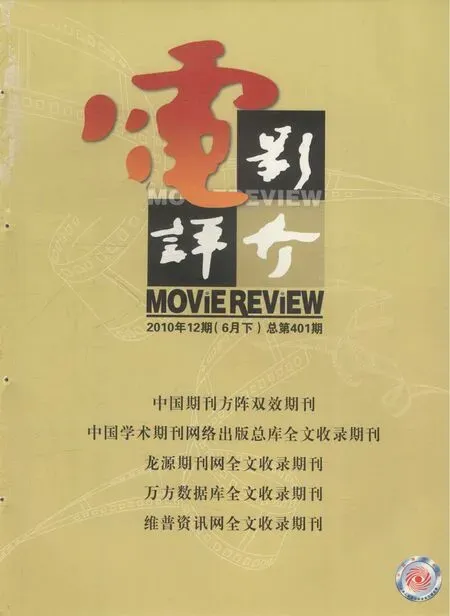遵义县、普定县花灯调查
花灯是广泛流行于我国民间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历史久远,大致起源于唐宋之间。贵州花灯大至于明朝初年由江南、中原传入,风行于明清,至民国,更是流行贵州大部分乡村集镇。花灯源于民间,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地域方言、民族、习俗等影响,在我省形成了不同演唱、表演风格的“四路”花灯:即以遵义县为代表的北路花灯、以普定县为代表的西路花灯、以思南县为代表的东路花灯、以独山县为代表的南路花灯。
一、遵义花灯
遵义县地处贵州省北部,遵义花灯男主角称为丑角,俗称唐二;女主角称为旦角,俗称幺妹,演员手持巾、扇,边唱边舞,俗称“跳花灯”。
花灯剧的唱腔有两类,一类是略具雏型的板腔,艺人称“灯戏调子”,一类是曲牌,艺人称“花调子”。在一出戏中,板腔与曲牌可以混合使用,形成一种综合体制。板腔的板式较单一,若干个上下句反复演唱,最后加上一个“收腔”(也叫“放板”或“放腔”)结尾。经常使用的灯戏调子有:《出台调》、《行程调》等;常用调子有:《四小景》、《四季相思》等;常用伴奏乐曲有:《游台》、《大开门》等;常用的锣鼓牌子有:《三六九》、《扑灯蛾》《半边月》等;花灯剧主要使用筒筒(胡琴类拉弦乐器)、月琴等弦乐器及锣鼓等打击乐器伴奏表演。
传统剧目小戏多取材于农村生活故事和民间传说,如《拜年》、《姊妹观花》、《放牛拦妻》、《刘三妹挑水》、《替嫁》等;大戏多由其他剧种移植而来,如《柳荫记》、《玉簪记》等;根据民间唱本改编的条纲戏有《二度梅》、《八仙图》等;共100多出。
遵义花灯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特征是:手执扇、帕,载歌载舞,表演以“扭”为特点,步法有二步半、四方步,快、慢三步,野鸡步、梭步、碎米步、矮桩步等;扇法有小花扇、大花扇、交扇、盖扇等;身段有犀牛望月、膝上栽花、黄龙缠腰、海底捞月等;花灯戏的曲调有的戏剧性较强,也有的源于抒情性的民歌小调,其中“绣荷包”最为闻名。在流行过程中逐渐打破了“灯、扇、帕”的歌舞程式,脚色行当也不再局限于“二小”、“三小”,而有了净、末、老旦、彩旦等的划分。
在表现情节刻画人物时,板腔与曲调综合使用,形成了丝弦灯调系、台灯灯调系和锣鼓灯调系,音乐表现力更加丰富。其乐曲腔调在原有曲调基础上也出现了扩展变化,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板腔”和“曲牌”。常用的板腔有《奉贺调》、《祝英调》等;民间花灯歌舞中形成的花灯小戏剧目如《五更劝夫》、《英台故事》等;民间祭祀、酬愿活动中的“坛夹戏”如《财神登殿》、《八仙送寿》等;移植、改编剧目如《安安送米》、《蟒蛇记》、《槐荫记》、《芦花装衣》、《范叔赠银》等。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遵义,花灯艺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迸发了编唱和演出新灯的激情,县境内先后创编了《红军灯》、《修路灯》、《参军灯》、《劝赌灯》等新灯。
据花灯艺人讲,从解放初期直到80年代初期,黔北每个乡镇几乎都有花灯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论是祭祀、礼仪、祈福纳愿、生子、祝寿、建房、开店、等都要唱灯。而春节到来之际,更是处处张灯结彩,玩灯唱戏。有龙灯、狮子灯、麒麟灯、走马灯、牛灯、马灯、蚌壳灯等。黔北花灯因时间、场合、意愿的不同可分为春灯(春节期间的唱灯)、寿灯(祝寿而请灯班演出)、喜灯(结婚、生子、建房等喜事)、愿灯(许愿或还愿)、孝灯(给故人所唱行孝之灯)等。
民间花灯歌舞中形成的花灯小戏剧目如《五更劝夫》、《英台故事》、《小妹卖面》、《红军灯》、《十二缘配》等;民间祭祀、酬愿活动中的“坛夹戏”,如《财神登殿》、《八仙送寿》、《孟姜辞神》、《扫土地》、《赦罪》等;移植、改编剧目。如《安安送米》、《蟒蛇记》、《槐荫记》、《芦花装衣》、《范叔赠银》、《断机教子》等;创作剧目如《血肉相连》、《支援铁路建设》、《请媳妇》、《丫枝》、《招郎榜》等。
团溪花灯主要传承人有:蔡云亭(1901-1973)由仁怀迁至团溪乐稼乡,将祖传花灯传与后辈蔡恒昌、蔡炳章、蔡汉章等,现今传承人为蔡孝刚(男,1955——)、蔡孝福(男,1966——)。
曾祥志(1945——),团溪镇农庄村村民,主要扮演唐二并担任乐队乐手。演出的多是农村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目前曾祥志是团溪镇民间演出花灯最多的民间艺人。曾祥志的第五个儿子曾令云(1977——),是当地有名的乐手, 2007年开始学习花灯。
1、遵义花灯现状
花灯在遵义县境内各乡镇均见流布,现今,花灯在三合镇、泮水镇、团溪镇较为流行。
1983年《遵义县戏曲志》29页载:“花灯戏……流布于全县各乡村,其中以枫香、泮水、茅坡、虾子、三合、南白、尚稽、团溪等地复盖面较大,各地花灯音乐大同小异,以枫香、泮水、茅坡具鲜明的表演特征……”在1991年的花灯流布地调查的分布图上没有了枫香、茅坡、虾子、三合,多了松林、新卜、龙坪、板桥镇;到2007年,则只有三合镇、泮水镇、团溪镇还有花灯。
二、普定(“西路”)花灯
贵州“西路花灯”主要流传于黔中腹地安顺市普定县。
“西路花灯”来源于江西的戈阳腔。明洪武六年(1373年),明王朝调北征南,汉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融合产生了普定花灯。始为庭院艺术,至清顺治年间出现花灯班,乾隆时期(1736-1796年)在城乡之间已较普遍。
“西路花灯”每逢新春正月演出,农历七月也有花灯演出,有祈祷五谷丰登之意,名为“米花灯”,出均在晚间举行。平时喜庆场合及宗教活动中也有艺人应邀演出。
现普定“西路花灯” 有100多支民间花灯队,主要分布在马关镇、城关镇、马场镇、龙场乡、白岩镇、鸡场坡乡、补郎乡。并向镇宁、六枝等周边县流布。县境内乡村一级的花灯队有近四十个。马关镇成立了“凤霞艺术团”、马堡村成立了“马堡农民文化艺术团”,专门从事花灯的创作和表演。城关镇在2006年普定县承办的贵州省首届花灯大赛活动中,新编花灯歌舞“四在农家开新风”荣获二等奖。
马官镇是贵州省文化厅表彰命名的“花灯艺术之乡”。
民间花灯队一般演出的主要还是传统剧目,如《高腔调》、《踩倒妹小脚》、《唐二闹春》等,基本没有纯花灯小戏。
1、主要特征
西路花灯有“地灯”、“台灯”之分,表演主要有歌舞灯和灯夹戏两种艺术形式。歌舞灯以“歌不离口,动不离手,手不离扇帕,身不离步法”为表演特征,表演上融庄、谐、雅、幽默、滑稽、插科打浑为一体,并与叙事、抒情相结合。花灯中的女角色一般都是男扮女装,假嗓演唱。
西路花灯在演出中,除表演闹堂亮相、登台白话倒灯、撒高腔、请旦角等外,还要表演参(拜)寨门、参土地、参庙门,在一些时候,根据主家的要求,还会表演开财门、贺家等。
“矮桩”是“西路花灯”舞蹈中从头到尾贯穿的一种形体动作,表演时,两脚下蹲,上身挺直,两手挥动扇帕,表演“螃蟹行”、“耗子蹬腿”等。
唐二趣乐表演,主要在“搭上咐”、“颂灯”、“白”程序中展现,均为唐二的独角戏。
老旦是普定花灯特有的风格,在歌舞灯、小戏中都可参与表演,一般不爱限制。主要从老妇人生活中的各种动作、步伐、表情提炼的形象动作,男扮女装,假嗓演唱。
花灯调子一般宣扬勤劳、善良、勇敢、正直、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有基本不变的固定调子,也有灵活多变的逢场作戏,可颂扬、可针贬,言词可温柔、可辛辣,视情节而定。
传统花灯一般为口口相传或现编现演,而现在新创作的节目则有文学本,现编节目多用新词套老调,如宣传计划生育、改炉改灶、三个代表、新农村建设等。
伴奏乐器有二胡、锣鼓、月琴;道具有花扇、花帕、灯笼。
传统花灯在开演之前有祭灯仪式,结束时要谢灯,把灯具烧掉,来年重新制作。现因有了灯光照明而鲜用灯具。现在的一些灯班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还购置了一些西洋乐器来满足现在人们的需要。
三、现今主要的传承人
龙场乡龙场村刘忠富,男,(1943——)在贵州省首届花灯大赛中获“民间花灯王”称号,被专家们称为“原生态西路花灯的代表”。现在马宫镇教花灯,前后共有徒弟100多人,现有徒弟20多人。
马官镇下坝村丁世龙,男,(1967——)在贵州省首届花灯大赛中获“民间花灯王”称号。
城关镇石头堡村王必成,男,(1956——)系已故徐荣华(有贵州西路花灯王之称)的弟子。擅长老旦。
城关镇何恒扬,男(1950——)从1983年开始指导全县各乡镇多个花灯队,弟子在各种比赛中多次获奖。
化处镇播仁村付尚伦,男(1943——)从1980年开始收集整理大量花灯音乐,编辑有《普定花灯集成》。
四、现状与建议
自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办[2005]18号) 颁发以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受到重视,思南花灯、独山花灯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名录,遵义花灯、普定花灯被列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遵义、普定县都对本县花灯制定了相应的保护计划;遵义、安顺将公认的老艺人纳入保护的第一要务,从生活、保健等方面对花灯老艺人给予政策性补助,挑选中青年向老艺人学习花灯技艺,参加各种花灯骨干培训班,文化部门还在每年重大节日组织不同形式的花灯大赛等,这些措施对我省花灯的保护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威胁花灯的现实则更为严峻:
1、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的普及,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各种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这是导致民间花灯逐渐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2、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商品经济的冲击,导致花灯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加速了传统民间花灯艺术的变异和消解。
3、农村大批青壮年外出经商、打工,分散各地,他们告别了家园生活,也告别了花灯,从而导致了花灯观众的后继乏人。
4、存世的老艺人越来越少,人亡艺绝形势严峻。如普定县的“西路花灯王”徐荣华等相继去世后,传承出现断层。
5、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式微,导致许多人认为民族民间艺术是落后、守旧的,因此对其加以排斥,使其生存空间变得狭小。
6、文化馆专业队伍匮乏,一方面,具有花灯专业的人员很难进入文化馆,另一方面,没有专业业务技能的人员则充斥专业人员的位置,很多文化馆已经失去对群众进行花灯辅导培训、创编节目的能力和水平。
建议:
1、利用有线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加强对花灯的宣传。
2、为培养新一代受众,在有条件的地方,可把花灯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同时,把培养花灯艺术人才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