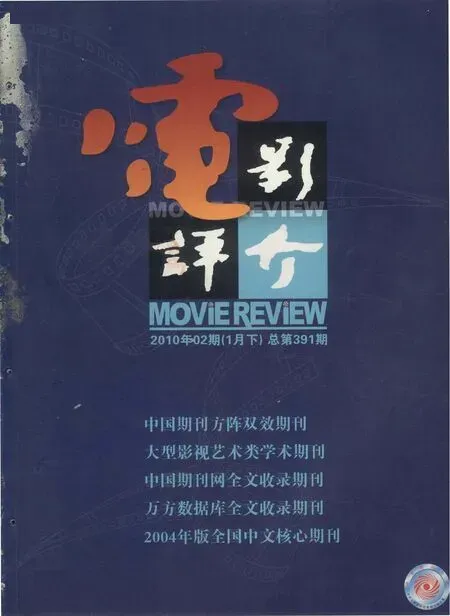用镜头雕刻时光:析贾樟柯电影对时间的处理
一、“雕刻时光”理论
在电影艺术方面,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对“时光”有着特别的研究:他有两本论著,一本日记集《时光中的时光》,一本电影理论《雕刻时光》。在《雕刻时光》中,塔可夫斯基明确提出了“雕刻时光”的理论。
电影自产生那天起,就必然依赖观众而生存。没有电影观众,就不会有电影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从这一意义上说,电影导演和电影观众是电影这枚硬币的两个面,两者不能没有对方而单独存在。对于电影观众,他们为何愿意花钱、费时间去观看一场电影?塔可夫斯基的回答是“一般人看电影是为了时间:为了已经流逝、消耗,或者尚未拥有的时间。他去看电影是为了获取人生经验。”[1]电影凝聚了人生流逝或尚未拥有的时间,蕴含了广泛的人生经验。观众去看电影正是为了获取这些时间,体验这些人生经验。
塔可夫斯基这里所说的电影,自然是他认为优秀的电影。观众观看电影为了时间,必定是导演在电影中凝聚了时间:
导演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雕刻时光。如同一位雕刻家面对一块大理石,内心中成品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一片一片地凿除不属于它的部分——电影创作者,也正是如此:从庞大、坚实的生活事件所组成的“大块时光”中,将他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抛弃,只留下成品的组成元素,确保影像完整性元素。[2]
电影导演与雕刻家的工作有着同质性,他们“雕刻”的对象虽然不同,雕刻方法却无异。电影导演面对丰富繁杂的人类生活,如同雕刻家面对粗糙硕大的石块,他们必先心中有数、成竹于胸,才能剔除杂质,铸造精品。他们的目的相同,他们用雕刀剔除的是冗余,造出的是艺术,而保存的是永恒的人类时间。
对于所有人,时间消逝都不可逆转,逝去的时间如同消耗的生命,不可挽回;留下的只是丝缠般的记忆,每个人对过往的生活都在头脑中留下一团一团难以磨灭的记忆。人类天性喜欢表达这些记忆,古人用雕刻、绘画和文学等艺术作品来表达,而现在,照相和摄影成了人们凝聚时间的主要工具。
电影导演就是那些凝聚时间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镜头保存了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时间;人们在电影中发现这些最珍贵的时间,勾起他们对记忆的确认,使他们逝去的生命得以重访。这就是电影导演为何要拍电影、观众为何要观看电影的缘由。
二、记录逝去的岁月
贾樟柯正是他那代人(或几代人)逝去或即将逝去时间的雕刻家。科技与传媒在今日已十分发达,可历史的书写,或者大部分影像资料记录的都是社会大事和社会高层,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却不被关注,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甚至被长期忽视;即使一些人有幸得以记录,也往往会有所扭曲,不能传达真实。在这样长久的忽视或扭曲中,人们过去的时间流逝了,却没有保存,许多人的记忆仅仅成了记忆,他们再没有机会重新体验。
对此,贾樟柯有着明确的真实记录普通人生命的使命意识:“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3]在贾樟柯那里,电影是医治社会遗忘症的医疗器械。
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处在社会旮旯里的小人物,他们无人问津,不被重视;实际上,这些小人物在中国有千千万万,更能代表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每个平淡的生命都有着他们的喜悦或沉重,都值得社会关注和记忆。
小武是一个被人忽略、被人鄙视的小偷,他是“小”偷,所以被人忽略;他是小“偷”,所以被人鄙视。人们忽视的是他的“小”,鄙视的是他的“偷”,可从来没有人关注他也有普通人一样的友情、爱情和亲情,没有人注意小武内心也有单纯与善的一面,没有人尊重作为一个小偷也有他基本的人格尊严。人们对小武只是斥责和嘲笑,贾樟柯却对他报以同情和尊重。
“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从来没有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4]小武就存在于贾樟柯出生的那个小城,存在于贾樟柯那一代人的青年生活中。贾樟柯在评价小武时说:“自尊、冲动以及深藏内心的教养,是我县城里那些朋友的动人天性。”[5]所以“到了贾樟柯那儿,他把他们那代青年的失落感,说出来了。”[6]
每一个人身边或许都有“小武”这样的人,每个人的身上或许都有些小武的影子,嘲笑和斥责是对自己的不敬,同情和尊重或许更能留存我们的记忆、提升我们的人生。
《站台》凝聚着中国人已经逝去的一段共同时光,贾樟柯用史诗般的镜头将这些小人物(实际上他们可以代表中国那一代人)的这段历史搬上银屏。贾樟柯认为《站台》“讲述了中国人的一段共同经历,那也是我时刻怀念的一段时光。”[7]
贾樟柯的目的在讲述一段历程,记录一段时间,表达凝聚在这段时间里的个人体验:
个人动荡的成长经验和整个国家的加速发展如此丝缠般地交织在一起,让我常有以一个时代背景讲述个人的冲动。如果说电影是一种记忆方法,在我们的银幕上却几乎全是官方书写。往往总有人忽略世俗生活,轻视日常经验……我想讲述深埋在过往时间中的感受,那些寄挂着莫名冲动而又无处可去的个人体验。[8]
《二十四城记》整个是一部回忆之作,三个女人的虚构故事和五位讲述者的亲身经历,记录了一段逝去的历史。贾樟柯认为,“同时用记录和虚构两种方式去面对1958年到2008年的中国历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9]
不管是贾樟柯电影本身,还是他对电影的认识,都有着明确的记录逝去岁月、凝聚平凡时间的目的,他的人物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小人物,却也最能代表那个时代。
三、精心选择的镜头
既是“雕刻时光”,“时光”成了电影导演表现的对象,那么“雕刻”就是电影导演记录时间的方法。雕刻不是堆积,也不是简单的削砍,而是精心地去除和保留。具体到贾樟柯的电影中,就是他对镜头的精心选择。
在《小武》中,有一个不易发现但颇具匠心的细节,最能说明贾樟柯对镜头选择的良苦用心。靳小勇电话上拒绝朋友提议婚礼邀请小武时,颇踌躇地回望一眼身后破旧的砖墙。墙上刻着几条历经年月、清晰可辨的身高线,线旁写着“小武”“小勇”的字样。这个镜头告诉观众,小勇和小武从小一起长大,那堵他们经常玩耍于下的墙壁是他们一年年长大的见证。那几条斑驳了的身高线不仅雕刻着他们的童年,雕刻着他们的友谊,还雕刻着他们之间如今难以弥合的隔痕。这一镜头是贾樟柯精心选择的镜头,是他对“时光”最精巧的“雕刻”。
在《站台》中,导演展现了三次不同的火车鸣声:第一次是影片开头部分演员演出时的学鸣,第二次是几年后崔明亮等人去铁路边听到真正的火车鸣叫,最后一次是影片结尾处水开时水壶如火车鸣叫般的鸣声。影片前中后三次鸣叫,伴随着崔明亮等人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流逝,有着巧妙的隐喻意味。
对于偏远县城里的青年,火车代表着远方和希望。贾樟柯曾说:“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比我大十岁的那主人公身上。”[10]三次火车鸣声凝聚了偏远县城青年们对未来寄予的希望和失望,凝聚了他们由青春激昂到平凡平庸的人生历程。
同样在《站台》中,有一幕是女青年钟萍和瑞娟在屋里抽烟,她们在烟雾中闲聊,她们的青春也随烟雾慢慢的消散。这一幕有着强烈的时间感,“两人女人的惆怅和着闲散的时光飞逝。这种景象与我的记忆完全一致,并让我沉浸于时间老去的哀愁中。”[11]在这烟雾弥漫的屋里,消散了的是烟雾,消逝了的是时间,而老去了的是她们如花般的青春。
《三峡好人》中,护士沈红远道而来寻找丈夫,在破旧的机械厂找到了丈夫破旧的储物柜,然而这储物柜已披满灰尘,钥匙已打不开锁。沈红果断地拿起锤子,一锤将其敲开。这个尘封的储物柜正是贾樟柯所说的那类“静物”,“静物”虽披满灰尘,被人弃置,可那灰尘上面凝聚着逝去的时间,保留着过往的记忆。“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视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12]沈红丈夫的储物柜装载着她与丈夫曾经的苦涩爱情,如今已布满灰尘、不可打开;她那果断的一锤,或许正是为了告别这段尘封的恋情,走向另一段崭新的时间。
四、用社会时间雕刻个人时间
贾樟柯电影雕刻时间最精妙的方法是用社会大事定位普通人的生活小事,这一手法意义丰富,最重要的是,将小人物的苦乐人生,印在社会大事的背景之下,给这些小事定下基调,刻上时间;也提醒观众,集体欢庆的时候,莫忘了小人物的哀愁。
小武友情破裂、爱情失踪后回到家中,因戒指事件与父母发生严重冲突,被赶出家门。当他沿着村里的小路一步一步离开生他养他的家时,喇叭里播放着香港回归的消息。香港回归,小武离家,这一大一小,一回一离,既定位了时间,又烘托了气氛,国家的集体欢乐并不能消除普通人的个人悲哀。同样,在《小武》中,电视和广播里反复播放的是社会治安的整顿和国家严打的政策,小武作为小偷,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顶风作案,为他挽回友谊、获取爱情偷取一份资本,这大事小事的糅合,传达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剧感。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站台》中贾樟柯对国家大事和个人小事的同时记录。钟萍与张军去医院打胎,钟萍害怕,张军执意让钟萍打掉,两人在楼道里发生争执,这时喇叭里传来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的声音。喇叭里的声音表明钟萍打胎的事发生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节的上午,那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国家集体欢乐中,小人物有着他们自己的苦乐,不因为社会的欢乐,他们就减少了生活的哀愁。
《三峡好人》中,两千年多年的奉节县城要在两年内完成拆迁,这样急剧的变化给许多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社会关注的是三峡水坝如何建造和如何雄伟,贾樟柯则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巨变下的小人物们的苦乐人生,记录下这段即将逝去的历史和记忆。若干年后,奉节县城已沉没在深达百米的长江水中,可《三峡好人》还记录着它最后时刻的一段哀戚忧伤的时间。
流行歌曲是时代的心声,是社会世俗文化的风向,贾樟柯惯用流行歌曲衬托普通人的生活。用流行歌给普通人生活定下背景,往往有着反讽意味。在《小武》中,贯穿整个影片的是《心语》,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歌曲之一,那哀婉的歌声给影片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站台》是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贾樟柯直接拿来作为影片的名字,来雕刻那一代人永远等待可毫无希望的青春岁月。直接以歌曲名字命名的影片还有《任逍遥》,这又是一个反讽,片中的两个小青年和一个歌妓一直追求着逍遥的人生,可是逍遥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在《三峡好人》中,《两只蝴蝶》和《老鼠爱大米》正是那两年最流行的歌曲,歌声里抒发着对爱情的渴望和赞美,两个山西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奉节寻找爱人,一对分离了十六年而艰难地走在了一起,一对黯然地离婚。《上海滩》是小马哥手机里的音乐,伴随着他走完最后的人生,那令人荡气回肠的歌声见证了一个普通青年由生入死的可悲青春。《二十四城记》中,《歌唱祖国》是成发集团工人唱了几十年的歌曲,歌声发自他们的内心,他们热爱祖国,辛勤劳动,可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段坎坷的人生历程。
贾樟柯的电影拍摄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西部小城镇人真实的生活。如他自己所说,时代大潮汹涌前进时,别忽视了被时代撞到在地的人;贾樟柯的电影镜头关注的正是那些被时代撞翻在地的人,他们虽是普通人,可他们是我们的同伴,甚或是我们自己。
几代人的青春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中张扬和消逝,贾樟柯对此不做评价,他要做的是用他的镜头精心雕刻这一历程,使之成为永恒。喜爱贾樟柯的人会在他的电影里找到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贾樟柯已帮他们雕成精品,保存下来。由于它们真实,所以感人;由于它们稀少,所以弥足珍贵。
观看贾樟柯的电影,他的镜头会时不时勾起观众曾经的记忆,让人哀叹,让人唏嘘。再过几十年,人们重温《小武》、《站台》和《三峡好人》时,又会记起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发生在他们青年时代的事情,重返已经消逝了的时间,体验这段时间留给他们的越来越厚重的人生经验。
[1]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第64页。
[2]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1版,第64页。
[3]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31页。
[4]陈丹青著《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转引自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页。
[5]贾樟柯著《片段的决定——〈小武〉》,2002年《今日先锋》第12期。
[6]陈丹青著《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转引自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页。
[7]贾樟柯著《片段的决定——〈站台〉》,2002年《今日先锋》第12期。
[8]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00页。
[9]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49页。
[10]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82页。
[11]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75页。
[12]贾樟柯著《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