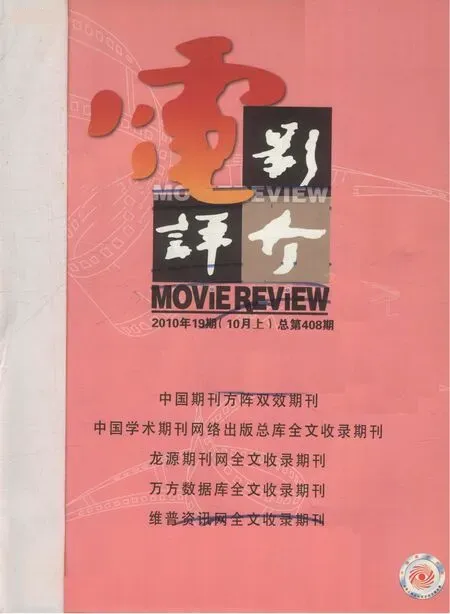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艺术之本在艺术家之心
与西方艺术不同,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孕育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特色。中国古代艺术重视情感的感悟,其本体在于艺术家内心情感的表达,而非其它外物。《乐记》是我国最早(公元前5-4世纪)和最系统的艺术美学专著之一,它探讨了乐之本质,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的乐之本体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乐不是专指的音乐艺术,而是泛指的当时的一切娱乐活动。“《乐记》的‘乐’字应读作lè,而不应读yuè。译为英文当是‘recreation’而不是‘music’”。[1]从这个意义上看,《乐记》中提到乐之本体在人心的论断可以代表中国古代艺术之本体也是在人心。下面分别以中国古代的绘画、书法和音乐艺术为例来看中国古代艺术之本体。
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之本
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关系”的发展可以用一个公式来简单的概括一下,即是由“神似形不似”到“形神兼备”再到“重神轻形”。在汉代以前,受材料和工具的限制加之绘画艺术尚处于起源探索阶段,这时期的绘画作品如岩画、汉画等均显得稚拙,但不失其神韵;“形神兼备”时期应以晋唐为代表,这时期的画家顾恺之、吴道子等均追求形似与神似的统一,这时期的作品达到了古典美的高峰;而“重神轻形”则始于北宋文人画派,进而一直延续至元明清乃至今日。文人画追求简约、意趣、追求诗书画印的融会贯通,这就导致了对形似的忽略甚至是批判。如徐渭的作品、八大作品等都体现着这一点。从而形成了中国绘画“重神轻形”的绘画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绘画不是机械的模仿,也不是一种“再现”,而是艺术家的一种内心情感流露。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绘画之本发于艺术家的内心,试看古代画论中的论述:
六朝•王微:“本乎形着,融灵而变动者,心也。”
唐•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宋•韩拙:“夫画者,笔也,斯用心运也。”
明•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
清•石涛:“夫一画,含万物于中,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2]
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说,“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会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3]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古今的绘画艺术理论家们都地认为中国画本于艺术家的内心感悟。从中国画的创作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画是用心来创作的。物有感于心而动情,情动而外显于物。关于心、物之关系,张璪说的很清楚,“师造化”是外,“得心源”是内,而其本在“中”,“中”即是人心。石涛也认为绘画的创作归于心运,“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最终是受心的支配。中国古代绘画强调内心情感的表达,是一种“表现型”的艺术,“表现”即表现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二、“书,心画也”——心为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之本
中国文字的特殊形态造就了中国的书法艺术,它是以中国文字为基础的。自从产生汉字之始便有了书法艺术,直至今日它以其魅力仍旧为很多人所钟爱。那么它何以产生如此之魅力呢?答案是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是一种“表现型”的艺术样式,也注重情感的表现。醉时可以书,病时可以书,高兴时可以书,忧郁时也可以书。书法艺术之本在于艺术家的内心,而仅仅追求字之美观,字之外表,则始终只能是写字,而非书法。汉杨雄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也提到:“书也者,心学也;写字也,写志也”。这里牵扯到了书法与写字之间的区别,认为书法是一种心学,抒发情感,写字则是抒发的志向。清代的周星莲说的更为明白:“后人不曰画字,而曰写字。写有二义,《说文》‘写,置物也’,《韵书》‘写,输也’。置物者置物之形,书者输我之心,两义并不相悖,所以写为心画。若能置物之形,而不能输我之心,则画字、写字之义两失矣”。[4]由是言之,所谓“写字”是“置物之形”,所谓“书法”是不仅要“置物之形”,而且更重要的是“输我之心”。
书法艺术的创作也是要用心来指导的。蔡邕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5]蔡邕说的是书法创作前的心态问题。他认为作书前的心态应该是自由的,即是“散”的,而不应受任何琐事所迫,任自己的思想徜徉于脑海。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如此的平静呢?那就是要“默坐静思,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达到一种完美的书法创作心态—精、气、神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体现出书者之情。这正是“书者,心学也”。
三、“乐者,心之动”——心为中国古代音乐艺术之本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艺术门类中,音乐可算是最能体现“本于心”了。因为音乐形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抽象的。要体会这个形象,则要通过想象力去思考领悟。音乐产生的历史比较久远,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在黄帝的神话中就有“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的音乐缘起之说。《乐记》开篇《乐本》篇就讲到了音乐的本体问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6]以上是《乐记》关于音乐之本体的论述,乐是由人的内心发出来的。人心有感于外物而生情,情作用于音便形成了乐。
对于音乐的欣赏更需要用心体会。不同地域的人们有不同的风俗,也就有不同的内心世界,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乐曲。之所以不同,根源在于他们不同的心世界的。阮籍《乐论》“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歌之者流涕,闻之者叹息”。[7]因此,听“火焰赴水”之歌时,我们便会感到楚越人好勇的风俗,听到他们内心的感情激荡;听“桑间濮上”之曲时,我们便会感到郑卫之风的轻荡,听到他们内心的阴柔缠绵。总之,音乐之本在于艺术家内心对于外物的感悟,而欣赏音乐艺术便是体会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小结
由于篇幅的限制,加之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中国古代艺术门类都拿来论述一番,来证明中国古代艺术之本在于艺术家的内心。就绘画、书法和音乐三门典型的艺术门类而言,“心”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重视“心”的本体就是对主体的充分肯定,不像古希腊的艺术摹仿之说强调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忽视了主体内心的能动作用。在表达“情”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艺术更胜一筹。因此,中国古代艺术强调个人精神的主体性,人格的自由性,是艺术家内心感悟的外在表现形式。
[1]赵宪章、朱存明: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2]俞建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17-718页。
[5]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页。
[6]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7]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集【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