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弘扬白求恩精神
/季 余
坚定不移地弘扬白求恩精神
文/季 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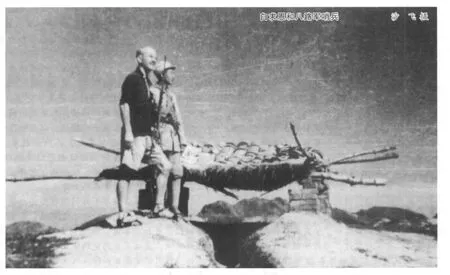
今年3月3日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诞辰120周年。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72年前,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民最艰苦的岁月里,真心诚意、竭尽全力地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最后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朋友,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这位真正的纯粹的共产党人。
我们都知道,白求恩牺牲后,毛泽东立即写下了著名的 《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指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成为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的高度评价,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要终生坚持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事实正是如此。正由于白求恩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才能在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狂肆虐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舍弃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弃自己已有的名誉地位,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地奔赴反法西斯的战场。正因为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发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他对人民对同志极端地热忱,对工作对伤员高度地负责任,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爱护。他宁肯自己挨饿受累,也要尽量减轻伤员的痛苦。他曾一连六七十个小时不下手术台,一口气为一百多位伤员施行手术。他把布鞋拿给伤员穿,自己穿草鞋,甚至打赤脚。他在手术之余,还自己编写教材,为中国培养医护人员。他是技术高超的专家,却拒绝享受高于别人的津贴。他曾说: “你们不要把我当作古董,我是来工作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来使用。”这种感天地、泣鬼神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知道感动和激励过多少中国的军民。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后来的胜利以及中国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取得,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我们党充分发扬了这种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
就像许多伟人、英雄以及一切革命真理有时也会遭到曲解和攻击一样,在今天,白求恩和他的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也受到了曲解、非议乃至诽谤和谩骂。十多年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著文说,提倡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 “完全扼杀人的个人性”;提倡 “为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全人类的 ‘共同理想’贡献一切”,就是 “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这是 “很可怕的”。钱先生这番高论,活活画出了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灵魂。个人主义者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和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要他们牺牲一点个人利益无异于要他们的命,当然 “很可怕”了。可是,白求恩是共产主义者,坚持的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后者和前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在共产党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它的最终实现而奋斗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终生追求的价值目标。提倡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然不是不要个人利益,但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个人利益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这是完全自觉自愿的,丝毫没有“强迫”的成分。但这在坚信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者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对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无独有偶。继钱先生之后,2009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上又刊出 “广州学者”林贤治先生的一篇同样是张扬 “个人主义”的文章,题目是 《白求恩:孤独的异邦人》。这回不是直接谩骂白求恩精神了,而改为从作者的主观想象出发,用虚构和幻想,用断章取义和歪曲文献的手法,给我们 “塑造”了一个与真实的白求恩丝毫不搭界的 “白求恩形象”。文章认为,白求恩的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外在的表现,他内心深处还保留着 “个人主义的特质”;在组织关系上他是共产党员,本质上却是一个保留着“个人化”,追求着绝对 “自由”的“西方知识分子”,一个充满着 “幻想的热情”的 “乌托邦主义者”。据说,这表现在他与党组织、与革命战争的格格不入上。他是受斯诺的 《西行漫记》等书的 “诱惑”才来到中国的,并没有真正融入中国的革命队伍,始终不过是一个 “孤独的异邦人”……听着作者这样的叙述,简直像是在听一个新编的拙劣的神话。
先来看林先生是怎样描写党组织以及白求恩与党组织的关系的。林文说,党组织是一个 “机械主义的”, “程式化、官僚化、甚至非人化的”机构,它要求个人 “无条件服从”, “但知识分子不能。他要在组织内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无论何时,维护个人的尊严甚于生命”。这里的所谓“组织”纯属虚构。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内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何来 “官僚化、非人化”?这只要看看毛泽东在延安穿着打补钉的裤子给席地而坐的战士们作报告的照片就明白了。党作为组织当然要有组织纪律,不过这种纪律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当一个党员认识到党的历史使命同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认识到党的纪律同党的奋斗目标相一致时,他就会感到纪律与自由是统一的。他既是组织的一分子,又是一个独立的奋发有为的个人。白求恩正是这样的共产党员。他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来,到枪林弹雨的前线去,都是主动请缨的。他在工作岗位上总是主动地创造性地工作,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独立性”,从而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他对党组织非常忠诚,非常敬重。当他把党证交给毛泽东时,他是那样的激动,仿佛一个游子回到了久别的家。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也不管工作多忙,他都坚持给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党组织写信,汇报工作。……只有戴着有色眼镜如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从这里看出什么党组织对白求恩的“压抑”和白求恩同党的疏离来。
再看看林先生怎样描写 “革命战争”以及白求恩与革命战争的关系吧。林文认为, “革命战争”容不得 “个人友谊、欲望、感情、志趣之类”。 “倘若革命不是以一种尽可能民主的、温和的形式进行,拒绝 ‘请客吃饭’”,批判 “人类之爱”,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便变得不可避免了”。这真是对不起,抗日战争不可能按照林先生的愿望, “民主的温和的”,像 “请客吃饭”那样进行,否则就等于不战而束手被擒,引颈就戮。革命战士也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 “人类之爱”,白求恩只爱中国人民和他的战友们,他经常表示 “要用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来 “报答”伤员们。他不可能去爱日本鬼子,他常愤怒地说: “我们的敌人是法西斯强盗,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人道主义。”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白求恩和他周围的同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和革命的友谊。他对革命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我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便是真实的白求恩。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任何白求恩与革命的“冲突”,因为白求恩根本不是林先生构拟的那种“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而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
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说白求恩是一个始终没有融入中国革命大家庭的 “孤独的异邦人”呢?原来他抓到了并夸大了白求恩有时流露出来的思乡情绪和有时对长期收不到报刊杂志、听不到外界消息而感到的 “遗憾”。其实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完全正常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远离祖国,在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的异国他乡工作的人,产生思乡情绪不是很正常的吗?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邮路不通,消息阻隔,谁会没有一点遗憾呢?但这些都不是白求恩的本质。 “德不孤,必有邻”。白求恩这样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在人类的正义事业中是不会孤独的。他在西班牙很快便同那里的反法西斯战友们融为一体;来到中国先后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热情的接待,到了前线,他热情开朗、诙谐幽默的性格使他很快便与同志们打成一片。他曾激动地说:“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家的界线把我们分开。”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儿生活相当艰苦,……但是我过得很快乐。” “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已经爱上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由此可见, “孤独”不是白求恩的感受,而是林先生的杜撰。
我们不得不说,林先生在虚构 “白求恩形象”时采用了不够光明正大的手法。例如,1939年末,为了向欧美人民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日事迹,争取国际援助,揭露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和蒋介石封锁解放区的真相,白求恩准备动身回加拿大一趟,这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他在向朋友报告计划的信中说: “中日战争将是一个长期的战争,我打算持久下去。我们计划这次战争起码要持续十年,我们必须帮助这个优秀民族比我们现在做的多些。” “这儿的人需要我。这儿将是 ‘我的’生活领域。我一定回来。”但是,这些内容统统被省略了,而只突出他临行前想到了 “咖啡、上等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等(这些在西方生活中其实是很普通的)。这样便使引用的文字俨然成了白求恩 “追求享乐”的自白。于是林先生断言,白求恩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 (空想主义)者”, “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实属强词夺理,乖谬已极!
行文至此,不妨化用杜甫的一首诗: “白求恩氏高风范,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钱先生的辱骂也好,林先生的编派也罢,都无损于白求恩精神的光辉,只能暴露他们一类人的不良用心。这种情况表明,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弘扬白求恩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各行各业都弘扬白求恩精神,社会风气必将进一步好转,唯利是图的假药、假酒、毒奶粉之类必然大大减少。公务员们弘扬白求恩精神,焦裕禄、孔繁森式的英雄模范必会更大量涌现,反腐倡廉也会抓到“源头”,贪官、庸官或将大量减少。诚然,在私有制还存在的条件下,彻底地消除私心杂念是不可能的。但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高举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就会有不竭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