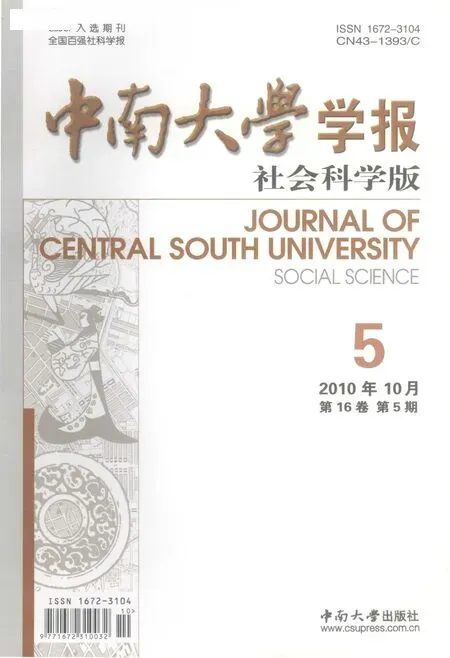汉语数量重叠式的历时考察及其类型
李康澄,何山燕
(1.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2.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汉语数量重叠式的历时考察及其类型
李康澄1,何山燕2
(1.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2.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现代汉语中“一一”“AA”“一AA”和“一A一A”四类数量重叠式各自独立发展,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基式和变式的关系。方言中的“A一A”数量重叠式,应该萌芽于唐五代时期;“一A一A”是数量短语的重叠,萌芽于唐五代,盛行于现代汉语,形成了“一一——AA——一AA/A一A——一A一A”的发展序列。这种序列既与词汇史的发展有关,也与语义的延伸有关。
汉语研究;汉语教学;数量词;数量重叠式
汉语的数量重叠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数量重叠式指数词和量词组合的重叠,包括“一 AA”和“一A一A”两种形式。广义的数量重叠式指数词的重叠、量词的重叠,以及数量结构的重叠,包括“一一”“AA”“一AA”和“一A一A”四种形式(A代表量词)。
一、关于几种数量重叠式之间的关系
以往对汉语数量重叠式的研究多关注其共时平面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很少探讨汉语数量重叠式的历时发展。长期以来学界很多学者认为,无论是狭义的数量重叠式,还是广义的数量重叠式,它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即四种形式之间是基式和变式(“省略式“和“扩展式”的统称)的关系。目前,关于数量重叠式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一A一A”是基式,它的省略式是“一 AA”。王力(1985)认为:“‘一个一个’也可省略为‘一个个’,‘一篇一篇’也可省为‘一篇篇’等[1](255)。”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宋玉柱(1978)[2](85−91)、刘月华等(1983)[3](89)、胡附(1984)[4](54)、吕冀平(2000)[5](109)、黄伯荣等(2000)[6](23)、张斌(2002)[7](298−299)。
第二种认为“AA”是“一AA”的省略形式。宋玉柱(1978)认为:“‘一 AA’有它的省略形式‘AA’或‘一一’[2](85−91)。”李宇明(2000)认为:“AA”可以看作“一AA”的省略[8](348)。
第三种认为“一一”是“一AA”或“一A一A”的省略式。认为“一一”是“一 AA”省略式的有宋玉柱(1978)[2](85−91)、张斌(2002)[7](298−299);认为“一一”是“一 A 一 A”省略式的有张静(1980)[9](104)、胡附(1984)[4](54)、邢福义(1998)[10](198)。
第四种认为“一AA”是 “一A一A”的基式。李宇明(2000)认为:“一A一A”可以看作是“一AA”的扩展[8](348)。
第五种认为“一AA”既可以是“AA”的扩展式,也可以是“一A一A”的省略式。郭绍虞(1979)认为:“因为这‘一个个’的形式,可以说从‘个个’的形式上发展来的,也可以说是‘一个一个’的形式之省[11](44)。”
以上五种观点都是从数量重叠式共时平面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的角度得出,即认为凡是能出现在某一句法位置、且语法意义相同的不同数量重叠式就存在基式和变式的关系。我们认为,基式产生变式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基式先于变式产生且使用较普遍,二是变式与基式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方面应该完全相同。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证明存在基式和变式的关系。
二、汉语数量重叠式的历时考察
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共时的语言形式是历时发展的的结果。要判断几种共时语法形式产生的先后顺序,我们有必要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考察。历时的考察可以通过抽选一部分现代汉语常用量词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进行。我们选取“匹、个、篇、件、口、头、首、片、枝、条、张、颗、节、根、只、支、滴、粒、块、双、株、朵、层” 23个现代汉语的常用量词来考察汉语数量重叠结构的历史发展顺序。我们将23个常用量词的重叠式(AA、一AA、一A一A)分别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进行检索,确定各个量词各种重叠式形式萌芽的年代。检索结果见表1。

表1 重叠式常用量词检索结果
我们将“个”“篇”“件”“片”“根”“颗”“只”“粒”“支”的数量重叠式在文献中的用例摘录如下:
(1)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唐·杜甫《屏迹二首》)
(2)妙喜回顾万庵曰:“一个个都似尔,万庵休去。”。(五代·《禅林宝训》卷三)
(3)管匠官每偷盗了钱物呵,一个一个根底斯拿省罪过,不告有管匠官三年满呵,不交管民。(《元典章·吏部》卷三)
(4)一个一个儿窝的眼又瞎,一个将纸鸦儿放起盼的人眼睛花,一个递撇牛的没乱杀。(《全元散曲·王大学士》)
(5)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南北朝·昭明太子集)卷五
(6)出众仙才是谪仙,裁霞曳绣一篇篇。虽将洁白酬知己,自有风流助少年。(唐·方干《玄英集》卷八)
(7)惊喜遽读味新好,一篇一篇奇亦奇。(宋·杨简《慈湖遗书》卷六)
(8)先生曰:“可弗杀了,我不受人恁地,此便是烧火不敬。所以圣人教小儿洒扫应对,件件要紧。……。”(宋·《朱子语类》卷七)
(9)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宋·张知甫《张氏可书》)
(10)读书须是一件一件读,理会了一件方可换一件。理会得通彻是当了,则终此生更不用再理会。(宋·张洪辑《朱子读书法》)
(11)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视人物之影如镜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南北朝·王嘉《拾遗记》卷十)
(12)一片片雪儿休要下,一点点雨儿休要洒。(宋·蒋捷《竹山词·最高楼》)
(13)趱出无数青面獠牙鬼拥住秦桧,先剐一个鱼鳞样,一片一片剐来一齐投入火灶。(明·董说《西游补》第九回)
(14)萐莆,一名倚扇,状如蓬,大枝小叶小,根根如丝,转而成风,杀蝇。(南北朝·沈约《宋书》卷二十九)
(15)大圣慌了,即使个身外身法,将左胁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喷去,喝声叫:“变!”一根根都变做行者。(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三十五回)
(16)老人即时用手一根一根扯断红线,行者方才得脱,便唱个大喏。(明·董说《西游补》)
(17)衔杯微动樱桃颗,咳唾轻飘茉莉香。曾见白家樊素口,瓠犀颗颗缀榴芳。(《全唐诗》卷八百二之《檀香》)
(18)一颗颗,一星星,是秋情,香裂碧窗,烟破醉魂醒。(宋·吴文英《梦窗稿》丁稿之《乌夜啼》)
(19)一颗一颗吃即尽。(五代·《启颜录》)
(20)到了常州,只见前边来的船,只只气叹口渴道:“挤坏了!挤坏了!”(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八)
(21)瑞虹寻了鞋儿穿起,走出舱门观看,乃是一只只开蓬顶号货船。(明·抱瓮老人《今古奇观》)
(22)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李绅《悯农》)
(23)五色舍利,一粒粒皆最后教诲,安得不愿乐流通? (清·金堡《徧行堂集》卷十七)
(24)入水银并花银同煎,以百步断碎,一粒一粒漫入油水,二伏时即成硬块砂子。(宋·《庚道集》卷四)
(25)苕水支支绿,淞云片片黄。(元·戴良撰《九灵山房集》卷十)
(24)李清也料道子孙辈必然如此,预先设下酒席,分着一支一支的,次第请来赴宴席。(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八)
为了更明晰地展现数量重叠式产生的历史顺序,我们将表1统计归并为表2。

表2 数量重叠式词产生的历史顺序
“一一”是最早产生的数量重叠式,例如:
(25)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26)韩昭侯曰:“吹竽者众,吾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曰:“一一而听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
从上面可知,“一一”产生于先秦,“AA”式产生于六朝时期,“一AA”式产生于唐五代,“一A一A”萌芽于唐五代,但仅见1例,至宋代才有所发展。从整体来看,这四种重叠式产生的早晚不同,“一一”产生早于“AA”,“AA”产生早于“一 AA”,而“一AA”产生又要早于“一A一A”式,因此它们的历史发展顺序为:一一>AA>一AA>一A一A。
有些在同一个朝代产生的“一AA”和“一A一A”,前者出现的年代早、使用的频率也高,例如:“一张张”出现比“一张一张”早,前者使用3次,后者1次。但也有极少数一A一A>一AA的情况,例如:“一颗一颗”早于“一颗颗”,“一粒一粒”早于“一粒粒”,“一支一支”早于“一支支”。
如果说“一A一A”是数量词重叠的基本式,“一一”、“AA”、“一AA”是它的变式或省略式的话,那么“一A一A”式的出现应该早于其它几种重叠式,至少是同时出现且用例较多。但是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一一”和“AA”要比“一A一A”出现得早。至于“一AA”和“一A一A”之间则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发展序列:一AA>一A一A ,一A一A>一AA。前一种是多数的数量词遵循的序列,后一种数量词的发展序列则是极少见的。这两种相反序列的存在恰好也说明了“一AA”和“一A一A”不存在简单的基式与变式的变换关系。
即使是在共时平面,几种数量重叠式的句法、语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郭绍虞(1979)[11](44)、刘月华等(1983)[3](89)、房玉清(1984)[12](277)、李宇明(2000)[8](348)、郑远汉(2001)[13](4−11)、杨雪梅(2002)[14](27−31)、孙力平(2002)[15](285−286)等均对此进行过探讨,我们将诸位观点概括如下:“一一”只作状语,表达“逐一”的意思;“AA”一般作主语,表达“周遍”的意思;“一AA”一般作定语和状语,主要表达“逐一”和“数量多”的意思,有时作主语表达“周遍”的意思;“一A一A”一般做状语,表达“逐一”的意思,作定语表达“数量多”的意思,“一A一A”的描写性、逐一性、次序性比“一AA”更强。
无论从历时的产生顺序来看,还是从共时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来看,四种重叠式不存在所谓的基式和变式的关系,它们是四种独立平行的重叠式。各式之所以能在相同的句法分布中表达了相同的语义,是由于句法环境所决定的;在相同的句法环境能够相互替换并且语义不变,只因为这几种重叠式构成了同义聚合关系,我们认为,从能从共时层面进行变换理解的语法形式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衍生发展关系。
三、汉语数量重叠式的类型发展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普通话中四种数量重叠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他们是四种独立平行的重叠式,这还可以从它们各自的产生途径看出来。除了普通话中的四种重叠类型外,汉语方言中还有“A一A”重叠式。下面我们分别论述各种数量重叠式的产生途径。
(一)“一一”。“一一”是典型的数词重叠式。先秦时期由于量词系统并不发达,因而出现关于数量表达的最早的重叠形式就是数词的重叠。假设例 25-26的“一一”是从“一个个”或“一个一个”省略而来的话,那么意味着先秦时就已经有了指人的单位词“个”,但是王力认为先秦还没有指人的量词“个”[16](275)。宋玉柱(1978)认为:“但从断代描写的角度看,仍然可以把它(‘一一’,笔者加)理解为‘一AA’(‘一A一A’)的省略形式,因为它的语法意义和‘一AA’(‘一A一A’)是相同的[2](85−91)。”在特定的句法位置中,二者表达了相同的语法意义,但是从整体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来看,“一一”只表达“逐一”的语法意义而充当状语,而“一AA”(一A一A)则既表示“逐一”的意义,又表示“数量多”的意义,主要充当状语和定语;它们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只是部分重合,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在形式方面可替换而认为他们之间有必然的衍生关系。
(二)“AA”。“AA”式是一个典型的量词重叠式,一般表遍指。这种形式萌芽于六朝,兴盛于唐五代。表遍指的重叠形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石毓智(2004)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汉语表遍指的重叠式的演化进程并认为:“该现象肇端于战国末期,起初只是个别的词汇现象,尔后成员逐渐增多,大约在魏晋时期发展成为一条相对能产的语法规律。然而在魏晋以前,汉语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语法范畴的量词,那时的名词都可以直接受数词的修饰[17](325)。”这种重叠表遍指的语法规律首先作用在普通名词上面,随着量词的发展和量词的广泛使用,量词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名词逐渐的不能再与数词搭配,只有量词才与数词搭配,因此,重叠表遍指这条语法规律的作用对象就逐渐转移到量词上面,之后量词重叠才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认为,“AA”是重叠表遍指的语法规律的产物,不是“一AA”或“一A一A”的变体。
(三)“一AA”。“AA” 表达“所有、每一”的遍指意义,具有统指性。统和分是相互依存的,当我们需要表达“分指”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AA”式前面加上数词“一”,于是产生了“一AA”。 “一”是计数的开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具有天然的分指性和逐一性,蕴涵和控制着“逐量”的特征。能够计数的单位都是离散的,因此在量词前加数词“一”,就表明数量结构所指称的对象是分离式的出现,而不是笼统的出现。“一AA”式因为前面有数词“一”,因而它主要表达“逐一”的分指意义,而分指性的“逐一”义又蕴含着“依次”、“纷纷”、“数量多”等意义,它所表达的意义比“AA”式要丰富,“AA”式可以做主语、定语,而“一AA”式则可以作主语、定语、状语。“AA”式是对“量”笼统性的表达,而“一AA”式则主要是对“AA”式“量”的分离性的表达,着眼于个体。“一AA”式是在“AA”式前加“一”形成的,它出现的动因是表“分指”、“逐一”语义的需要。太田辰夫(2003)说:“又有在名词·量词的重叠形式(AA)型前面用‘一’,表逐指的,这也是唐五代有的。如‘一人人’‘一个个’等的计算方法,从唐开始,在近古很盛行[18](155)。”[18](155)我们认同太田辰夫的观点,认为“一AA”是在“AA”前加“一”形成的,并将它的结构韵律重新分析为“一A·A”。
(四)“A一A”。数词“一”不仅可以附于“AA”之前形成一AA,而且可以嵌入“AA”之间产生A一A,汉语方言中就存在这样一种数量重叠式。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在四川成都(2001)[19](196−197)、湖南冷水江(2008)[20](93−94)、湖南绥宁(笔者母语)三地汉语方言中都存在这种数量重叠结构,这种结构表达“逐一”和“数量多”的意思,兹举成都方言材料如下:
① 个一个的说才听得清楚。
② 堆一堆的萝卜,到处都是。
③ 肉切成砣一砣的。
④ 院壩头停的自行车,排一排的。
“A一A”不是现代汉语方言才有,在近代汉语的文献当中就出现过,但它的使用远没有“一 AA”和“一A一A”普遍,因此在文献中的用例极少,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方言用法,并没有进入权威方言。我们将文献中的例证尽列如下:
(28)太翁阴骘天来大。后隆山、层一层高,层层突过。簪绂蝉聊孙又子,眼里人家谁那。(《全宋词》之刘鉴《贺新郎》)
(29)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诚能条一条编之,法公词讼之断则纷纷,末世之制作皆在,可省而治,道行矣。(明·骆问礼《续羊枣集·附录》)
(29)见则见乱石巉巉,个一个利如刀斧;污泥烂烂,寸一寸滑似膏油。(明·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卷下)
(30)但愿天多生善人,个一个不堕地狱;又愿人多行善事,件一件莫犯天条。(同上)
(31)我只教他霎时间跪的跪,拜的拜,个一个都俯伏在尘埃,方显我雄才。(同上)
(32)三十日,皇上差摆牙喇传旨,在金山住泊船,双一双不许开。(清·《圣祖五幸江南全録》)
我们认为方言中的这种结构不是“一A一A”的省略式,原因有三:第一,轻读才有可能会脱落省略,一般“ABAB”中的第二个“A”才轻读,第一个“A”不轻读,而且这样的形式还经常处于分句的开头,开头的第一个音节很少有轻读的,因此轻读很难产生“BAB”。第二,通过我们上面的考察,“一A一A”在近代的使用频率不高,因此它也很难产生变体。第三,“A一A”具备和“一A一A”一样的功能,它只有一个“一”控制,因此“逐一性”和“分指性”没“一A一A”那么强,“一A一A”的表义更精细化;如果方言表义不需要像普通话那么精细的话,就可以不产生“一A一A”。
因此,我们认为“A一A”是一种独立类型的数量重叠式,是在“AA”中嵌入“一”形成的, 事实证明“AA”中间可以嵌入一个语缀形成“AXA”,这从其它方言量词重叠形式就可以找到佐证,张一舟等(2001)发现成都方言“M 是 M[19](196−197)”,黄伯荣(1996)发现:山东平度有“A顶A儿”、 浙江温州有“A加A”、浙江宁波老城区有有“A打A”、湖南益阳有“A什A”、湖南汝城有“A士A”、湖南湘乡有“A四A”[21](138−146),陈淑梅(2007)发现湖北鄂东方言“A 数 A儿的”[22](42−45),储泽祥(2009)发现安徽岳西“量词+似+量词”[23](218−219),这些重叠式都表达“周遍”或“逐一”的意义。因此,“AA”之间可以嵌入中语缀,那么“一”是否可以作为中语缀?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某些方言中有动词重叠式“V一V”,其中的“一”轻读,语法化为中语缀成分表达语法意义。“一”可以是“V一V”的中语缀,也可以是“A一A”的中语缀,只是语法意义不同。我们完全相信“A一A”是在“AA”中嵌入“一”而产生的,其结构韵律重新分析为“A·一A”。
在汉语中,“一”既可以附于“AA”形成“一AA”,也可以嵌入“AA”形成“A一A”。在不同语言系统中,表达相同语法意义的语法格式的发展可以是不同的,于是在不同的方言中,既表“周遍”意义又表“逐一”意义的不一定是“一AA”,而完全可能是另外的句法格式。上述成都、冷水江和绥宁三地方言的数量重叠式除了“AA”外,只有“A一A”,而没有“一AA”和“一A一A”。“A一A”和“一AA”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完全相同,而又不出现于同一语言系统,因此,我们认为“A一A”和“一AA”是两种平行发展的格式,是相同语法意义在不同地域的语法形式变体,是两种独立的数量重叠类型,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我们推测“A一A”和“一AA”同步出现,“A一A”产生的时间上限在唐代中后期,时间下限在明代,它产生之后并没有进一步扩散开来,只保留在某些方言中。
(五)“一A一A”。 “一A一A”是数量短语“一A”重叠而产生的,最早产生于唐五代,至明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选取了八部明代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金瓶梅》《今古奇观》《欢喜冤家》《封神演义》)和九部清代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施公案》《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镜花缘》《隋唐演义》《海上花列传》)穷尽考察了“个、根、层、颗、张、件、片”七个量词的“一AA”和“一A一A”的运用情况,结果发现,明代“一AA”274条,“一A一A”4条,清代“一AA”223条,“一A一A”42条。从统计结果可知,在近代汉语时期,“一A一A”的使用远远没有“一 AA”普遍。太田辰夫认为:“一A一A”这种重叠形式在近古受到“一AA”形式的排斥多半不使用。[18](155)“一 A一A”主要表达“逐量”意义。我们在上面说过“一”具有天然的分指性和逐指性,当数词“一”重叠时只表达“逐一”的意义,因此,出现两个数词“一”的重叠式“一A一A”比只出现一个数词“一”的重叠式“一AA”,其分指性和逐一性要更强。
“一A一A”在这几种数量重叠式中出现最晚,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量词真正作为一个名词数量表达的必须语法标记,这条规律直到宋元之际才建立,因此数量重叠式要作为一个比较能产的语法格式也应该在宋元之后才能够流行;二是先行出现的“一AA”具有与“一A一A”一样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随着表义精细化的要求,“一A一A”比“一AA”所具有更强分指性和逐一性的这种优势才慢慢凸显出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共时表达来看,这几种重叠式根据句法位置形成不同的同义聚合关系。从结构类型看,广义的汉语数量重叠式有五种类型:“一一”“AA”“一AA”“A一A”“一A一A”;狭义的有三种:“一AA”“A一A”“一A一A”。
从历时发展来看,汉语的几种数量重叠式之间并不存在基式和变式的关系,他们是几种不同性质的重叠式,都有各自独立发展的历程:“一一”是数词的重叠,先秦已经出现;“AA”是量词的重叠,萌芽于六朝;“一AA”属于数量重叠式,产生于唐代,盛行于近代汉语时期;方言中的“A一A”是数量重叠式,应该萌芽于唐五代时期,但文献中的最早记录是宋代(仅见1例);“一A一A”是数量短语的重叠,萌芽于唐五代(仅见 1例),在宋代有所发展,盛行于现代汉语时期。形成了一一——AA—— 一AA/A一A—— 一A一A发展序列。这种发展序列既与词汇史的发展有关,也与语义的延伸有关。从词汇史角度看,数词最早产生,其次是量词,最后是数量短语,相应地,它们的重叠式也遵循同样的时间顺序。从语义延伸角度看,“一一”是完整的数词重叠式,表逐指,“AA”是完整的量词重叠式,表遍指,“一AA/A一A”是不完整数量重叠式,表达遍指和逐指,“一A一A”是完整的数量重叠式,主要表达更强的逐指性,语义的发展遵循了“逐指-遍指-逐指/遍指-强逐指”的发展方向。
[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255.
[2]宋玉柱.关于数词“一”和量词相结合的重叠问题[J].天津: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 1978, (6): 85−91.
[3]刘月华, 潘文娱, 故韡.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89.
[4]胡附.数词和量词[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54.
[5]吕冀平.汉语语法基础[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09.
[6]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3.
[7]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298−299.
[8]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48.
[9]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下册)[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 104.
[10]邢福义.汉语语法学[M].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198.
[11]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册)[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44 .
[12]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M].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 1984: 277.
[13]郑远汉.数量词复叠[J].武汉: 汉语学报, 2001, (4): 4−11.
[14]杨雪梅.“个个”、“每个”和“一个(一)个”的语法语义分析[J].延边: 汉语学习, 2002, (4): 27−31.
[15]孙力平, 刘挺.数量结构重叠的语法功能与分布[J].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 (3): 285−286.
[16]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75.
[17]石毓智.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325−326.
[18][日]太田辰夫著, 蒋绍愚, 徐昌华译.中国语历史文法[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55.
[19]张一舟, 张清源, 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M].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196−197.
[20]李红湘.湖南冷水江方言数量结构“A一A”研究[J].曲阜: 现代语文, 2008, (9): 93−94.
[21]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6:138−146.
[22]陈淑梅.鄂东方言量词重叠与主观量[J].武汉: 语言研究,2007, (4): 42−45.
[23]储泽祥.岳西方言志[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218−219.
The Diachrony Exploration and the Overlapping Form of Quantity
LI Kangchen1, HE Shanyan2
(1.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2.Faculty of Chinese linguistic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verlapping Form of Chinese Quantity , which were debated by the research circle for a long time in China, and all of those synchronic studied were debatable further.Secondly, it explored the generated sequence of Overlapping Form of Chinese Quantity diachronically, and reached conclusion that the four kinds of overlapping form,“yiyi(一一)”、“AA”、“yi(一)AA”、“yi(一)Ayi(一)A” in Chinese 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s with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and variant-form.Finally, it further explored the types and historical gradation of Overlapping Form of Chinese Quantity by combining with the Overlapping Form of Quantity “A yi(一)A” in dialects, and put forward the developing sequence of “yi yi(一一)——AA——yi(一)AA / A yi(一)A——yi(一)A yi(一)A”, which both 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vocabulary and the extension of semantics.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Teaching; Quantifiers; Type the Number of Overlapping
H122
A
1672-3104(2010)05−0125−06
[编辑: 汪晓]
2010−03−14
李康澄(1980−),男,湖南邵阳人,苗族, 湖南科技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方言,汉语语法;何山燕(1975−),女,湖南永州人,广西民族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对外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