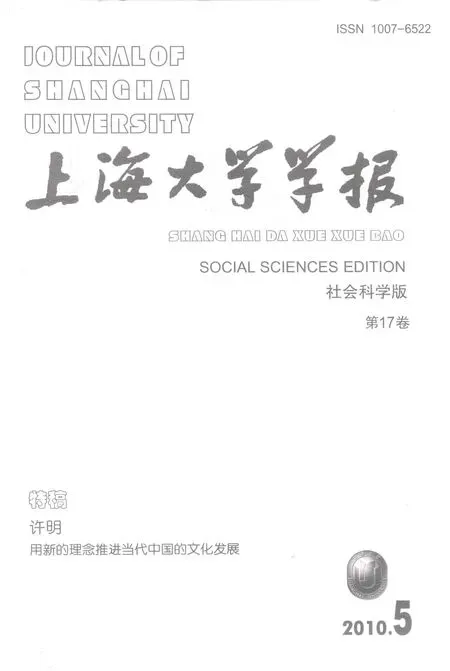风险社会:我们准备好了吗?
——对于转型期国民社会教育紧迫性的思考与应对
邓 伟 志, 孙 抱 弘
(1.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2.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风险社会:我们准备好了吗?
——对于转型期国民社会教育紧迫性的思考与应对
邓 伟 志1, 孙 抱 弘2
(1.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2.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国民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当代中国,本应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驾齐驱的社会教育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所适从乃至明显失重。从多维的视角,在源头上探寻社会教育失重的成因及其后果,探讨可能的弥补对策与路径,从而提升国民应对风险的素质,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确保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一路走好”。在具体的国民社会 (伦理)教育的实践中,首先要注重务实性的起步,这就是:面对社会冲突可能引发的风险,应加强社会共生的教育;面对高科技带来的风险,应进行人文关怀的教育;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风险,应加强现代环保意识的教育。在这些教育中,特别应重视对正面教育有严重阻碍作用的陋习潜规加以清理切割。其次,在实施社会(伦理)教育的过程中,在内容上要注重渐进性、持续性,在形式上要注重多样化、日常化;在目标的实现中也要凸显兼容性,让有助于人类共生共荣的各种理念与行为产生“迭加”效应。再次,鉴于社会分工、分层的客观事实,对于社会精英的教育要求应高于社会大众,社会精英要真正成为社会之“师”。社会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与城市现代社区建设相伴而行,从而实现刚柔相济——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配套。
转型风险;国民素质;社会教育
说起教育,我们习惯于将其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于前两者的理解,界线明确、内涵清晰;而对于后者,则因包容性大,反而不易界定,社会各界好像都颇为关注,好像也有众多的参与机构,但却分散而无序,缺乏明晰而系统的指向目标,甚至将其简化为某种知识教育或拔高为个人道德修养。这样,在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极为重要的社会教育却给人以一种好像无处不在却又若显若隐、似有似无的感觉,而且事实上也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之中。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今天,社会教育的失重已经产生了什么后果,原因何在,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教育,如何进行适应中国转型社会迫切需要的社会教育,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系列问题。
一、问题探讨的假设性分析框架
为了超越简单的因果性直线思维,努力以多维的关联性复杂思维探讨问题,本文综合多学科的理论,以人为本,试图从人的“素质发展、日常生活、文化传承—教育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演进,以及这些层次性、阶段性演进之间——自身和相互的对应关系中,展开对国民社会教育之意义、目标、实现路径和可整合吸纳资源的探讨。由于将问题置于多维的视角下,使我们能在张力中思索,肯定会有助于问题探讨的深广度。但是本文的分析框架只是一种假设,还需要实践与经验的反复验证,所以不敢妄言建构理论体系,只是有此一说而已。
对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 (见下表),解释如下。

表 1 人的发展、教育、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层次与关联
首先,关于人的素质发展机制,笔者早已有专文论述,①参阅孙抱弘:《社会环境·接受图式·养成路径》,载人大复印资料《青少年导刊》,2002年第 2期。该文从对“素质”概念的厘定入手,运用场论、机制论、发生认识论、生命历程理论、行动分析理论、接受理论等对素质养成的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诸结构要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从内部到外部、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梳理和解读。这里不再赘述。本表所强调的是:如果以人的成长发展为分析问题的立足点,那么,文化传承—教育、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是对人的成长发展起核心作用的要素,不同层次的要素决定着人的素质水平的不同层次,当然这种影响必定是双向互动的。这里先对表中的部分内容略加阐述。
从人的伦理道德素质的发展看,做人者可能只是知道德,只能被动地遵守各种社会规范,而做好人者才会自觉践行各种伦理规范,唯有高尚的人才会在做好人的基础上,追求德性修养。
从人的接受教育的层次看,接受知识技能教育主要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接受了社会伦理教育的人,才可能和谐地融入社会生活,只有产生了信仰追求的人,经过自我完善,才会领悟人存在的意义。
从日常生活的水平看,物质生活满足的是人的各种感官的需求,这是一切动物都有的满足而不是人特有的生活需求,换句话说这种生活不是以人为本的;伦理生活使人和谐地与人相处,得到各种感情的满足,由此体现出人的特殊需求,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生活;精神生活体现出人的一种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人的生活的至高境界。
其次,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人的素质发展、受教育的水平、日常生活的状况和宗教信仰的层次都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各个要素的同一发展阶段之间则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对应性。也就是说,当个人接受了知识技能教育后,他实际上也就接受了生存的训练,就有能力立足于社会,有了物质生活的保证,能够“为人”了。不过,这只是人的素质发展的初级阶段,“造就”的是一个充满了物性的不完全的人。所以,个体还应当继续发展,只有当我们完成了社会教育——笔者认为:就现阶段中国的社会教育而言,此教育的重点在教人如何处理各种伦理关系特别是公共伦理关系为主,所以也可称其为“社会伦理教育”——提升了人际的交往理性和契约理性,能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向善的好人,才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同样,只有确立了理想信仰的人,才有真正的精神生活,才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当然,理想信仰的教育应当提倡的是非工具性的尚善尚美的德性追求,是对无功利的人格境界的崇尚;由此,这一教育过程也必定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远离了“被”的过程。
最后,表 1中将宗教分为三个层次,这是按照黑格尔的分法,[1]其中自然宗教实为原始宗教,包括迷信、巫术在内,因此更多的是无知状态的盲目“信仰”,这与表中处于初级阶段的教育要素并不存在对应性。本文关注的是处于中间层次的实用宗教,这个层面上的宗教伦理体现出一种工具性的对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安顿的关注和影响,当然,本文并不是提倡大家都去信仰宗教,但是,在宗教伦理中的这种让人向善的劝诫与社会教育中教人“做好人”,以及主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利共存的工具理性,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由此便可能成为国民社会教育中吸纳整合的宝贵的非物质资源。至于宗教伦理精神中还有更高层次的无功利的价值性的劝人向善的追求,其与理想信仰教育中的德性追求也有相通之处,这对主流的理想教育也应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二、面对失衡的国民素质:社会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今天的国民教育缺失了什么?
社会转型期,人们在关注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问题的同时,正在越来越关注国民素质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人们既不得不承认又困惑于以下现象:“信仰失落、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行为失检”是如此普遍,不少高等学府刑案频发,一些政府高官纷纷落马,有的人连道德的底线亦已放弃。人们开始追问:一个五千年的文明礼仪之邦、一个理想信仰教育的投资大国,何以如此?!与此同时,无论是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还是已经本土化的佛教,其信徒与日俱增,其传播范围、影响程度也日甚一日,信徒们对自身行为的自觉约束、对宗教化伦理的虔诚敬畏,也是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一时间,宗教信徒成了坚守社会道德底线的中坚力量。面对这些现象与追问,我们必须作出解答。
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综合的,不过从教育的角度去看,或许能窥见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人类的教育活动发展至今,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解决人的生存需求的知识技能教育,第二是提升人的交往理性和自觉遵奉伦理规范的社会教育,第三是提供人的精神寄托、德性追求之需的理想信仰教育。
那些在转型期发生的诸如“伤熊事件”、“马加爵凶杀案”、“毒奶粉案”以及“倒钩事件 ”、“躲猫猫案 ”、“范跑跑新闻 ”等个案 ,还有大量的类似事件,如果追究其原因,那么往高处说是因涉案人员“信仰失落、德性低迷”而产生;往低处看,则无不是丧失理性、毫无社会责任感与职业精神而直接造成。如果从教育目标追求和文化传承职责的立场加以分析,则恰恰就是上述社会教育的缺失,以致任由传统社会落后文化中的丛林规则、潜规则泛滥肆虐而形成。如若进一步追问产生的历史缘由,显而易见,这是由于近代以来,出于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革命推进的紧迫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知识技能的学习教育和理想信仰的宣传灌输,而冷落甚至否定了社会教育,使用思想史研究者的话语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乃至用革命取代了启蒙。由此,尽管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少有识之士为各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呼吁呐喊,但很快就归于沉寂了。在相当一个时期,理想教育也的确是完全取代了社会教育,以至于把一切的人际关系完全简化成了阶级关系。
不过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有意味的是,各种宗教伦理中具有宽容、妥协与合作内涵的理念,却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无声地传播,悄然发挥着约束人性之恶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填补着社会教育的缺失,在实际上满足着人们日常伦理生活的需求。今天,我们主张加强社会教育,应该肯定一些宗教伦理主张的合理性,并与之形成互补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漠视或放弃社会教育对于当代伦理生活的指导,那么各种宗教伦理必定迟早会填补这一生活领域的所有空白点。
最后,我们强调转型期的社会教育的紧迫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性考量,这就是全体国民应如何面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件的问题。就当代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项,存在着弥补的必要性。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充满着各种风险,面对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如果当事的各个方面都不知所措,任由情绪化对抗的发展,都可能使小事端变成大动荡;而在日常的社会职业活动中,缺乏社会教育的人们,往往毫无公共意识,习惯于用私人立场、情感去处理公共关系与公共利益分配问题,以至于在一些事关公共安全的工作岗位上职业精神沦丧、恣意妄为,进而人为引发各类灾害,破坏环境,危及他人生命。这些状况无疑都呼唤着一个独立于知识技能与理想信仰的、自成系统、基础理论和行为指导相配套的国民社会教育。
(二)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教育?
本文定义的社会教育,基本等同于现代教育学“大教育”的概念,但对其内涵则略作丰富,①参阅侯怀银等:《‘社会教育’解读》,载《教育学报》2007年第 4期;张少军等:《社会教育的实践方式研究》,载《外国教育研究》2006年第 12期。本文在对以上文章的摘引、解读中,在本文所作的定义里加进了“文化传承建设”以突出定义的历史纵深感,同时呼应文中的相关讨论。这就是:一切文化传承、建设和现实社会生活影响于人的身心发展的教育。社会教育的目的,不仅指人才的培养,还包括群体的教化和个体良好心态的养成。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教育的意义与内容必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由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转型期的国民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中,现阶段的社会教育的定位,应该是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想性大目标的前提下,考虑目标实现的阶段性、可能性,特别是面对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更要注重务实性的社会教育,要在历史文化传承与现实社会建设的交汇点上,根据人的理性的发展规律,通过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有针对性、渐进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社会教化,推进全社会成员养成适应现代公共社会生活的良好心态和基本素质,推进现代和谐社会建设。
在此,我们应当指出,上述的社会教育内容,在当下的各类教育活动中,呈现着一种“碎片化”和“空转化”的状态,也就是只散见于知识技能和理想信仰教育之中,尚未自成体系,也没有核心理念的支撑,更未成为可上承理想信仰教育、下接知识技能教育、相对独立的教育层次。所以,全面推进系统而独立的社会教育既显得紧迫却还尚待起步。
(三)社会教育与理想教育的区分与关联
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期之社会教育最实际的目标就是确立正确面对日常公共伦理关系的态度与行为取向。这样的教育,在公共生活缺乏的传统社会中显得可有可无,而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空前扩张的转型社会则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强化凸显社会教育的意义与地位,不是要取代或淡化理想信仰教育,而是要更有效地进行理想信仰教育。
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分析本文所定义的社会教育与现行理想教育的区别与联系。首先,区别一:就日常生活的层次性而言,如果将人类日常生活分为物质生活、伦理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层面的话 (见表 1),那末,社会教育主要是解决如何面对伦理生活的问题,而理想教育更多的是思考精神生活的问题。伦理生活面对的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原则与规范维护,而在转型社会中,由于社会公共空间的快速扩张,社会教育的重心更多地就必然偏向日常公共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其次,区别二:就人的成长与发展的阶段性而言,如果将人发展的层次分为“做人、做好人,做高尚的人”(见表 1)的话,那末社会教育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从做人提升到做好人”,而理想教育自然是希望或要求人们成为“高尚的人”。最后,两个教育的紧密关联:日常生活的三个层面与人的发展的三个层次紧密相连。我们今天加强社会教育,不仅是为了提升国民的素质和理性,转变滞后的习惯、价值观与心态,以安度社会与自然风险;同时,更是为了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德性,使更多的人有可能成为高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教育是在为理想教育铺台阶打基础,使理想教育进行得更扎实、更有效。如果缺少了这样的铺垫失去了必要的台阶,理想教育极可能踏空,甚至走向反面。所以说,社会教育是理想教育的必要前提,理想教育是社会教育的自然延伸;离开了社会教育的理想教育将成为空中楼阁,失去了与理想教育联系的社会教育有可能迷失方向。
三、面对风险社会:
社会教育的务实性起步
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失衡的国民素质和失重的社会教育,这三者的迭加将大大加重社会转型的成本,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之一,就是认清风险来源,实现社会教育的务实性起步和优化实施路径。
(一)中国转型社会的风险
现代社会或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往往被称作为“风险社会”。这主要是因为较之传统社会,转型社会的公共空间日益扩展——高科技的网络技术更使之呈现几何级数的扩展,由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交往、接触无限扩大,并且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往往蕴藏着、潜伏着种种风险。如果不把可能的外来侵略估算在内,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向:
第一,社会冲突引发的风险
转型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原来的社会利益格局亦随之变化以至失衡,进而因为社会建设欠账和社会政策的不到位,而产生社会冲突,引发风险。这些风险由于现代传媒工具的推波助澜往往极易从局部迅速扩展至全局。
第二,高科技带来的风险
任何一项高科技的成果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因为人类在进行任何科技开发之时,大多出于良好的愿望而追求其正功能、忽视或无视其负功能,从核物理研究到网络开发概莫能外。由此,这也就给人类带来了风险,更因为种种利益的驱使与不负责任的运用,这些高科技引发的风险具有潜在性与突发性。特别是当其与其他风险纠缠并发时,其危害之烈度将成倍增长。
第三,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
这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风险,不过在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猖獗的当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对生态的严重破坏而使得灾害频发。这种灾害的风险,会在有无相应社会教育、国民素质高低不同的国家中引发不同的后果。这在近日同样发生地震的拉美国家海地和智利就得到了印证。
(二)社会教育的务实性定位
面对转型社会风险的国民社会教育,应该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这一目标来定位。也就是说要减少和安度风险,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和谐的或者说是互惠共生的社会生态,而构建这一社会生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通过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教育与实践,从而形成互惠共生的共识。这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通过社会教育与社会实践,逐步提升人的理性,将国民生而俱有的求生存发展的个人理性,提升为求群体互惠共生、和谐发展的公共理性。如果用传统的思想道德建设的话语来表述的话,这应该是一种肯定独立人格意识与追求基础之上的新集体主义。
国民的社会教育是面对全体的大众教育,这就决定了其务实的特点。由此,也决定了其本土化的出发点;就现阶段而言,大致应从两方面展开,概括地说就是:清理地基去牵挂;打好基础定重心。
清理地基去牵挂是指社会教育的定位是否务实,无疑还要考虑到教育所面对的特定对象。应当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并非一张张“白纸”,也不是一个个生活在理想社会中的无牵无挂之人,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置身于日常生活、有历史文化承载、有现实社会联系的有牵有挂之人。由此,我们的社会教育必定要对这些牵挂作出“要”与“不要”,为何“不要”,如何“不要”的回答。这也就是说,要通过系列的、多种形式的教育,去摆脱种种消极的、阻碍国民确立互惠共生理念、提升社会公共理性的滞后文化与心态的羁绊,我们才能在充满风险的转型社会中“一路走好”。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那些滞后文化与心态之牵挂的负面影响将不断增长,进而会大大地加重改革的成本、恶化社会生态,以致使各类风险被人为“放大”。为此,梳理、评判与切割滞后文化与心态,提升人的公共理性,增强互惠共生的自觉意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教育,应尽早尽快地推展。唯此,才能放下那些阻碍我们深入改革的人治意识、臣民心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已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的陋习、潜规则等“牵挂”,从而“轻装上阵”。
综上所述,以去牵挂、清地基为前提,整体性提升国民公共理性应是当今社会教育的基本定位。
打好基础定重心是指有效的社会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建设阶段应体现不同的侧重点。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无疑将大大激发人的竞争能力,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不断积累,但是这种竞争应当是有序的,更不可陷入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泥淖。由此,社会教育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阶段的侧重点应该是:适时将人——国民与生俱来的适者生存的低水平的个别生存理性,提升为互惠的、较高水平的群体共生理性。通俗的表达就是:我们要适时将那种自在的只能“共患难”的低水平群体意识,提升为自觉的、能够“同富贵”的群体意愿——既要共享改革成果,也要同担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责任。以此为侧重点的社会教育,才可平衡社会利益,改善社会生态,共建和谐社会。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面对社会冲突的风险,进行社会共生教育
首先,反思与梳理文化传统:对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利于人们和谐相处、互惠共生的理念、心态乃至集体无意识,要通过教育和自我教育,以进步的代替落后的。其次,要改善社会生态,坚持社会和谐的立场,对以往误解、误读的一些社会理念进行正确的解释或者说是重新认识,这些理念是:改良、渐进、让步、妥协、和解等,要辅之以中外历史的个案加以深层次的解读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教育,才有可能使社会的各个人群、各个利益体尽管存在差异乃至矛盾,但却都有容忍之心、尊重之意,并能互留余地以求共生、共荣、共赢。这应是我们安度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最佳路径,也是当下社会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
第二,面对高科技的风险,进行人文关怀的教育
社会教育应帮助国民以人文关怀的立场去认识和面对与高科技相伴相生的高风险,防止片面地认识与发展科技,摆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摆正科技发展和人类安全的位置,强化现代公共意识,遵奉风险防范的各种公共规范,高科技高风险行业的从业者更应有执着的职业精神与职业规范意识。
第三,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风险,加强地球环保意识教育
地球村日益拥挤,作为地球人都应有高度的环保意识。同时,要更新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卫生理念,比如把自觉基础上的“不扔垃圾”转变为“分类处理垃圾”等等。从而在科学、理性的层面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自觉地维护好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园。
(三)社会教育路径的思考
当下的社会教育应在吸纳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拓展时空效应,注重日常绩效。由此,本文对教育的实施大致有以下一些思考:
第一,内容上注重渐进性、持续性
渐进性是指教育内容要确定低起点,从“不要”再到“要”,从相对消极的“不做XXX”开始逐步走向相对积极的“要做XXX”。概括一句话就是:先清理地基、打好基础,再建设大厦。
持续性,就是教育不靠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大呼隆”,尊重文化变革的自身特点,遵循观念转变的韧性规律,重在坚持不懈的小步子教化,重在社会生态改善过程中的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第二,形式上,注重多样化、日常化
当今社会教育的多样化立足于信息时代的传媒工具及传播形式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大大地有助于最佳教育效果的获得。诸如电视讨论、电台对话以及网络交流等等形式,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特别是这类参与式的大讨论是对以往传统的教育形式的冲击与超越,无疑应成为未来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乃至主要形式。不过,目前这类传播形式似乎还仅用于应景式或热点式讨论。我们所要进行的社会教育,因其内容的深广度、系统性和专题性,就决定了在运用这些工具与方式开展社会教育方面还有很多开拓性的工作要做。
转型期的社会教育因其对象的大众化,也就决定了其方法乃至内容的日常生活化,除了以上的对话讨论形式外,还应运用多种的艺术手段,尽可能做到教育艺术化、艺术教育化,将社会教育的理念化入一些艺术形式、化入细微的艺术情节。清口相声这一类新兴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无疑是此类内容的最好载体,社会教育的日常生活化应充分运用此类载体。
第三,教育目标追求的兼容性
当下的社会教育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生活态度与现代公共伦理生活规范的教育,基本上不属于精神生活指导,也非理想信仰教育,其务实性特点在伦理生活层面上与宗教伦理文化有不少对应之处,而在较深层次的向善层面上也有相合之处。现有的不少实证调查也证明大多数的宗教信徒的信教水平还停留在生活态度层面,尚未达到精神信仰层面。所以,客观上在日常生活提升人的理性方面存在着实际的互补功能。然而,由于封闭的文化传统中长期积淀的排外心理和“恐教”心态,也由于极少数传教士及其机构以传教之名对中国政治的干涉而留下的历史“阴影”,这种显在的互补功能并未产生“迭加”效应,有时候甚至处于抵消状态。作为社会教育的宝贵资源和潜在的互补功能,如何使资源能尽其用,我们应该展开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与更高级别的政策协调。本文认为,至少在社会共生、人与自然共生等意识理念与行为指导上,还是有可能实现思想资源整合与互补功能发挥的,进而让这些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成果为不同信仰者所共享。
四、实施社会教育的若干可操作性建议
在探讨了转型期国民社会教育的背景、目标与路径之后,我们就社会教育面对不同群体的推展,提出几点可操作性的建议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关于大众的社会教育
进行大众化的社会教育就是为了一小步、一小步地整体性提升大众的理性水平,提升遵奉应对社会与自然风险的社会公共规范的自觉性。
具体地说来,就是要在日常生活的理性化需要与大众的合理性需求的结合点上,进行应知、应戒的教育与自我教育。
所谓应知,就是运用多种传媒手段,传播进步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更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传播健康的、进步的日常生活态度,一方面养成和谐、共生、共荣的理性心态。前者可以依据衣俊卿教授①衣俊卿教授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主要研究文化哲学,是中国学界最早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学者之一,并主编出版了中国学术界第一套日常生活批判丛书,其论文《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专著《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都产生过很大反响。衣俊卿的研究特别关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文化启蒙和现代教育事业,建立理性的和人本的新文化精神对民众的普遍的启蒙机制;建立民主化和理性化社会体制对民众的普遍制约机制,遏制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对非日常活动领域的侵蚀,为自由自觉的非日常主体的生成提供适宜的条件;通过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深刻的社会重组,使普通民众积极地接受开放的、现代化的、城市化的生存方式所内含的非日常价值观念和新文化精神,建立现代化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民众的普遍的教化机制。衣教授的研究为我们进行社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涵。等关于日常生活研究的成果[2]以及社会学关于生活质量的理论见解,加以通俗化、个案化的处理与传播;后者则可以胡守钧教授“社会共生论”②胡守钧系复旦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走出轮回》、《走向共生》,在其最新著作《社会共生论》中提出: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所组成,和谐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社会进步就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胡教授的这些思想应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的一系列研究内容进行通俗化的改编与传播。[3]其他关于应对自然灾害和高科技风险的知识,也可以通俗读本以及多样化的方式加以传播。
所谓应戒,是指那些应当戒除的、阻碍和谐社会建设、恶化社会与自然生态的价值观、心态和陋习乃至潜规则。要推动进步的文化建设,就要从否定、告别滞后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做起,这应成为大众的共识与自觉的文化取向。这方面的实际操作,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滞后文化有其共性,所以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适当学习引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比如秘鲁的“发展十诫”,以及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的一些做法。[4]第二,由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自身的滞后成份,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王学泰③王学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长期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系中国大陆最早系统研究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学者,70万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2007年版)是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慎之先生认为其研究意义在于“发现另一个中国”,这一研究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产生影响。王教授对《三国》、《水浒》及其人物的批判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刘再复、孙绍振等著名学者都在近两年著文深入评判这些古典作品的文化内涵。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可吸纳为社会教育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游民文化的深入批判与切割。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加以提炼和通俗化处理,通过讨论、对话逐步梳理、批判和切割那些反文明、反理性、反社会的心态、潜规则和陋习,并以“应戒”的形式诉诸大众。[5]第三,在中国百年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不少属于启蒙式的“应戒”,劝人向善、向美、破除陋习的民歌、民谣,也有不少曾经取得相当成效的社会教育理论思考和实践模式,由于民族救亡的冲击与政权的更迭,这些“遗产”处于湮没休眠状态,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似乎还有重新整理并加以系统化处理和科学转型的价值。
此外如前所述,鉴于各大宗教在民众中实际存在的现状,我们认为还是要超越对宗教的各种片面认识、极端思维,以发挥正传正信之宗教引人向善的正面功能,以及与我们要进行的社会教育的互补功能。为此,我们建议可将“宗教伦理常识”作为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大众进行关于宗教的正确认知教育,通过一定的实践摸索,普及对宗教的正确认知,普及与社会伦理教育相通的基本普世伦理价值的了解,让社会教育与宗教教义关于日常伦理生活正确态度的传播效应得到迭加,甚至还可缓解乃至消除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对立情绪和紧张关系。[6]这个教育对于那些自认为信仰宗教,但其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的群体而言尤为必要:有助于防止因盲目性而引发狂热性,进而违背宗教伦理精神的根本宗旨。
(二)关于精英的社会教育
任何时代,社会教育的核心对象都是社会精英——尽管其边界会有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吏为师”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吏”仍是现代科层制社会中社会精英的骨干部分,所以对这部分群体的教育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成败,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本文认为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就政治身份而言,至少应当包括各级党政干部、各级党代会和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和民主党派干部;就职业身份而言,应包含各级司法执法者、律师、教师、新闻、科技及医务从业人员,企业家与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就教育程度与职称而言,则包括大专以上、技术员以上的知识分子。以应知、应戒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应当是“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新知、告别旧知,建设先进文化、切割滞后文化”的过程。作为社会精英,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应当更自觉、更系统、更深入、更持久地经历这样的过程,真正成为全社会之“师”;另一方面,对于这一群体而言更要强化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的教育,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和民族的脊梁。进行这样务实的直面问题的社会教育或许能使我们超越因定位过高而日渐空洞化的种种理想教育的窘境,在一个新的更现实而牢靠的立足点上转变社会文化心态,稳步提升国民的现代素质。
(三)作为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教育
转型期的社会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当代中国建设新文化、告别旧文化的历史进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传“新知”,更是为了塑“新人”。这样的社会工程无疑应当“整体推进”,应当融汇于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贯穿于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从外供变为内需,从自在变为自觉;更应当与“四个建设”齐头并进、互相呼应,也应当与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和大城市现代社区建设相伴而行、刚柔相济。
鉴于“四个建设”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国民素质的实际水平,也就是离不开以提升国民素质为宗旨的国民教育;所以,随着刚性的各类硬件建设的深入推展,柔性的人的素质的发展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只是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投石问路性的初步探讨,更深入的理论探讨、更切实的社会实验还需我们以更饱满的精力、更持久的努力去不懈地进行。
[1]邓晓芒.在张力中思索[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41-43.
[2]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胡守钧.社会共生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塞缪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64-365.
[5]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6]卓新平,等.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globalmodernization,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But,in contemporary China,social education,which should go hand in hand with schoo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falls into inaction for various reasons,and even loses weight evidently.This essay,from the perspective ofmulti-dimension,tries to probe into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osing weight in social education from the source,as well as the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and path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risk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ing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can"go well all the way".Therefore,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for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or ethical)education,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agmatism,that is,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social symbiosis to face the risk of social conflict;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to face the risk of hightechniques;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moder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o face the risk of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In all these kinds of education,a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first be paid to cleaning or cutting the bad habits and potential regulations thatmay counteract seriously the positive education.Secondly,in the processof implementing social(or ethical)education,the content should be progressive and continuous,and the form should be varied and routine,and the goal should also highlight the compatibility,so as to be helpful in producing a"superposition effect"for the ideas and behavior of symbiotic human.Thirdly,in view of the objective facts of social division ofwork,for the demand of education,social elites should be higher than general public,so as to turn social elites into true"social examples".Finally,as an important part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social education should accompany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villages,small towns and modern communities,which have appeared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new century,so as to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firmness and flexibility——the complementation of hardware construction and softwa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transitional risk;national quality;social-education
(责任编辑:周成璐)
The Society of Risk:Are We Ready for It?——The Thinking and Response on the Urgency of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DENGWei-zhi1, SUN Bao-hong2
(1.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2.Center of National Spirit and Quality,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200020,China)
C913.4
A
1007-6522(2010)05-0016-11
2010-06-2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9XAJ001)
邓伟志(1938- ),男,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