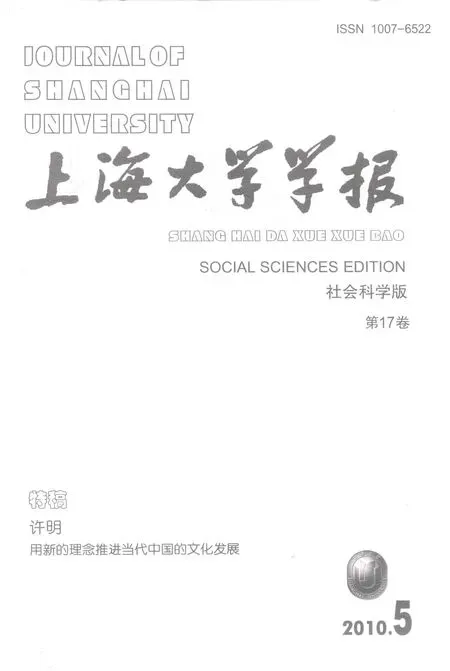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朱 新 山
(上海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上海 201701)
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朱 新 山
(上海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上海 201701)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在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尤其是作为中介和上下缓冲的绅士阶层发生剧烈分化与蜕变。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有上升渠道遭遇制度性解体,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绅士阶层的外流与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的宗族组织机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失衡,陷入总体性危机中,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绅士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社会结构;传统乡村;绅士;解体
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组织机制
1840年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受到巨大冲击。1905年科举制废除,作为乡村社会结构定型力量的绅士精英向上流动的路径被切断,绅士阶层发生分化、蜕变,中国乡村社会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
在科举制废除前的典型传统乡村社会里,处在社会底层的是无数生活在村落里的独立小农,他们与国家的联系是通过绅士精英,在这里,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这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得以长久维持的秘密所在。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套相当发达和完整的集权化的行政科层系统。但这种集权型的政治,却是建立在由小农所形成的分散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个并存排列在无数村子里的独立小农。[1]328
和大庄园相比,小农是较易控制的税收源泉,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政治的威胁也很小,因而历代新朝的开始,多扶植小自耕农的发展。[2]86公元 5世纪以来的均田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小自耕农纳税当兵,此原则被后继朝代所沿袭。[3]182除政治上的限制外,经济、社会等因素也制约着地产的集中。晚清,中国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人均耕地面积的缩小,如鲁、冀两省明初人口共约 700万,1800年增至约 5000万,两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则相应地从近 20亩递减至 4亩。[2]90中国的地产更因传统的多子继承制而趋小型化,一个小地主在几个儿子一次分家后,即可下降到自耕农的地位。
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伴随的,是财富的社会分散掌握和各个农户的自行运营,两者结合恰好化解了要求国家采取行动的压力。除防止地权集中、保持经济平衡外,国家基本上不干预经济运行。中国传统国家因而一般采用小政府模式,正式机构很难深入乡村基层,只能到达县一级。
赋税征收是乡村和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叉点,中国是唯一从公元前迄至 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种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3]47明清两朝都限定和严格坚持低税率,国家从低税率中寻求道德信誉。但是,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行政费用。除窘迫的财政限制了国家的能力外,国家机构有限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制约着国家权力的下渗。从汉朝到清代中叶的两千年间,相继各朝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并未增加,而中国的人口却增长了 5倍。在汉朝末年,一个县官管辖 5万人,到清末却要管30万人。常设民政官员不足,帝国的行政机构日趋浮在面上,并不断削减了它的地方行政职能。在唐以后,政府放弃了对城镇集市的官方管理,停止了对“商务的严密控制”,并逐步不再“正式过问当地的事务”。[4]
这样,由于小农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其附着在土地上,安土重迁,聚族而居;同时,由于帝国权力高踞于地方社会之上,统治者便设计一些措施来诱导民众实施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以使那些作为同盟者并拥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绅士能够管理地方民众。传统乡村在组织机制上,就体现为绅士主导的宗族自治。费正清明确指出:“王朝高居于地方官僚统治之巅,而在官僚统治下面则通过宗族关系和绅士领导集团的忠诚来维持对地方的控制。”皇帝的官员从来不去大多数中国人民居住的乡村,“传统的中国在地方一级是受扩大了的家庭或者说受宗族的支配。”[5]宗族机制得到国家法律上的支撑,法律总是维护族长、家长的威信,并按亲属关系身份进行处罚。
传统中国在治理结构上就有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地方权威 (乡绅,其管辖权在乡村以下单位),一是官府权威 (衙门,主要在县以上区域活动)。这种治理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两种情况的结合: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管辖区域实际治理权的分离。在基层社会,地方权威控制着地方区域的内部事务,他们并不经官方授权,也不具有官方身份,而且很少与官府权威发生关系。表面上,中央下达政令,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正规渠道贯彻着帝国的整体秩序,但在实际运作中,经过各级人员中介变通处理,帝国秩序并不能真正触及地方管辖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默认并谨慎对待管制领域的边界,除非在基层无法处理的事务才上达官方。[6]18地方权威的自主管辖权没有受到严重挑战,它们各成一体。虽然正式官制制度并没有承认这种分治局面,但事实是,分治的迹象随处可见。官制秩序与基层自治经多年磨合,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安全的隔层,即身处官民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绅士集团。
绅士是传统中国非官非民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他们享有制度赋予的特权,包括参加特殊的礼仪、免除徭役、不受刑罚、减税等优待,并有特殊的生活方式。[7]他们知书明理,在乡村建立起象征资本,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组织,提供社区保护所需的庇护关系,承担起社区秩序和社区凝聚的公共责任。绅士借助自治机制,填补了县衙与农户之间治理上的真空,成为官民中介,既是官治民的工具,又是民对付官的代表。
绅士主导的宗族地方自治机制,达到了对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都有利的互动均衡,从而形成传统乡村的超稳定结构。首先,宗族地方自治大大简约了国家的管理范围,确保传统中国始终维持间接治理的小政府模式,防止了国家政权的过分庞大。其次,宗族组织通过“守望相助”、“同族相恤”,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和帮助小农抵御天灾人祸。再次,宗族自治与国家的科举制相配合,为绅士提供了上下活动的大舞台。最后,绅士借国家获取特权与地位,国家赖绅士维持基层秩序。绅士利用自身优势和宗族自治抵制国家的渗透,反过来讲,国家也不允许绅权膨胀和宗族自治过分扩展从而对国家权威构成挑战。小农是国家理想的征税和征兵对象,传统国家也维护小农的私有财产权,限制其他社会势力对小农田产的侵夺。
二、乡村绅士的分化与蜕变
传统中国的国家、绅士和小农三层结构形成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一是由皇帝、职业官僚组成的政治系统;一是由绅士和小农构成的社会系统。两个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分化是相当清楚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互不干涉。社会系统是整个帝国体制的基础,绅士在三层社会结构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农民起义打击的是帝国的官僚机构,而很少将矛头对准绅士阶层。皇冠虽然可以落地,但绅士与小农的结构关系依然可以保存下来,帝国体制可以周期性地得以恢复与重建。[8]绅士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绅士力量的稳定、兴衰与向背,直接影响着帝制的稳定与传统社会的走向。
“身份建构包括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既需要群体自身对其身份的主观认同,同时也需要客观外在于群体之外的社会性建构”,[9]而有时后者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在新学堂取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中,作为传统社会基础的绅士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科举制度废除,原有上升渠道制度性解体,逼使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当时尚长期乡居的山西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于胡底耳。”[10]131-132社会的变局,清政府重商政策驱诱,绅士从商一时成为风尚。时局变动客观上也推动了乡绅从军。一边是社会动荡,军队地位提升、物质条件优厚,一边是正途雍塞、中式无望。当时,贫民子弟当兵为糊口活命,士绅富家子弟则以选择军官为利禄捷径。[11]随着新学影响力的增强,绅士也在不断向新学界靠拢。他们通过新学教育,蜕变分流到近代性质的不同职业群体。绅士阶层的分流,未能对传统体制起到培根固本的作用,相反,他们日益成长为各种离异的力量。绅士从商和商人社会地位的跃升从整个社会基础上瓦解了传统社会“士首商末”的等级身份结构。实质是以近代文明内核的“平等”精神所指引,将中国社会改组引入社会平等取代社会等级的历史轨道,最终使包括清朝贵族在内的特权阶层丧失合法性基础。乡绅从军也不是一曲福音,新军吸引了不少乡绅,但新军思想开明,倾向革命。辛亥革命“事实上是由新军发动的,而且大部分新军站在革命者一边”。[12]449绅士在新式学堂中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所接受的民主、平权观念更是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
时局的变动,科举制的废除,还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费孝通曾指出,“在我们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1]357随着城市近代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乡村绅士向城市的流动逐渐加剧。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阶层被迫进入新式学堂,接受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学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新后,只能在近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才能寻找到适合自身专业特点的社会位置。这样,有才之士从乡村不断流出,费孝通所称的中国乡村的“社会腐蚀”[13]95因现代化过程不断加剧。彭湃在 1926年说:“廿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14]杨开道大约同时也观察到,一方面是农村最缺“领袖人才”,而乡村读书人向城市浮动已成“普通潮流”:“一般有知识的人,能作领袖的人,都厌恶农村生活,都放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农村社会费了金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本想他们来作农村社会的领袖,来作农村社会的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教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活?”[15]“社会腐蚀”卷走了“上层的养分”,乡村大地日益荒芜。
绅士阶层的外流与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作为社会中介力量的绅士阶层,在官、绅、民三层结构中,借助于科举制和等级制,成为社会流动的定向所在。绅士阶层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的官吏队伍提供后备力量,而且也持续不绝地吸纳平民阶层成员补充进来。绅士阶层稳定的继替常规,保证着基层社区领导权有赖于绅士阶层。科举制度消亡后,绅士分子向城市的流动和新式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滞留,使得一向把持乡村政权的绅士阶层失去了最基本的力量补充,由此造成了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毛泽东 1930年在江西兴国县永丰区看到,当地管理公田的“公堂”,“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他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而“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因其田产“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从中剥削”。[16]1935年河北濮阳某村的一份调查报告说,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于旧式知识分子、家族长及一小部分地主的手中”。“现在的村长、佐、里排长,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枣行、盐行的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在该村的权势转移中,新兴掌权者受教育成分已明显降低。[15]山西举人刘大鹏也看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10]336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与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先前那种保护人型的村庄领袖纷纷隐退,村政权较为普遍地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相反,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赢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17]民国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关系急剧恶化,社会骚动变乱迭起,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乡村政权力量的蜕化。
三、乡村原有组织机制的破坏与社会失序
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有赖于国家、绅士和小农结构之间的均衡。当然,三方均衡互动、长期稳定,有其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其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稳定。自秦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低水平循环的状况。其二,以礼治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形态长期稳定,共同的价值观念链条把各社会阶层粘合在一起。
然而,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了。正如费孝通所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其延续的稳定性来看,似乎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当中国开始和有着工业优势的西方打交道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机器时代给中国人带来了现代化,同时,中国被迫进入世界社区。这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13]124现代工业给予西方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倒农业文明的力量,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要维持生存,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国家必然要肩负起现代化之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不断向乡村基层下渗。现代化也必定引起最为敏感和唯一的知识阶层绅士集团的率先分化。西方现代工业的进入还导致中国乡村传统手工业衰弱,瓦解小农经济的基础,导致乡村社会持续动荡。这样,传统乡村既有社会力量格局发生基本变化,从而引发社会改组。
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进入近代以来,国家曾尝试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委任,变乡土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使地方权威成为服务于国家目标的组织机构。这种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进程,事实上触及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框架,使乡土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发生了平稳但却是重要的变化,地方权威“公共身份”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6]30其结果是,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联日益下降,他们对地方民众的责任弱化了,剥削性增强了,乡村社会整合结构逐渐解体。传统乡村领袖一直是无薪的职位,是自愿性的服务,他们通过“保护型”的角色,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维持基层的社会秩序。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进逼和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进程,意味着一个冷酷的压榨机器压到村庄头上,迫使原有村庄领袖必须在国家政权与自己领导的村民之间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顾及自己在村民中地位的乡村领袖是无法保持其领导地位的,他们大批地从乡村政权中隐退。伴随这一过程出现的地方上的新权威 (如区长、村长,晚清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能将县下机构完全官僚化,只实现了半官僚化),从政府和农民双方从事掠夺,成为赢利性经纪。因此,随着作为中介的绅士精英的分化、消亡及隐退,原来官、绅、民的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的自治机制受到深刻触动,官民之间丧失了至关重要的缓冲,彻底“摧毁了传统政治体系的安全阀”。缺乏任何形式的阻拦,高居人民之上的官府就变为直接入村的赤裸裸的掠夺者——“老虎 ”。[13]56,20传统皇权及其官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真独裁的,然而这种制度的理论是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但是,近代以来,政治与道德渐次分离,向乡村下渗的国家权力,既无道德约束,也缺西方那种大众检查机制,结果就变为一种赤裸裸的横暴统治。当局势变得忍无可忍时,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
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的宗族组织机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清初无论华北与江南,均以自耕农经济为主。然而,在随后的三个世纪中内外多重压力下,华北的小农经济向半小农、半雇农的方向发展,江南的小农经济则向佃农的方向迈进。自耕农的生产活动一般全在村内自家的土地上进行,与村庄有切身利害关系,因而是村庄组织的骨干。贫农因失去了土地,而在村庄组织中地位下降。因脱离了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不再关心村内公共事务。那些长年在外的佣工,更是逐渐与本村疏远。[2]316许多地主和富农移居城市,更使乡村失去天然领袖,原来以士绅名流为中介的上与国家、下与地方社会的政治利益联系都不断减弱,地方社会的内聚不断弱化。因而,自耕农一旦分化为上层的地主、富农与下层的贫农、雇农,村庄组织的宗族纽带和聚合力便会随之松散。
另外,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到 20世纪 30年代,农民的半无产化普遍发展,如华北地区 45%的农场面积降到 10亩以下,而一户维持生计最起码要求 15亩。[2]301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18]小农的贫困化,会改变他们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弱化对国家的支持。贫农比中农更可能响应消除租佃和雇佣关系的革命运动。作为与宗族和村庄集合体关系较松散的人,贫农也比中农容易组织动员。真正的穷人在农村也留不下来,他们只能抛弃土地。“但是一旦离开了土地,他们本身也甩掉了土地的束缚。”[13]120他们是心怀不满、无所顾忌的游民,因此有革命性质。20世纪初年,“在许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百分之十九,湖南某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12]671到三四十年代,情况更趋严重,“农民们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悲惨。他们不得不扶老携幼弃家出走,逃难的浪潮就像无尽的波涛,无论时间流失多久,同样的情景依旧发生”,[19]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已走到革命改造的前夜。
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乡土性的,中国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20]城乡文化一体,人才始终不脱离草根,财富在城乡间有机循环,并不大规模外流。而早期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工业和城市现象,接受现代文化的新精英倾向城居,越来越难与农村利害一致。以“修齐治平”为主旨的儒家价值观衰微,而追求实利和机会主义价值观在新精英中广泛生长,他们与农村日益隔膜。同时,社会财富在城乡间的有机循环被打破,变为城市对乡村的单向剥削,“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落相平行的”。[13]73伴随城乡文化同质性的破坏,以及乡村社会精英和社会财富向城市的单向迁移不断加剧,中国农村日益凋敝,传统村社涣散解体。
到 20世纪上半叶,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严重失衡,组织机制破坏,乡村社会陷入了总体性危机中。“在社会腐蚀潮流的冲击下,逼得农民起来造反,生活、经济、政治和道德的种种问题摆在中国面前,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无能为力,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与改革”。[13]8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历史使命,领导人民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并以组织农民为突破口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造。
[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37-38.
[5]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5-27.
[6]张静.基层政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7]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2.
[8]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J].天津社会科学,1993,(6):35-38.
[9]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6):175-188.
[1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1]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J].史学月刊,2008,(1):61-69.
[12]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3]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4]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J].中国农民,1926,(1):54.
[15]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91-204.
[16]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2.
[17]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49.
[18]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二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99.
[19]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90.
[2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1991:150.
Abstract:The reason for the long lasting of the Chinese rural society i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the gentry and the petty farmer takeson a steady,balanced situation.Since themodern times,an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foreign modernization,the state power of China has continuously filtered down to the rural areas,producing the extensive pauperization of the petty farmer,especially the violent differenti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gentry,who,as an agency,plays an up-and-down cushioning part.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gentry is chieflymarked by the fact thatmost of them are diverted into the industry or business or army or school or even the bottom,although a little continue to serve their own interests in the official career.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e I mperial Examination not only destroys the original going-upward channel but also promotes the one-waymigration of the rural gentry into the city,thus produc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power.What’smore,the continuous filtering-down of the state power to the rural areas invalidates gradually the indirectmechanism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With the bankruptof the cottage industry,the petty farmer consistently makes differentiation and pauperization,which also gives a great impacton the rural religiousorganization and rural cohesion.And the day-by-day pauperization of the petty farmer just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turbulent structure before 1949,and,at the same time,foretells the reform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lso increase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cultures,making the rural community lose cohesive force and shaking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its foundation.All these reflect the great social change of China in the modern times.
Key words:social structure;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gentry;disintegration
(责任编辑:李孝弟)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and Its Disintegration
ZHU Xin-sh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Adm inistration,Shanghai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Shanghai201701,China)
C912.3
A
1007-6522(2009)05-0036-07
2007-08-30
修改日期:2010-01-11
朱新山(1969- ),男,山东潍坊人。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