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四个战略挑战
□戴维·兰普顿
中美关系的四个战略挑战
□戴维·兰普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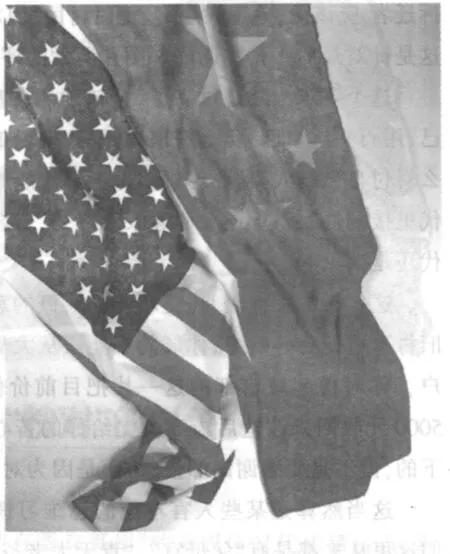
美中关系从根本上讲是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将如此。但双方关系在战略上的四个相互不信任的来源,如果得不到华盛顿和北京的充分关注,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转移。
第一:确定双边关系的挑战
最近流行起来的有关美中关系问题的一项定义,由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做出,他提出的问题是,美国能否“致力于保持亚洲的稳定,保护自己在那里的盟国,并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同时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卡普兰对这一问题的定义起码具有两项缺陷。
第一项是,它使中国扮演破坏稳定的角色,而又不承认中国实际上或可能起到稳定作用的重要情况。第二个缺陷就是,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能够“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的同时,赢得中国在应对跨国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
关于美中关系的国家战略任务,一项比较富于成果的和较少自我拆台的方针应具备以下几点:与中国等伙伴国合作来保持该地区稳定的大国均衡;与该地区和中国合作,以保持和开发对于经济与人类发展来说所必需的安全与人力基础结构:解决构成本世纪生存方面的挑战的跨国问题——粮食、能源、气候、核扩散、资源的提供,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错误地估算两国实力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同时牢记几个有些相互对立的概念:中国日益强大,中国具有相当多的弱点;美国有着严重的问题,美国仍然十分强大,并且拥有自我更新的巨大能力。
如果夸大中国目前和在中期内的实力,就会助长有关威胁的看法,这就像低估中国的能力一样。中国如果对美国的实力加以低估,就可能会造成不谨慎的自信姿态。此外,如果中美两国不对自己的优缺点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的确也会招致错误的估算。
简而言之,双边关系中在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来源之一就是,美国人对美国在有关中国实力的夸张面前的软弱感到不应有的惊慌。
第三:中国“改变博弈”的愿望
一种认识是,对于国家自豪感方面的旧的伤痛,再也不需要默默地忍受,其他国家的实力衰弱十分自然地意味着,从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应当更加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正如在中国接受采访的一位外交界资深人士对我所说:“变化发生在中国方面,因为民众对美国干涉的容忍程度‘大大下降’。如果是发生在10年前,中国政府可能会与人们讲道理,但现在却不能。国内对美国胡作非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差。这是公民社会的自然发展,也是中国的崛起所使然……可以见到有影响的学者说,美国应当付出代价,中国人失去耐心……中国人正在施加压力。”
第四:挑战和对策方面的动态关系
除了对30年来政策方面的成功和对竞争对手日益衰败的看法所产生的自信之外,还有一种几十年之久并逐渐加速的挑战与对策方面的动态关系,也促使双方在战略上彼此猜疑。
中国政府在1985-2000年期间做出的三项战略决策促使美国感到担忧。第一项,是1985年开始中国军事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即想要使未来的冲突扩展到天空、海洋和太空。中国在战略决策方面的第二项关系涉及台湾,关键的年份是从1995年到2000年,台独情绪在台湾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使得中国确信,两件事情是必要的——对台湾宣布独立实行“威慑”,并加强军事力量,以使美国今后进行干预的风险和代价增大。第三项是预算问题。1978年以后的10年里,中国在军事开支上保持低水平,把可用的资源用于经济增长,但之后这发生了改变。
但目前,我们距离冷战规模的上升螺旋甚远。保持战略稳定和避免出现上升螺旋,涉及讨论两国在太空、网络空间、反导技术和精确制导的常规武器等方面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这种讨论变得更加紧迫。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book=131,ebook=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