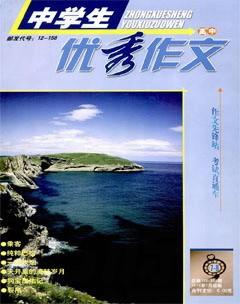乘客
孔如画
老屋残损的棱角划破凄凉的暮色,昏鸦疲弱的翅翼掠过西边的天空,漾出淡淡的霞彩。夜风挟卷夏日滞凝的暑气,婆娑了香樟茂密的叶。灰黑色的青绿色的枝干摇曳着,轻轻的,浅浅的,荡漾着湖面氤氲的夏梦。
枯瘦的老妇人站在那里,那里镜子似的湖上,牵着灰白色编织袋的开口,轻轻放入一把把蔬菜。她在絮语,豇豆硬,放在下面,油麦菜和小白菜放在中间,熟透的西红柿放在上面……昏暗的客堂只有她一个人,夕阳透过那几面结着蛛网、覆着灰尘的玻璃,一直投在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没有人回答她,她亦没有说给任何一个人听,只有一群黄绒绒的小鸡在那暖煦的光线里唧唧叫着,争抢一条肥大的青虫。
我在门外看着她,看着残阳抚摩她脸上的沟壑,看着薰风拂乱她的短发,看着那湖面蒸腾的水汽一步步逼近。渐渐吞噬了她。我想伸展翅翼飞去她身边,将她从迷障中拉出,却只能站在这里,无助得如同婴孩。忍不住心中的钝痛,蹲下身子轻轻啜泣,用香樟的小枝混合泪水与泥土,仿佛这样可以将我的灵魂留在这片土地,留在她的身边。
可是这又会有什么作用?坠落的香樟红叶撞击额头,看着叶片上清晰的黄色叶脉,一如浩荡的生命河流,永不停息,亦是永无止境。而她,而我,而我们,只是忙着生,又忙着死,只是时间这列客车的乘客,在某一站上车,又必定会在某一站下车。谁会拥有带来救赎的能力,我又能够做什么?只是睁开眼时看见了她,却又在某站目送她离去。
她送我到公路边,手里硕大的袋子被她塞进了后备箱,又关紧,催促我们离开。从屋前延展出的小路,我无数次走过,父亲无数次走过,她亦是;我倦了,父亲倦了,她却依旧用脚掌丈量它,抚摸它,乐此不疲,仿佛它承载着她生命的意义。日暮的时候,望见向前铺展的灰白公路与窗边掠过的乡村景致时,她竟又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枯瘦的身体与路边新栽的小白杨等高。她在风中颤栗着,同那小树一起,仿佛是可以永远那么站着,迎我们回来。又目送我们远去。
而在左边,是我的父,年过四十的沉默的父,鬓角微沾霜雪。眉目却仍隐隐透露年少的桀骜锋芒。此刻的他,正沉默地开车,轻轻的音乐在耳边萦绕,心渐渐沉寂安静,是在从老家回来的路上。
暮色沉淀,窗外的世界隐遁在夜幕之中,只是一瞬间的呆滞,恍悟时天色已经黑透。仿佛是想起翻越福建繁复的武夷山系的颠簸旅途,又仿佛是想起初三那年的五月,开车去黄冈的情形。六小时的车程,一直坐在副座,从日光暖煦直到夜色深沉。途经流芳时,听见他呓语般说:“鹏鹏就是死在这里。”随之而来的是暮色和与暮色一样深重的沉默。
这是我为数不多地嗅见他身上萦绕着的悲伤气味。鹏鹏是他的堂弟,在我还未有记忆时死在流芳的路桥上。他未曾忘记,而我,却未曾记得。
现在的他,比一年前更显衰老。也许我是个令人费心的孩子,也许是他已到了衰老的年纪,可以确定的却是他将陪我一起走过的时间不会再像从前那般长,我们终会离散。可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在意了。车里的音乐缓慢流淌,而我,只是他的乘客,一切堂而皇之,无关紧要。
院子里的花树一季季绽放,它们的生命也许比我们长久;黑色大狗在青砖上晒太阳,慵懒却狡黠,有它陪伴的日子也许不足二十年;破旧的房子已经守在这里二十年了,还能支撑多久,它不知道,我亦是无从得知。一切如果用时间来计算,公正严明,冰冷残酷。于是将时间的足迹抹去,仿佛只是这样一日日,花树在,大狗在,她在,他在,仿佛是可以不离散。
进城的时候,在山坡上望见喧嚣的市井灯火。街灯与霓虹灯聚成的河流流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此刻的我,只是倦倦地靠在座椅上,头倚着玻璃,感受那冷冽的触感。
倘若我真的只是个乘客,而不是迷失在灯火中的孩童,也许有那么一瞬间的我会明白,自己是多么爱他。
点评
我们是时间的乘客,一种亲情的感伤在作者淡淡哀伤的叙说中浸漫人心。读罢,令人感伤不能自己。
(邓济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