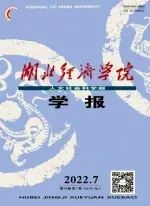从归化翻译看林纾现象
安东阳
(吉首大学 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从归化翻译看林纾现象
安东阳
(吉首大学 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归化翻译能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而林译小说正是使用了归化的翻译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主要的文学流派和主要文学作品。但林译小说不尽完美,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分析“林纾现象”可使人们对林纾有更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
归化翻译;林纾现象
一、引言
严复曾赞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钱钟书,2006)郑振铎曾曰:“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钱钟书,2006)郭沫若曾说过“《迦茵小传》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添了不少光彩”。(郭沫若,1982)康有为的名句“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郭延礼,1998)非常公正地概括了林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在21世纪的今天,研究林译小说的热情依然不减,研究成果比比皆是,各种观点褒贬不一。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王克非,1997)钱老虽然为林纾的翻译作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同时也为后人讨伐林纾及其译作埋下了伏笔。钱老甚至认为林译作品是错译、误译和漏译的代表,受钱老的影响,后来的一些学者对林纾作品不屑一顾。笔者认为,用错译、误译和漏译来描述林译小说有失公正。
二、归化翻译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归化(domestication)的概念。他认为: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Venuti,1995)朱安博在他的《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中提出:归化翻译指的是“一种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翻译,即采用目的语文化所认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使译文流畅、通顺,以更适合目的语读者”。(朱安博,2009)由此看出所谓“归化”是指译者用与原语意义和功能基本对等的译语来翻译,使译文的语言本土化,这种方式主张使用译语中现成的表达方式和传统的文学形式来取悦译语的读者,由于使用的是本国人熟悉的语言来译,所以译文自然会比较地道、顺口,读者读起来也容易理解和接受。我们提到翻译的本质是促进交流文化,恰到好处地归化可以使译文地道简洁、生动活泼,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和接受,从这方面看来,归化翻译能够较好地达到此目的,能被读者广泛接受。林译小说正是使用了归化的翻译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主要的文学作品。
三、林纾现象
“林纾现象”的概念是最初由祝朝伟教授于2006年在其撰写的《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这种不懂翻译的原文、译作类似创作的翻译现象称为庞德、林纾现象”。(祝朝伟,2009)这一概念的诞生势必会减弱一些学者对林纾的负面看法。可惜祝朝伟教授对这一概念没有作具体的探讨,“林纾现象”一词至今也未得到普遍认可。笔者和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黄元军先生此前曾就“林纾现象”的表征及要素作了系统论述,一致认为林纾现象存在四方面表征,即:删节、误译、增补和改译。
(一)删节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林纾翻译小说的开山之作。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的重印本字数为5.1万,1994年译林出版社的郑克鲁译本字数为15.8万。《块肉余生述》是林纾最满意的译作之一,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的重印本字数为29.7万,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庄绎传译本字数为80.6万。《黑奴吁天录》是林纾翻译时最动情的译作,1981年商务印书馆的林纾译本的字数为12.4万,而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继忠译本则有34.8万字。书中摘章节译和篇中摘段译的手段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字数之差,这足以反映出林纾在翻译时删节程度之深、频率之高(当然古文比白话文简洁也是一个因素)。
(二)误译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林纾,笔者按)把‘开门’(ouvre)和‘工人’(ouvrier)混为一字,不去说它,为什么把也是‘法兰西语’的‘谢谢’(merci)解释为‘不规则之英语’呢?不知道布封这个人,不足为奇,为什么硬改了他的本姓(Buffon)去牵合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癞蟆’(bufo,bufone),以致法国的动物学大家化为罗马的两栖小动物呢?”(钱钟书,1981)1918年,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奉答王敬轩书》一文,文中说:“林先生所译的小说……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本不高明,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的地方,便含糊了过去。”(刘半农,2005)
(三)增补
在中国文学翻译的早期,译者考虑国内读者而采用增补内容策略是一种风尚。林纾就是典型代表。钱钟书在讨论林氏增译时,就写道:“他(林纾,笔者按)却按照他的了解,在译文里有节制地掺进评点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之笔,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钟书,1981)以上论述向我们展示了林纾在翻译时惯用的注释式的内容增补,而这增补之缘正如谢天振评周桂笙所译《毒蛇圈》:“完全是因为出版者考虑到接受者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接受者所处环境中的社会事件等因素而添加进去的。 ”(谢天振,1999)
(四)改译
林纾译作的改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原作标题的改译,如:《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 《茶花女》)、《块肉余生述》(今译 《大卫·科波菲尔》)、《魔侠传》(今译 《唐吉诃德》)、《黑奴吁天录》(今译 《汤姆叔叔的小屋》)、《吟边燕语》(今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贼史》(今译《雾都孤儿》);其次是对原作体裁的改译,林纾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和易卜生的Ghosts(《梅孽》,今译《群鬼》)译成小说。
四、从归化翻译看林纾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林纾(1852~1924年)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小说翻译家,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林纾虽未曾留学,也不谙外文,但他却是那个时期能兼纳中西学术的新型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文化浸润的文人,他看到了中国数十年中的衰落和西方文明对于中国之发展所带来的希望。从一开始翻译小说,他就自觉地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使中西方学术之优点能融会于一处而为我所用。林译小说的文化选择在历史转折时期,一个有思想、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会对自己乃至对民族的出路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与他们的知识、思想背景紧密相关。远在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就开始了对佛经的翻译,但从译文的内容来看,译者曲解原意以使其本土化的地方太多而为后世经师所诟病,从道安直到姚秦鸠摩罗什和南朝陈真谛才完成了佛经翻译在文辞与意义上的完美结合。近代小说之翻译不可避免地要与佛经翻译所经历的过程相似。著名学者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之标准,显然难以适应于林纾所处的那个年代,因为毕竟士人对西学之了解甚少,还需要借助本土文化之固有的、相似的东西来帮助了解域外的新鲜事物。所以说归化翻译势在必行。
(二)自身原因
林译小说存在着大量的删改与增补现象,这首先要归结于林纾并不懂西方语言,而是与留学归来者合作完成的。不过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意思是有所选择的,并在此基础上有意地进行再创造,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和士人的阅读习惯相融接。《黑奴吁天录》是林纾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过来的。林纾嫌原来的题名不够雅,而改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读者能从这个简短的题名当中直接领悟全书的基本内容。题名“吁天”,虽然隐去了原作题名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就中国本土读者而言,人们可以从自己所熟知的文化系统当中汲取相似性的内涵来阅读这部译介来的域外名著。其次,林纾个人受到了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限制,这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性无疑会在其翻译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林纾本人认同当时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采取省略、改译、增译等方式以迎合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三)读者原因
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去代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是“讹”。若再从诗学环境之传统来说,这种故意的“讹”又使得异质的文化走向归化。古代中国历来都不把小说作为雅文学的主流,因此林纾有必要在翻译时把以他的桐城古文笔法进行语言润色,使其更易为读者接受。以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而言,林纾的这些努力拉近了小说叙事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不会因为文字的艰涩而淡化原著的精彩之处,从而觉得会索然无味。在林译小说中,林纾以极妙的手法展现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法与价值,同时也以这种特殊方式加深了世人对西方小说的理解与鉴赏力,提高了学习借鉴西方小说技巧的自觉性。因此,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融会中西文学之长处,林纾的文化选择也即是历史性的睿智选择。
五、结语
综上所述,林纾在翻译中主要采用以归化翻译为主的策略,在其翻译过程中,通常都对原作进行了删节、误译、增补、和改译,而这些翻译法也是林纾现象的主要表征,是林纾在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影响下,为了使译本符合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对原作做出的一定的调整。归化翻译也就必然成为林纾翻译方法的主导。虽然他的译作中充满了漏译、误译等,但是从其影响力来看,仍不失为好的翻译。用林纾现象来描述林纾翻译作品呈现的特征,可以令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正确地评价林纾这位翻译家,并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
[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4]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祝朝伟.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7]刘半农.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刘半农卷[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8]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0]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