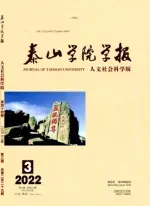努力的徒劳与徒劳的努力——从日记看“五四”退潮之初鲁迅的日常生活
刘克敌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36)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远在美国的吴宓和徐志摩在各自的日记中,对此都有很多记录和评论,可见此事对中国留学生的冲击之大。鲁迅虽然此时早已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以自己的白话小说创作,与胡适等人的白话诗一起,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篇章,但他当年 5月和 6月的日记中却只字不提发生在身边的这个运动,只有一次提到和周作人一起去看胡适所写的话剧《终生大事》的演出,多少让人感到有一丝新文化运动的气息。不过,考虑到鲁迅的日记本来就是纯粹个人杂事的记录,其日记中没有提及五四运动也属自然。
创作白话小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一帮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按说这些都应该使鲁迅兴奋起来,那种挥之不去的无聊和苦闷即便不能消除,至少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笼罩在鲁迅心头了罢。可是,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兴奋似乎只维持了很短一个阶段,鲁迅就又回到民国初年那样的“无事”可做的境遇之中,这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其日记中的“无事”字样又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并迅速增加到令人震撼的程度:
在 1920年的7月,“无事”记录出现 12次,到8、9两个月,出现“无事”的次数达到 15和 16次!而其他各日的记录也极为简单,整整一个月的日记内容不足两页 (以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排版为准),7月份每日字数为两行的仅有七天,8月份每日字数为两行的仅有五天,9月份则仅有 3天,且没有一天其内容超过两行。相比之前其日记每月内容往往长达 4、5页,每天内容记录多达5、6行者很多的状况,这种变化是惊人的。阅读这一阶段的鲁迅日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鲁迅已经连日记也懒得写了,之所以这样简单仅仅是为了维持日记的连续性。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年底,至次年年初才稍稍好转 (日记中“无事”字样在 10月为 13次,11月为 10次,12月为 10次)。
我们不仅要问,这一阶段鲁迅怎么了?其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其思想上有什么变化,才导致其日记出现如此状况,这个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战士的“鲁迅”,怎么又感到“无事”可做了呢?
也许,了解鲁迅此时心态变化的一个角度就是书信。可惜,鲁迅在 1920年所写书信至今被收入《鲁迅全集》者仅有该年 5月 4日写给宋崇义的一封。不过,就是这一封我们也可以发现鲁迅当年心态的些许蛛丝马迹: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1]
显而易见,鲁迅这里所评述的就是刚刚过去一年的五四运动,不过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却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似乎都不入鲁迅的法眼。在鲁迅看来,那样一次伟大的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至于中国的未来,鲁迅更是绝对的失望:“但有一塌糊涂而已”。请注意“而已”一词在鲁迅笔下绝非简单的语气助词,而是有深刻意蕴者之特殊词汇,只要想想他后来那本有名的《而已集》就明白了。
以鲁迅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如果连五四这样的伟大运动都不能使他改变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态度,那么即便是继续从事刚使他获得世俗名声的白话文学,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在书信中,因为毕竟是与外人交流,鲁迅还是尽量表现出一些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至于日记,因为纯粹私人记录,则鲁迅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自己所有的绝望情绪。不过由于鲁迅记日记一向较为简约且已成习惯,不会因为暂时的情绪变化而更改。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看来,其实任何试图宣泄悲观绝望的企图也不再必要,因为自己既然还要忍受枯燥无聊的现实生活,则书写本身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能书写的形式“而已”,那么“写什么”和“怎么写”就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他还在“写”——借“记日记”这个活动证明自己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和勇气。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鲁迅这几个月过于简略的日记,看看透过这些极为简略的文字,是否能够窥视出鲁迅那时的内心世界。先看“无事”出现最多的八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车耕南信。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舲假泉廿。
三日晴。无事。
四日 昙,下午雨。无事。
五日 晴。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小说一篇至夜写讫。
六日 晴。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得李遐卿信。
七日 晴。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午前往铭伯先生寓。
八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九日晴。无事。
十日 昙。夜写《苏鲁支序言》讫,计二十枚。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午前访章子青先生,取泉卅,由心梅叔汇来。
十四日 晴。上午徐吉轩泉十五。下午昙。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六日 晴。晨访蔡先生,未遇。晚寄汤尔和信。
十七日 晴。上午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 晴,下午昙,风。无事。
十九日 小雨。无事。
二十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下午雨。晚得蔡先生信。
二十一日 昙。下午宋子佩来。寄蔡先生信。晚李遐卿来并送平水新茗一包。
二十二日 昙。星期休息。午后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假泉十二。夜雨。
二十四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得李遐卿信。寄朱孝荃信。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李遐卿信,即复,并假来泉八。傍晚雨一陈。得高等师范学校信。夜寄毛子龙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雨一陈,夜大雨。无事。
二十八日 昙,午后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整理书籍。
三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买鞋一双。
三十一日 晴。无事。[2]
从日记中数次出现“星期休息,无事”字样看,显然“休息”仅指这一天不用上班,而“无事”指的是鲁迅个人的身心状态,既包括形式上的无事可做,更表示心理上的无聊与寂寞。
这一个月中,鲁迅记入日记的内容有:
关于写作事两次、书信往来 11次 (次数明显少于以往)、看病取药一次、外出购物一次、看朋友及朋友来 10次,其中书信及与友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借钱与还钱,次数多达八次 (对此下文会分析)。除此外就是那些触目惊心的“无事”了,如果不是还有一两个关于当日天气情况的词汇,则出现在日记中那一排排整齐的“无事”将更加引人注目。
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年从 7月到 12月,鲁迅逛琉璃厂的次数明显减少到只有四次,购买古书等更是寥寥无几,与以前每月数次且购物甚多形成强烈对比。当年鲁迅的书帐仅有 51.8元,较往年的动辄数百元实在是差距太大。此外,与好友外出吃饭次数从 7月到 12月竟然为零,也是反常之举。那么如果不是鲁迅有意不记录,肯定与其经济上出现问题有直接关系。可能影响到鲁迅心情不佳的事件还有家人的病。其中以沛 (鲁迅三弟之子,当时仅一岁)的病最为严重,住院时间长达两个月,之后又是鲁迅母亲患病,这两次家人之病显然会严重影响鲁迅的心情,且直接导致鲁迅为看病借钱多次。本来按照鲁迅的正常收入,应付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方面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大量欠薪,导致鲁迅实际收入大减。另一方面是周作人一家来京后,其妻子大肆挥霍,使得入不敷出,鲁迅为维持家庭正常生活不得不借债。据 1920年的日记,当年鲁迅就借债20多次,总计近千元。也许,被迫借债的鲁迅又会联想到当年为父亲医病而不得不来往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日子,如此鲁迅的心情又怎么会好起来呢?
“西马”著名代表人物、20世纪法国哲学家列菲伏尔指出,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其意义就是要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深处发现历史的无穷希望与可能性,就是寻求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永恒的轮回性与瞬间超越性的统一。日常生活就其单调乏味的循环过程而言,确实无法给人带来希望,似乎也没有任何值得欣喜的意义。但是,它毕竟潜藏着无穷的希望与产生短暂幸福感的可能——谁知道那人生的辉煌何时会大放异彩呢?问题在于,为了等待那短暂的辉煌却要忍受漫长的无聊与空虚时光,付出极大的身心方面的痛苦,对于一般人而言,也许代价过于昂贵以至于他们因此放弃了这种可能而甘愿混迹于世俗生活,拒绝思考自己的不幸。那么,似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级的人物,是否就一定心存不甘而拒绝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否就必然寻求免于堕落的一切机会与可能?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本来是鲁迅借此摆脱个人苦闷与痛苦的极好机会也几乎是他唯一的机会。可惜,新文化运动发展到 1920年,领导者与参与者自身却发生了分裂,对此鲁迅有一段有名的话给予总结: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3]
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句:“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显然,已经拿起笔来的鲁迅在取得重大成就后,在尝试到藉此可以暂时部分消除内心苦闷的“甜头”后,已经无法停止文学创作的脚步。但就在此时,他所寄予希望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却开始分道扬镳,自然让鲁迅一时无所适从。继续创作是必然的,但再听谁的“将令”呢?“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所谓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是鲁迅此时心境的最确切概括。
关于新青年同人此时的分裂情况,学术界已有论述,此处仅从影响鲁迅心态角度分析。《新青年》从 1918年一月开始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具有了同人杂志的形式,鲁迅也从第四卷开始写稿。到 1919年第六卷,《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宣布此后各期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六人分期主编,鲁迅没有主编但却参与过编委会的工作。1919年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新青年》诸人之间的辩论,可以认为是分裂的信号。由于 1919年 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停刊 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 12月的第 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已在上海居住的陈独秀开始接触到共产国际的思想,导致《新青年》的办刊思想趋于政治化,而胡适却不喜欢谈政治,《新青年》内部出现分裂。《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于 1920年 9月 1日在上海出版,其中刊登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驳斥胡适等人“不谈政治”的主张,分裂自是公开化。不过,陈独秀并不希望就此与胡适等人彻底分裂,还是于当年 12月给胡适、高一涵去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人“多做文章”。当时,陈独秀曾经让胡适提出意见,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办。胡适于是提了三个意见,其一是将《新青年》撤回北京,编辑同仁们共同刊发一则声明,说明不谈政治,只做文章。其二,让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来办《新青年》,大家另起炉灶,再办一份其他的刊物。其三,停办《新青年》。陈独秀得到这封信后,意识到双方的分歧已是很难弥合,决定不能让步,他给《新青年》的编辑同仁们回信,驳斥了胡适这三个解决方案。特别是对于不谈政治这个问题的回复,陈独秀态度十分坚决,写道“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不赞成第二条办法”。胡适收到回信后将信给在京的同人传阅,钱玄同见信后十分感慨,“初不料陈、胡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并认为胡适“所主张者较为近是。…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4]
当初鲁迅加入《新青年》写白话小说本来就是受了钱玄同的鼓动,所以后者认为有义务将这些消息告知鲁迅。而鲁迅的反应也很明确,就是同意胡适说的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由北京同人发表声明,此后刊物重点在学术思想文学方面。但鲁迅不同意一定要声明“不谈政治”,理由是一则“不愿示人以弱”——这是典型的鲁迅性格;一则是“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5]但此后的发展是,陈独秀没有听取北京同人的意见,《新青年》此后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完全脱离了与北京同人的联系,这大概就是使得鲁迅失望的原因——此后,是否又要回到抄古书的轨道上了?鲁迅自然是不愿意如此,但连参与新文化运动都落得一个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么还会有什么值得他再去尝试?鲁迅是真的害怕再次掉进希望——失望——再希望——最终更加失望乃至绝望的恶性循环之中。
值得注意的信号再次出现:一个是鲁迅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中国小说史》,虽说是为了上课的需要,但这毕竟显示出鲁迅的一种姿态,他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可做之事了。一个是重新开始校《嵇康集》,这个就更加明确是回到原先的老路。此外,在 1920年年末用日文写给青木正儿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未来极为绝望:“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成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鲁迅又说:“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吧。”此外,对于《新青年》的转向政治,鲁迅也表示出担忧:“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6]
现实生活确实对鲁迅过于严酷,在刚刚给鲁迅提供一些希望的“新芽”后,就要无情地摧毁它们。不过,鲁迅既然已经体验过可以藉世俗生活中的某些看似有意义的活动 (文学创作)来摆脱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无聊与空虚之感,就不想再次回到“绍兴会馆”那单调乏味的抄古碑之中,在稍后创作的《故乡》中,那著名的结尾虽然有些吞吞吐吐,还是表达出寻求走出一条拯救自我之路的渴望。《新青年》的改弦易辙以及和一些战友的分道扬镳,固然给鲁迅带来莫大的打击,但其他的尝试还是可以进行。鲁迅至少找到了两个维持世俗日常活动的出路:一个是到北京的高校教书,这个效果极为明显,后来的与许广平开始交往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是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虽然限于其教育部职员身份,鲁迅不能直接参加,但借助于周作人,鲁迅实际上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等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此时的鲁迅,尽管有意无意有回到旧生活轨道的倾向,但内心深处渴望新生活、寻求新的拯救之路的愿望更加强烈。日常生活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没有意义的简单重复,特别是对于鲁迅这样思想深刻而又对现实格外敏感者。但是,也只有继续这种简单的重复,才有可能于无数的重复之后产生瞬间的对人生的美好感受,这就类似于浮士德的一生及其幸福的结局。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看似永恒轮回的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深处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生活的希望——尽管这希望只有短暂的“灵光一现”,也就值得为此等待大半生乃至一生。作为普通人,也许只有被动的等待而已,但像鲁迅这样的哲人贤者,就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去主动谋求“灵光一现”的尽快到来和更多地出现。
不过,对于鲁迅这样的人物,日常生活中那些短暂的有意义的瞬间毕竟更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时候的无聊的日常活动,该如何打发才不至于重新陷入苦闷与“无事”可做的状态之中?唯一的可能就是把这种日常生活给予“节日化想象”,就是谋求日常生活的“狂欢化”,于是就不难理解鲁迅对尼采、对“酒神精神”为何给予高度评价和推崇了。本来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对尼采学说很有研究,1920年在《新青年》面临分裂之时,他还是要从尼采那里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一年的八月十日,鲁迅完成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作《译后附记》。鲁迅在对此序内容和一些术语进行说明的同时,也隐隐显现出自己的心境态度:
第七节 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 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第九节 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 (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 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W ieder kun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 (Bildung)的结果。[7]
其中那“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一句不就是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心境的最好描述?此外,那蛇所象征的“永远轮回”一词也值得注意,是否鲁迅从中悟到一些日常生活对“超人”的影响以及超人试图挣脱之努力呢?
看鲁迅 1921年的日记,的确有所变化。首先是日记篇幅重新开始拉长,对有关事项的记录变得详尽起来,出入琉璃厂的次数也变得多起来, 1921年的书帐为 137.19元,虽然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确实有了很大增加,原因就是鲁迅本年拿到了一些欠薪,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心情自然会变好。其次当然是那触目惊心的“无事”出现的次数明显减少:1921年 1月还是 10次,到2月就减为 4次,到 4、5月份已经只有两次了。1921年全年日记中出现“无事”的次数为 59次,仅为 1920年 117次的一半,减少幅度之大也说明鲁迅的心态有所变化,对自己所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已经逐步减轻了那种无聊与苦闷之感。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鲁迅的心情确实开始好起来,那就是本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多日后又移居西山疗养,为此鲁迅不仅在经济上再次承受压力,时间精力等都是付出很多,但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却很少看出鲁迅那种民国初年初到教育部上班时的无聊、寂寞与空虚之感,此时的鲁迅似乎变“俗”了。也许,以精神上的“俗”之一面应对世俗生活,就是五四之后鲁迅所能找到的新的救赎之路。自然,在灵魂深处,他对此是采取不屑态度的,但鲁迅懂得,如果自己不想回到民国初年那种枯坐终日抄古碑的状态,就必须暂时忘却这所谓的世俗之“俗”,甚至还要带有热情地投身其中才是。
在当年 9月 11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对中国热衷于表现派戏剧创作的浙江老乡宋春舫给
[1]鲁迅.鲁迅全集 (第 11卷)[M].北京:人民文学予这样的讽刺:“表现派剧,我以为本近儿戏,而某公一接脚,自然更难了然。”[8]被鲁迅如此讽刺的那个剧本名为《只有一条狗》,是宋春舫翻译的意大利著名剧作家 Francesco Cangiullo的作品,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剧本只有三句:
登场人物???……
一条街;黑夜。冷极了,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狗慢慢跑过了这条街。(幕下)
实事求是讲,这剧本虽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却是很有内涵,至少不像鲁迅所讽刺的那样“儿戏”。那么,鲁迅之所以还要讽刺,是否意味着他不想再看到这样荒寒冷寂的场景,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还是在心灵深处?出版社,1981:369.
[2]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78.
[3]鲁迅.南腔北调集[M].上海:上海天马出版社, 1933.
[4]钱玄同.钱玄同文集 (第 6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16.
[5][8]鲁迅.鲁迅全集 (第 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1、403.
[6]鲁迅.鲁迅全集 (第 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4.
[7]鲁迅.鲁迅全集 (第 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