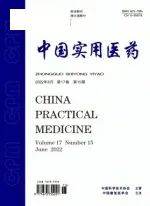糖尿病宜从五脏论治
刘显章
糖尿病相当于中医学之消渴证,为临床常见之疑难杂病,以多饮、多食、多尿,身体消瘦或尿浊、尿有甜味为特征。关于病位问题,现今临床多以肺胃肾论治,但有许多患者按此治疗效果不佳,因此对糖尿病的发病机理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笔者依据《灵枢·五变》篇“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之论并结合临床,认为五脏病变皆可致消渴病,非独责于肺胃肾。本文就心肝脾与消渴证的发病关系作一探讨。
1 从心论治
《灵枢·本藏》曰“心脆则善病消,热中”,提出心气先天不足,气血虚弱,调摄失宜,终至精亏液竭而发消渴。《素问·气厥论》云“心移寒于肠,肺消”,认为上消的形成原因责于心,而非肺的原因。《医宗已任篇·消渴》称“消之一病,原于心火炽炎……”;明·周慎斋《慎斋遗书》曰“心思过度,……此心火乘脾,胃燥而肾无救”。发为消渴的认识,刘河间《三消论》云“……心火属阳而本热,虚则为寒。消渴之人肾水阴虚,心火阳实,则上下俱热而致病”;张子和《儒门事亲》谓“三消当从大断”,又曰“夫身之心火甚于上,为膈膜之消;甚于中,为肠胃之消;甚于下,为膏液之消”。这些论述均说明心在糖尿病发病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心气郁结,郁而化火,心火亢盛致心脾精血暗耗,肾阴亏损,水火不济而致消渴。在治疗上,刘河间确立了消渴病的治则:“补肾水之虚而泻心阴热之实,除胃肠燥热之甚,济人身津液之衰”。这一治则,遂为后世医家之圭臬,而备为喻嘉言等医家称诵。临床中发现,凡消渴者,特别是在疾病的早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心火偏亢,心阴不足或心肾不交之证。刘河间主张用辛苦寒凉药,如治消渴的麦门冬饮、人参石膏汤、人参白术汤、消痞丸等方,均选用黄连、黄芩、大黄、石膏、知母、山栀等苦辛之品,釜底抽薪,俾心火下降,肾水上升。至今,清热降火仍为治疗消渴病常用之法。
2 从肝论治
《灵枢·本藏》有“肝脆善病消易伤”的论述;黄坤载《四圣心源·消渴》曰“消渴者足厥阴之病也,厥阴风木与少阳相火为表里……风木之性长欲疏泄……疏泄不遂,则相火失其蛰藏”。在《素问·灵微蕴消渴解》又曰“消渴之病,则独责于肝木而不责于肺金”。郑钦安在《医学真传·三消症起于何因》论述到“消渴生于厥阴,风木之气,盖以厥阴下水而上火,风木相煽,故生消渴诸症”。这些论点成为消渴独责于肝的理论依据。肝的主要功能为主疏泄,调畅气机,促进中焦运化。糖尿病的发病原因极重要的一点是情志失调。《临床指南医案·三消》云“心境愁郁,内火自燃,乃消证大病”。说明五志过度,郁热伤津,是发生本病的重要因素。五脏之中,唯肝畅情志。肝气郁结,情志失调,可致消渴。现代研究表明,不愉快的精神,可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交感神经兴奋,通过神经-下丘脑-肾上腺髓质轴分泌儿茶酚胺,作用于动脉细胞,使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多,并促进肠道对葡萄糖的摄取,从而诱发糖代谢紊乱。另外,“肝为五脏之大贼”,上侮肺金,下竭肾阴,中伐脾胃,不一而足。肝火上升,肺金受灼,津伤失布,是以为渴;肝火下灼,肾脏之虚,封藏失职,多尿乃成;肝木横行,乘脾犯胃,肝胃郁热,消谷善饥,由是而作。因此,肝脏在糖尿病的病变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故临床上应结合疏肝、平肝、养肝、活血化瘀等辨证施治,方可提高临床疗效。
3 从脾论治
脾居中属土,主饮食运化,津液输布。消渴病从脾论治,在《千金要方》中即有体现,孙思邈认为“食物皆消作小便”。至金元时期,养脾生津液作为治疗大法而确立,并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刘河间曾云“消渴者土湿之气衰也”;李东垣曰“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能四布而输膀胱,故小便数而大便难”;《类证治裁·五消论》曰“小水不能散精达肺,则津液少;不能通调水道,则小便无节,是以渴而多饮多瘦也,可谓获其要旨”。糖尿病是津液耗竭之证,是导致津液精微物质流失的原因,是消渴的本质,而控制津液精微物质的流失,才是固本之治法。脾主运化,输布津液及精微物质。脾病可导致津液精微物质代谢功能紊乱而发生消渴。在治疗上从脾着手,通过益气健脾,恢复其化输津液、布化精微之功能,使机体的津液和水谷精微代谢趋于正常。刘河间在其人参白术汤、人参散等治消渴方中也并未忽略四君子汤酌加葛根、麦冬等培土生津。陈修园认为消渴“以燥脾之药治之,水液上升,即口不渴矣”。主张用黄芪六一散、七味白术散、理中汤治之。仲景治消渴病主方之白虎加人参汤、人参合甘草粳米汤健脾益胃以化输津液。近代张锡纯所创玉液汤,重用黄芪、山药补脾益气,佐以内金,更以葛根升发脾气。现代药理研究亦证明诸多健脾益气之中药如黄芪、山药、人参、葛根等均具有良好的降糖作用。故在糖尿病早中期,治疗应着重健脾,酌情化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