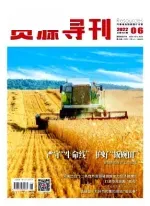报刊文摘
报刊文摘
最低工资上调陷竞争怪圈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北京、上海、四川、江西等14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从调整后的情况来看,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14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已经陷入竞争怪圈,各地区只是盲目跟风上调,调控过程尚缺乏公开透明的依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车伟就指出,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却也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从而增加了物价上涨压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彭剑锋表示,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只是盲目跟风调整,并未考虑自身特点,未来该标准的调整可以和物价挂钩,并可让不同地区根据地区内部劳动力成本来进行测算,这样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才更有实际意义。
(摘自5月2日《北京商报》)
从“托儿”看公共服务的漏洞
近日,陪朋友去城东北一处办理车检等事务。人尚未下车,“托儿”们已围了上来,说是这里停电了,可以带我们到城西或者城南去办理相关手续。出于警惕的本能,我们还是要到该办事机构看个究竟,发现真的停电了,无公务人员接待,也无相关服务公告。
情急之下,车主只好从 “托儿”中选择一貌似干练可托之人,谈妥300元协助办理相关手续。而在城西的车检点,历经交税、车检、交保险费、选车牌、办车证等诸多繁琐环节,到处都能看到“托儿”领着“办证菜鸟”穿行其间的忙碌场景。
据悉,除了前述车辆办证外,“托儿”在办理劳动保险、土地征用、房产交易等诸多领域大量存在。“托儿”们的“亲民”,显然是为了从中渔利。而相关公职人员呢?难道纳税人没有供养着他们?从“托儿”身上不难看到公共服务的差距和漏洞有多大。
(摘自5月2日《长江日报》)
“最美女教师”为何没编制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张丽莉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救出两名学生,被誉为“最美女教师”。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教师,居然没有编制,也没有医保。也就是说,她是一名教师中的“临时工”。
现实中,青年教师中没有编制的情况很多,特别在一些实现教师阳光工资的地方,因总数固定,每进一个教师,就要从总数里分走一杯羹,导致其他教师的阳光工资下降。所以,许多地方严控进人,导致许多年轻人,毕业多年都是无编制的“临时工”。
一方面,为了争夺编制,家有门路者不惜送钱送礼,打通关系把资质平庸、成绩不好或是缺乏责任心的年轻人送进正式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许多热爱教育事业、业务出众,怀揣教师梦的年轻人,却不得不离开这个队伍。
教育行业留下的,本应是这个国家的精英。这些年来,我们是否把最适合做老师、最有资格做老师的人留在了教师队伍里?我们还需反思,对于那些委曲求全留下的精英,为何要让他们承受低工资、无保证、无尊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委屈与痛苦呢?
(摘自5月18日《广州日报》)
赖昌星案一审凸显“追赃”挑战
5月18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赖昌星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记者获悉,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了解赖昌星在国外的资产状况,并拟与加拿大签订“关于返还和分享被没收财产的协定”。
对于两国如何分配被没收财产,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主要视该国在执法合作中贡献的大小来定。“这是斗争和妥协的产物,也是基于解决问题的需要。”他表示,将外逃犯罪嫌疑人引渡或遣返回国内,对中国有力打击犯罪、特别是外逃的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意义重大,利大于弊。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追逃成本大、追赃返还难,大量嫌疑人因无被引渡之忧且提前转移大量财产,而在异乡逍遥法外。具体到远华案件,追赃并不是那么顺利。
今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增设了第五编“特别程序”,其中第三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大大压缩了外逃犯罪嫌疑人生存空间,同时也为中外执法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专家陈雷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18期)
官员任免:将“网络公示”进行彻底
人事领域的不正之风,正被一种新的监督方式所制约,这就是微博上的集中围观。
山西长治“神童官员”扎堆以及“女商人吃空饷15年变身副县长”、湖南湘潭“拟任90后女副局长”的事件调查和处理结果,已经陆续曝光。这几起因微博发酵的事件刺激着大众的神经,也推动着问题的处理。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副教授认为,“以前这类不正之风也存在,但是因为传播的途径有限,受关注度也不高,所以很难统计。”李瑞昌认为,电子政务的推开,干部选拔的网络公示程序,使得过去可能发现不了的问题,现在容易被发现。
李瑞昌也坦言,目前全国乡镇一级政府中,还无法完全做到电子政务的配套,很多信息的纸质公示效果也并不明显。“不过,县级政府的干部选拔任命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网络公示,今后可以考虑在县级政府网上公示乡镇干部的选拔任用。”
要实现“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李瑞昌指出,应该进一步“加大网络公示的力度,尤其是对于拟提拔任用的干部,其工作年限、业绩能力应该有更加详尽的介绍,最好采用公开竞聘的方式”。
((摘自5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该下河的不仅仅是环保局长
日前,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表示,“检验温瑞塘河治污成效,不以部门报上来的数据为准,要以环保局长和公用集团董事长带头下河游泳作为河水治理好的标准”。
这真的是个好办法。想要彻底治理水源污染,环保局长确实是首当其冲。不过,环保困境,单靠环保部门,实在难以打破。
当下,不少地方奉行的标准是:“小污染可以倒、大污染则要保”,甚至是:“污染事小,财政事大”。一些污染企业的存在,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但其对于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地方政府官员权衡利弊,很可能多数是求经济效益和政绩打眼而放弃环保。
众所周知,环保部门通常只是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上级下的命令,环保部门敢不执行?曾有环保官员无奈地说:“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从来不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承载量。”如今环保部门责大权轻,没有地方政府其他部门的全力配合,环保局长把命搭进去,也未必真能见到环保治理的真效果。
有网友戏称,要说下河游泳,最该下河的非市长、市委书记莫属。当然,要是市长能够带着三套班子一起下河,那老百姓肯定对于环境治理相当放心。
(摘自5月8日《北京晚报》)
武汉平均2年消失3个湖“城市之肺”变“城市之泪”
曾经数百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的武汉,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百湖之市”。然而,最近几年,大小湖泊周围鳞次栉比盖起的高楼越来越多。曾经引以为豪的湖泊,给市民带来的不再是美景和水韵,而是环境恶化和城市内涝。被生态学家誉为“城市之肺”的湖泊,变成了“城市之泪”。
据武汉市水务局统计,2002年武汉市共有200多个湖泊,10年之后的今天,只剩下了160多个。其中,消失最快的是中心城区,新中国成立初的127个湖泊现在仅保留了38个,平均每两年消失了3个湖。
目前城区仅剩的38个湖泊,情形也不容乐观。曾经清冽甘甜、捧之即饮的湖水,不少已变得污浊脏腻,甚至臭气扑鼻,垃圾遍布;碧波荡漾的水面一片一片遭到蚕食,变成繁华的街市、宽阔的马路和成群的楼宇。许多环保人士呼吁: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保护,这38个湖也难逃消失的噩运。
据武汉水务部门统计,1995年以来,这38个湖泊的总水面减少了1083公顷,相当于25个沙湖的水面消失了。而环保部门对湖泊水质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市没有一个湖泊的水可以直接饮用,中心城区绝大部分湖泊已不适合游泳,甚至湖捞起来的鱼也没人敢吃。这座因水得名、因水而优的城市,正忍受着来自各方的伤害。
(摘自5月9日《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