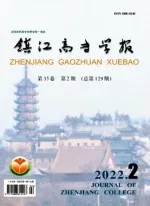论金庸小说的“异质武侠”特色
蔡建美
(南通体臣卫生学校 基础部,江苏南通 226007)
论金庸小说的“异质武侠”特色
蔡建美
(南通体臣卫生学校 基础部,江苏南通 226007)
金庸小说不懈追求的“异质武侠”特色,是整体武侠小说中最具民族性与个性特质的部分。他通过对传统侠义精神内涵的深入挖掘,很好地体现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同时在对武侠思考的过程中,他既张扬了其合理的内涵,对于其负面因素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金庸能全面提升武侠小说品格,成为新武侠小说创作第一人,得益于这样的认识及其在创作中的成功实践。
异质;武与侠;传承;反思
随着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对武侠认知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褒之者称之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1],其意义类似于元曲、小说进入高雅文学殿堂;贬之者则认为“低俗化”明显,是“消极浪漫主义的产物”[2]35。有意思的是,与海内外的媒体和评论界的热烈关注相比,金庸却一再低调地声明:自己写武侠小说,不过是为了自娱娱人,最好不要与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我的武侠小说只有娱乐性”[3]211,但同时他也认为,“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4]表面上看,他的声明是矛盾的,这与武侠小说身份的暧昧与矛盾是对应的,也反映着金庸看似矛盾的创作态度:以严肃作家的态度来做公认的“娱乐性”事业。而当我们离开言说者的众语喧哗,深入探讨金庸的创作观念与其小说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金庸像一名超级的艺术魔法师,在紧张的雅俗对峙这样一场“永远难分难解的拔河比赛”中实现悄悄的“移步换形”[5]274,让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区分显得更加的暧昧而混沌。
1 对武侠精神的传承
侠义精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无一不涉及这一命题,加上后来传入国内的对中华民族有深刻影响的佛家,四大皆空之外还有如来的“狮子吼”,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中,侠义是其中不可缺的一环。
在此背景下,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到陶潜、李白等的侠义诗歌,直至鲁迅的《铸剑》,武侠文学源远流长。新武侠小说文起旧武侠之末,面对的是一个三千年侠义的大仓库,是陈陈相因,还是求新求变,将“在赞扬侠义精神的同时,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糟粕”[2]11的侠义进行现代意义的改造,这是衡量其思想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最重要方面,也是持严肃文学创作态度的金庸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金庸的思考无疑是深入的,通过对侠义精神内涵的深入挖掘很好地体现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司马迁曾对侠义精神做过准确描述: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之矣[6]578。侠义的精神就是为了扶困救弱,仗义援手,不求回报,在普通百姓常常可能遭到飞来横祸而哀哀无告的情况下,武侠小说体现了他们对正义的期盼,它虽然反映的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但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想象,将其艺术化成为一种文学想象,就具有了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金庸笔下的大侠们对此精神可谓是极度张扬。在《飞狐外传》中,主人公胡斐自幼父母双亡,成长过程中倍尝艰辛,这形成了他济危扶困的思想。他与穷苦人钟阿四虽然素昧平生,但就是激于一股侠义之气,同情其家庭的不幸遭遇,而毅然决定铁肩担义,为其除掉恶霸凤天南。不巧的是,凤天南一家却极难对付,不仅自身武功很高,而且在武林朝廷都有广泛的关系,这与传统的武侠中表现大侠们拯救危难的情况迥然不同。在传统的武侠场景中,大侠们往往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行侠仗义轻描淡写,潇洒至极。但作者却不愿意采用这样讨巧的做法,他更希望在类似日常生活情境中表现大侠们的侠义,所以,胡斐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杀凤天南失利,在追杀过程中受到金钱、美色的诱惑,但是他不屈不挠,不求名利,只求无愧于心,一定要杀凤天南为钟阿四一家报仇,而自己为此就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从而将侠义精神张扬到了极致。
当然,金庸小说笔下的侠义精神不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扶危济困,而且推而广之,将其扩展到国家人民,即《神雕侠侣》中郭靖在襄阳城对杨过所说的:“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厄困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为了大多数人而奋斗甚至牺牲自己,金庸认为应该给予更大的肯定。正是在郭靖精神的激励下,杨过在蒙古大军压境的时候,能够奋不顾身地保家卫国,并以象征国家感情的一枚石子暂时结束了两国的争斗,为自己赢得了大侠的声名。另外如张无忌率领明教英豪消除内斗,驱除鞑虏,袁承志帮助李自成推翻腐朽的朝廷,都表明金庸对这种为民族和国家而奋斗的精神给予的肯定。
侠义内涵的另一方面的挖掘在于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小说《天龙八部》写到当时的中国分为五国,辽与大宋相互仇视,甚至互称对方为“宋猪”、“辽狗”,从人格上抹除对方和自己对话的可能性,金庸则在作品中超越了这种思想,探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主人公萧峰就被设计成身处这样一个峰口浪尖的人物,他身上汇集了两个国家的仇恨,也汇集了两个国家的仁爱。他生于契丹,父母被汉人所杀 (其父后来证实未死),可谓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但另一方面,他长于中原,深受汉文化陶冶,他的师傅、养父母、朋友都是汉人,众人给了他最多的爱,他自己也成长为一个汉族大帮派丐帮的首领,同时他又是契丹人,和辽国皇帝结为兄弟,甚至身居南院大王这样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两国恩荣也集于一身,金庸就是特意将萧峰置之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位置上来展现自己对于国家间关系的思考,面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萧峰以其气壮山河的一死,换来了两个国家的和平,而无论是辽国皇帝耶律洪基还是宋朝昏庸的朝廷边将,都受到作者非常严厉的批判。在萧峰身上,寄托了作者理想中的和平、多元并存的现代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2 对武侠的反思
在对武侠的辩证思考中,金庸既张扬了其合理的内核,又对其负面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首先,体现在对“武”的反思上。武侠小说以武名之,武是其精髓,虽然梁羽生曾不无偏颇地说过:“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但武与侠并提,历来都是武侠小说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纷繁复杂的江湖流派、多姿变幻的武艺技击、威力无穷的神奇功法,成了江湖中大侠的立身之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衡量一个大侠地位的最关键因素。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武侠小说中,主人公总是在历尽磨难之后,成为那个武功最高的人,从而拥有了对他人随意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传统的武侠中,掌握了最强武力之后的大侠往往是快意恩仇,纵横江湖,将个人意志化成法律,个人成为最高的审判者和执行者,这对限于日常生活规则中的读者来说,无疑可以获得思想的轻松和愉悦,但金庸不满足武侠仅有的这种娱乐性,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武力到底带来什么?
武力带来仇杀。在江湖之上,武力成为生活中的最高标准,社会遵循着丛林原则,因此,夺取武功秘籍,练得超人神功,少则防身,多则可以随意取人性命。《笑傲江湖》中的五岳剑派和日月教,双方水火不容,究其始,就是因为一本武功秘籍《葵花宝典》导致双方往来仇杀,而其另一版本《辟邪剑法》则使林平之一家惨遭灭门,“武”成了一切祸患的总根源。
对于武的弊端,金庸给出了自己的匡正方案。《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从小便被灌输为父报仇思想,练武成了他的宗教。当他武功越高,对于武的反感也就越强,当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千万老百姓惨死在铁蹄之下的时候,对武的反感也达到了顶峰:“每个人都有母亲,都是母亲十月怀胎,辛辛苦苦地抚育长大,我怎能杀了别人的儿子,叫他的母亲伤心痛哭?”,后来认识到:“学武为了打人杀人,看来我过去二十年全都错了,我勤勤恳恳地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有害人。”推己及人,母爱战胜了武力仇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从儒家的家族伦理所找到的治疗秘方;在小说《鸳鸯刀》里,对武的反思已经直白化,众人争夺的中心原来只有“仁者无敌”四个字,“仁”是作者给出的第二剂药方;而在《天龙八部》中,无名老僧对于武的一段议论:“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强”,而正是因为争强斗胜,强练武技,才导致慕容博和萧远山这一对仇深似海的老对头患上了同样的病症,而正是在二人放弃复仇,相互原谅之后,他们的身体也就恢复了健康,“佛法”是作者开出的第三剂药方。
其次,体现在对“侠客”的反思上。侠客们往往因为意气相投,成立帮派,去实现共同的理想。可惜良好的愿望往往结果悲惨,侠客们遇到了多种多样的人生窘境。
侠客们一般都奋发有为,为了天下百姓,“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墨之侠。他们往往饱读诗书,武艺高强,可谓文武双全,一腔侠义之志,要为天下苍生造就一番伟业。有志向、有本领、有组织,照说理应有所作为,但实际上却往往相反。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对恢复汉人江山所采取的策略就是策反皇帝,可想而知这策略非常荒谬,同时,策反皇帝的依据是“汉族正统论”,而这种思想本身更是荒谬,老百姓可不愿意管什么汉族异族,让自己生活过得好才是根本,荒谬的思想加上荒谬的策略,施行的就是荒谬的行动,而其结果可想而知。而《鹿鼎记》中的陈近南,在台湾被尊为军师,是郑氏的智囊,而其自身武功高强,是中原大帮派天地会的首脑,甚至江湖人称“为人不识陈近南,总是英雄也枉然”,可惜这位英雄中的英雄除了愚忠台湾,实在没有其他作为,后来死得也糊里糊涂。
行侠不成,金庸将眼光投向了另一方面,侠客们开始热衷退隐,我们可以称之为佛道之侠。侠客们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豪情不见了,在连自己的正常生活都难以保证的时候,侠客们就暂时将忧国忧民放到一边。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退隐也是一件难事。正如《鹿鼎记》中神龙教教主夫人所说:“神龙教创教以来,从来没听说有人活着出教的”,所以,侠客们在此不再为了行侠仗义而斗争,而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斗争。可惜,侠客世界是讲武力的,所以,在《笑傲江湖》中,衡山派高手刘正风只想退出武林,致力于自己钟爱的音乐,竟然被侠义派全家灭门;梅庄四友也只想在西湖边颐养天年,但后来依然死的死,中毒的中毒,被绑到了武林霸权者的战车上。金庸对这些侠客寄予同情,同时也是对侠客万能的否定。基于此,我们看到令狐冲、杨过、狄云、张无忌、袁承志能成功引退,远离烦扰世事,无人觉得其背离了侠义,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其实也是一种侠义。
另一些侠客则开始走向心理变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魔侠”。一方面他们拥有超绝的武功,但或出于对权势的渴望,或出于身世的不幸,他们的超强武力成了他们对世界最大的危害,“大奸大恶之辈往往都是大智大慧之人”。如谢逊、萧远山由于家庭血仇而从豪侠变为凶徒,滥杀无辜,在江湖上制造血雨腥风;而任我行、岳不群、左冷禅等人为了夺取权力,无所不用其极,武侠不再是人类世界的拯救者,而是对普通百姓的虐杀者。
金庸对于武侠最终走向了反叛,他的笔下出现了“反侠”。这就是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这个小流氓式的主人公,贪钱贪色,行事更是坑蒙拐骗,这与侠客有了很大的背离。但这并不是作者特意塑造的反面人物,而恰恰是这样的侠客符合国情符合生活实际,与康熙、天地会交往他不忘“义”,与双儿、木剑萍等相处他也有情,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大义上,他率军力抗俄罗斯,维护民族利益,为边疆换来百年和平,正如钱锺书所说,高雅目标得“附之于俗地”,正是他才达到了陈近南等传统侠士想都想不到的成就,在此,作者宣布了传统侠义的末路。
最后,体现在对“侠义”的反思上。侠义精神往往太个人化,情绪化,也容易误入歧途。它一方面具有正面意义,正如鲁迅所赞扬的“豪侠之士”:“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以起之矣,”[7]11但同时鲁迅对这种复仇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女吊》中就曾引用王思任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表明侠义如果滥用,则必然走向反面。因此,金庸笔下既有替钟阿四一家复仇的侠客胡斐,也有一些变态的复仇人物,《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就是一例,他出身富家,但不幸由于家藏武林秘籍而全家被人灭门,“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林平之的复仇完全符合传统的复仇模式,但是金庸却用厌恶的笔触,写到他复仇时穿上华贵衣服,对仇人进行虐杀,甚至置深爱他的妻子于不顾,最终杀妻求荣,表现了“追求正义的声张”过程同时也是人性扭曲和疯狂的过程,从而警示了复仇的负面作用。
[1]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08.
[2]袁良骏.武侠小说指掌图[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温瑞安.金庸茶馆:三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4]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G]//杜南发.诸子百家看金庸.香港: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71.
[5]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7]鲁迅.鲁迅选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胡 菲〕
Abstract:Jin Yong keeps on cha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martial arts chivalrywith special character,which is the partwith the most nati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in his novel.He deeply explore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martial arts chivalry and shows a good relationship of inheriting and creating.During the process of thinking,he not only promotes the reasonable connotation,but also pays full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factors.Jin Yong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martial arts chivalry novels comprehensively and has become the firstwriterof the martial arts chivalry novels thanks to recognition of promoting the moral character and his successful practice in writing.
Key words:special character;martial arts chivalry;inheritage;reflec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tial arts chivalry with special character in Jin Yong's novels
CA IJian-mei
(FundamentalsDepartment,Nantong Tichen Health School,Nantong 226007,China)
I207.425
C
1008-8148(2010)04-0015-04
2010-07-05
蔡建美 (1972—),女,江苏启东人,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