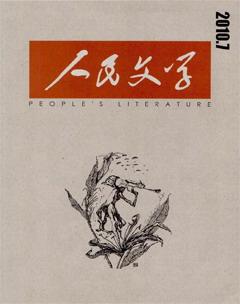自然笔记
刘克襄(台湾)
戈壁来的呼唤——致彭加木
还记得李希霍芬吗?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你在罗布泊的沙漠迷途,被五十度的高温狂晒着,濒临死亡之际,有无想过这位罗布泊的定位者?
来年暑夏,当你在沙漠失踪一年后,我在淡水河口北岸,顶着太阳,走进沙丘时,想到了这位来自普鲁士的著名地质专家。早在深入罗布泊前一年(一八六一年),他也来过这儿,写了一篇北台湾的地质报告。
那年,普鲁士组了一支调查队,准备效仿英国,在远东觅得一处类似香港的港口。当时,锁定的目标是台湾。李希霍芬的职责是实地勘测,供给远在西方的祖国遴选。李希霍芬在北台湾完成勘测后,呈交了一份翔实的考察报告,对台湾称赞备至,但他的调查并未被采纳。
在遗憾和愤懑中,他退出了调查队,却也因这次的离去,日后宿命般地投入中国西北疆域的地理探查,早你一百多年,在这块辽阔死寂的戈壁,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但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出现一如那篇地质论文之匆促,只闪过短短数秒。接下来,挥不掉的,还是你的身影,一位中国现代地理探险家的悲怆。
你已作古,并未来过台湾,我们亦不相识,如此状态,为何还写此文?我一时也难以说清,只觉得自己生命里,潜藏着一股微妙而复杂的情绪,非跟你诉说不可。
在淡水河口北岸旅行前夕,我已经听闻你的事迹。最初,你出现在中日两国电视台合作的《丝绸之路》影片。在喜多郎空荡、略带哀伤的音乐里,我看到了早年丝路的壮丽风景,也崇仰着你探查楼兰古路的精彩成绩。当时,无知、懵懂的我,已偷偷地萌生一个心愿,向往着有朝一日退伍后。能够前往那儿冒险。
来过淡水河口北岸的李希霍芬,也是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或许是这个微妙的因由吧,当我走进这座沙丘时,再次想到你。
到底你我之间有何关系?原来在你失踪前夕,我正服役海军,曾冒险写了一封信,辗转透过回香港工作的大学同学寄给你。在信里。我天真地打探,是否允准一名台湾的年轻人,在未来的时日里,加入你领导的调查队伍。
那封信寄出后,始终未有回应。没多久,我便得知了你的失踪。一九八。年五月,当我转托同学,寄出此封自荐信时,你正带领一支探险队,前往罗布泊考察。六月十七日,你因缺粮缺水,独自一人到沙漠里找水,此后就杳无消息。
对照时日,我相信,你一定未收过这封来自台湾的信。日后,我也放弃了丝路的冒险。但我的退却,并非因了没有获得前往的机会,或者是因了你的失踪,而是另一个因素改变了我的初衷。
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当然跟这座海岸边的沙丘有关了。来年暑夏,自海军退役后,我开始走进这处海岸的沙丘观察。有一回冬天寒流来袭,海岸如极地幽黯的冻土带。强劲的海风吹灌下,潮汐线几无任何动物,石沪更因满潮而淹没于海面下。我肩着背包,全身紧裹着长袖衣物。每道海风都夹杂着盐沙,锐利地针砭着皮肤。我只敢露出双眼,吃力地走在海边。你常在沙漠里,背负着吃重的行李前进,想必更能感受,这种被风沙吹袭的刺痛。
艰苦地走了好一阵,正怀疑如此凄厉的海风下,还有什么生物时,突然间。前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影,约摸老鼠般大小,伫立在灰蒙蒙的潮汐在线。
我好奇地接近,赫然发现,竟是一只鼠灰色的小水鸟。它单脚伫立,头埋入背羽。偶有浪花的碎沫,滚过脚前。当所有水鸟都飞往内陆,躲避海风或觅食时,我着实不懂,弱小的它,为何仍挺立在这儿,甘愿接受冷冽寒风的吹刮。
那种惊奇,我相信你亦能明白,就好像在戈壁上遇见一只狐狸般的困惑。你会讶异,到底是什么驱力,让一只小狐狸千里跋涉,越过几无生命迹象之戈壁,抵达你的营地附近。
当时我邂逅那只小水鸟,心中浮升的便是这种疑问。隔天,再到此地,继续看到一只,依旧单脚伫立在潮汐在线。
它侧着身,以尾羽的方向对准了东北季风,减轻了受阻的面积,好让自己能站得更加节省体力。很显然,它也想避开寒风的吹拂。当我逐渐接近,距离二三米左右,它机警地放下另只脚,往前跑动一小步,随即停了,缩脚如前。很明显,试图和我保持距离。
我停了好一阵,再往前踏出一步。它也往前,继续维持这等安全的间隔。又过了好一阵,我再踏出一步,它又挪移向前。我们就这样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亦步亦趋,在寒气凛冽的北海岸,孤单地相伴着。
初时,邂逅这种小水鸟,印象深刻而有趣,但还没有强烈的感动,或者种下决心。想要在那儿长期滞留。
小水鸟吸引我,是缓进式的。
后来,我分析,它的长期滞留海岸并非巧合。当所有水鸟避开东北风,飞进内陆时,少数这种小水鸟的单独伫立,其实已经告知了,其习性里,必有一潜藏的因子,在其他水鸟不愿意忍受海风侵袭时,它却愿意坦然面对。
我在那儿观察到春天。
有一天清晨,当我又走进沙丘,马上敏感而纤细地察觉到,西南季风开始吹刮。经过一季寒冬,重新被这种季风温煦、和善地吹拂,总是特别振奋,我想水鸟们的心情亦当如此。这也是迁徙的讯息,许多水鸟都将搭此季风,加速北返的脚步。但它非旦未走,在众鸟集聚石沪加紧觅食时,反而花更多时间,走进沙丘里,数度展现类似麻雀沙浴的蹲伏动作。
它的蹲伏让我颇感震慑,一来它并未像多数水鸟展现北返的意图,二则竟然选择在如此炎热干旱的环境继续栖息。我不免进而揣想,难道它会在炙热的沙丘产卵?
在一些世界知名的探险人物身上,我们常拜读到这样纠葛的旅行情境。这只小水鸟的诡异行为,竟激发我理解自然间的某些特例。日后,它在沙丘上还遇到了伴侣。我的臆测果然也无误,真的产卵了。从此,我前往沙丘的次数更加密集。
没想到,西南风不尽然是舒适、和悦的气流,还带来生命繁衍的讯息。
有一次,西南风大吹,沙丘上举步维艰,我试着把铅笔丢到沙丘,不消半分钟即埋没。我很担心小水鸟的安危,努力走到卧巢的位置,没想到,竟目睹了一个震惊的画面。
其中一只,竟在狂风吹袭中,坚持蹲伏在沙丘最高点的巢区,卧着蛋,不愿离去。以当时暴风卷沙的侵袭态势,如果它不起身,沙石就会迅速将它和蛋淹没。
以我对其他鸟类的认知,它应该选择弃巢,先行离开。等风沙平静后,再试着回来看看。但它继续坚守着。很快地,风沙将它淹没一大半,只露出头颈的部位。它继续闭目,静若磐石,不愿离去。
我蹲伏在不远的沙丘,着急地观看着。有一度,真想冲上去,将它抢救下来。但最后还是隐忍住,继续尊重自然的法则。
没多久,不幸的事便发生了。我眼睁睁看着它,在眼前不远的沙丘上,被风沙吹没,寂然地消失。我深信,它是抱着巢蛋一起不见的。
我一边锥心地看着。很奇怪,那时还是想到你。想到,当你最后身陷在沙漠里,面对死亡进逼,毫无援助时,你会想起什么?
你还未失踪前,透过大陆电视的广泛播映,你早已是中国著名的探险人物。在一封
写给郭沫若的信里,你亦慷慨激昂地提到:“我,彭加木,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的发言权。”
失踪以后,你更成为民族英雄了。最近我去丝路旅行,走访了好几家博物馆,里面都镌刻着你显赫的探险事迹。你的名字被置放于玄奘、法显和林则徐等历史人物之后。
你还活着时,我偶尔拜读你的文章,总强烈感觉,字里行间满腔热血,一副沛然莫之能御的民族意识,潜藏着百年来的历史屈辱。同时,一股坚决的傲气,跟你的生命意志紧密结合,也一起缚绑在中国地理探险的大纛上。
郭沫若称许你为“科学雷锋”,我想你是欣然接受的。以你的学养知识和探险能力,同时肩负豪情壮志和国家情仇,才是值得追效的英雄。像李希霍芬之流,恐怕不过是另一个史坦因、斯文赫定等探险家的前辈,挟其殖民帝国之力量,命定地功名成就,但探险的才质犹待检验。
我也相信,死亡对你犹若鸿毛之轻,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在野外遭遇挑战时,难免心存犹疑、茫然。
有一回,我在爬山途中,遭遇土石流的侵袭。那天豪雨不断,前面是断崖,一群山友在后面的林子边缘,等我回报。
我在前方探路,突然间一阵土石流从上方涌出,顿时如大河奔腾,将我和队伍岔开。大雨中,我的眼镜起雾了,看不清前方,手上捉不到任何支撑的物体,更找不到往前的山路。
视线模糊下,仅能以双手双脚谨慎缓慢地探触前方。万分紧急之时,我也试着努力呼喊,但除了轰隆的雨声,根本听不到团队的响应。更糟的是,未几,回应我的竟是另一波土石流的崩落,从头顶流泻而下。自己活像一根漂浮的流木,随时会被吞没,或冲走。
那不过是一处台北盆地的郊山,因山势不高,出发前我做了轻忽的决定,未带任何防寒衣物或救生设备。这等危急万分时,偏偏又双腿发软,力气亦放尽。也不知因害怕,还是寒冷,不断发抖着。我很少这样,斗志全无,直觉自己完了,回不去了。
但不过瞬间,很奇妙的,或许是长期浸淫在山林,我的心里也在那时放空。心想横竖一死,就让自己是人类在此破坏山林的祭品吧。只默祷着,万一自己走不回去,就让土石流完整带走也好。
那样的死亡心情,一点也没有得失的计较,也没什么壮志未酬的遗憾,反而有着逆来顺受的平静,准备接受自然的召唤。所幸,后来土石流并未继续冲刷,我侥幸地逃过一劫。
今年春末,我站在丝路的阳关上,远眺着层层如峦嶂的浩瀚戈壁,想象着你最后的死亡之旅。
当你迷失在沙漠里,那最后的挣扎,会不会如同我的懦弱?在山里遇到小小的死亡威胁,就悄然地屈服,放弃了坚决生存的意志。充满国仇家恨之历史情感的你,跟自然搏斗多年,会接受这种宿命的安排吗?这是我年轻时,也是我年过半百后,继续的困惑。
我亦不知自己观察的小水鸟,最后抱着蛋,在风沙中埋没,它心里想的是什么。那一年看着它的寂然消失,看着它坚决眼神的最后画面,我还是联想到你,想到你一定会握紧拳头,自沙土中悲壮地伸出。
如今回顾一辈子的鸟类观察,日后常在台湾的沙岸遇见小水鸟的同类。早年目睹其中一只的卧蛋和消失,我仿佛已释然,不再耿念在心。关于一个人的生死,时间久了,就像站在广漠的石砾地,凝望星子低垂地平线的闪烁。好像这样的怀念,也就够庄严亲切了。
或许,从半甲子前,我认识你这位英雄时,就一直在离开你。而当我年纪半百,已经离你很远了,才又遽然想到你对我的撞击。
但这时,这样缥缈而扼腕的回忆里,钦慕恐怕早多于崇仰了。
附记:
彭加木(一九二五-一九八〇),广东番禺人。一九四九年后进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一九七九年担任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他先后十五次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一九八。年五月,他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进入罗布泊,第一次揭开了罗布泊的奥秘。六月十七日,考察队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扎营,油和水所剩无几,他独自外出走向沙漠深处找水,不幸失踪。
李希霍芬(一八三三-一九〇五),德国地理学家。一八六。年到一八六二年之间,参与普鲁士政府组织的东亚远征队,前往亚洲许多地方,诸如锡兰、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地。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八年间,在美加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潮。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二年间,转到中国做了七次远征,这段时期中,正式地指出罗布泊的位置(旁边有古接兰遗址),并命名了“丝绸之路”。在近代地理学领域中,李希霍芬被视为重要的先驱,倍受学者推崇。
新中横的绿色家屋
过了山城水里,再往内山行去,只有一条台十六线。
这条山路的尽头,井然二分,看似吉利的数字也变了。绵长的台二十一线紧贴着中央山脉,但南北风光截然不同。
往北行,不远处,日月潭坐落着,沿途开阔,景致明媚,一路好山好水。晚近熟知的一些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或者小区营造的示范村落,这儿也散落了那么好几处。在此仿佛看得到美好的光景,也看得到未来的发展可能。
若折道向南,俗称新中横,道路突地变得窄小,穷山恶水,直通东埔,遥指神木村。过往新闻报道里,雨季一到,凡新中横,都是负面的新闻为多。山崩路断、土石流横阻等不好的印象,常拢集而来。
前个月,我临时要去日月潭附近,拜访小区营造的新景点,一时订不到附近的,只好上网在就近的水里,找间适合的民宿过夜。初时我们以为,民宿就在镇上不远处。岂知,水里范围甚大,非区区一小镇之内涵。当我和内人摸黑驾车,寻路抵达台十六线的尽头,发现不是左转,竟而非得转向新中横时,二人顿时不安起来。
“可以退掉,说不去了吗?”我一边转向,一边迟疑地嚅嗫着。
“可是人家已经准备晚餐,这样太失礼了。”老婆口气还是很坚决。
车子又开了三四公里。一路上,左侧多为险峭的山势,右边则是开阔的陈有兰溪。或许是接近山区,夜空不时急落暴冲的阵雨。月光下,溪水看似优美,但时断时续的豆大雨珠又仿佛提醒着,山洪若暴发,随时可能会有那种挟着巨大土石,浩荡奔腾的骇人情景。
我们欲下榻的民宿叫老五民宿,坐落在上安村,一个叫郡坑的小地方。一般地图上,还不一定注明。连我这样经常旅行的人,久未走访,对此地亦是充满强烈的陌生和疏离。
车子抵达荒凉的村子后,只见街道暗灰灰的,仿佛已半夜多时。单面的一排街屋,几户人家露出鹅黄之小灯和电视屏幕的闪烁,映照着柏油路上湿答答的水溃之光。从抄录的地址索骥,我们小心翼翼地沿一条小径右转,再陡下而行,弯绕至一河阶台地才结束。这段更没路灯,只能靠着车灯搜寻。夜色昏暗,我们虽然看不见彼此的脸,但势必都充满无奈,仿佛误上了贼船。
按木牌指示,驶抵民宿规划的空地后,四周尽是荒郊林野。我们不禁再纳闷,想要下榻的民宿到底在哪?直到把行李卸下,又有一牌子指引方向,才豁然有了另一番新境。
眼前一条蜿蜒的幽深小径,铺着错综的石阶,弯弯曲曲地伸入一座庭园。小径旁并没有路灯装置,路面亦有些崎岖不平。我暗自诧异,这些小细节都没处理好,该不会民宿还未完工吧?还是老板为了省钱而就简?走没几步,才警觉,自己一时心急,大意误判了。
只见不远处溪声潺潺,几只流萤缓缓滑过,周遭蛙鸣亦不断。若是小径旁有明亮的灯光,恐怕就无此风景了吧?而小径刻意弯曲,保持原始风味,也有形成多样风景的功能。我们再举头,林子不远处,一栋二层楼木屋外貌的民宿坐落着,黑瓦白墙散发着和风味,仿佛风景明信片上的画面。
主人似乎恭候多时,仍在一楼亮着鹅黄小灯的餐厅工作,有机的晚餐也早就备便了。这几年在家习惯清淡安全的食物,外出旅行吃东西,甚是辛苦,尤其是走访偏远地区。没想到这家民宿在网络上的宣传,毫无夸张不实之处。二人一边享用晚餐,自是开怀不已。
我们当初在网络上寻找民宿时,主要便是看到了自然农园的介绍,被此一信念而吸引,决定挑此夜宿。但那时还是半信半疑,可能只是广告噱头。现在不仅旅途的舟车劳顿终于卸下,连当初订房的忐忑不安也解除。
桌上的晚餐内容如下:红曲面线、土肉桂佐破布子煨苦瓜、有机蔬菜色拉、金针菇炒洋葱、花生豆腐,以及梅子炖鸡等。几乎所有食材都采用当地自然农园的物产,或者以自家腌渍的食品作为作料。这顿简单而别致的晚餐,从内容的选择即可忖度出主人的理念和用心。
饱足后,走上二楼的客房休息,环顾房间内的摆饰果真无电视、冷气,外头亦无卡拉OK。一般民宿若是如此布置,相信游客必定抱怨不已。但女主人一开始即提醒我们,希望旅人来此敞开心胸,多聆听周遭自然环境的声音,而非躲在房间内观看电视。我虽欣赏主人的信念,但不免疑惑着,到底有多少旅客,愿意选择这等简朴的民宿环境?
净身后。下楼再拜访女主人。她正在餐厅另一角,制作多种口味的全麦馒头。这项副业。如今慢慢地成为老五民宿的品牌。民宿在此偏远位置,能够吸引的旅客着实不多。他们因而发展手作食品,譬如馒头、酿造醋、腌梅、梅精等,试图推广地方物产,同时增添些许收入。
饭后,通常民宿主人都会泡茶,请客人吃些小点心。如果客人愿意聊天,他们也乐意分享自己的生活信息,或当地风物见闻。
这间开业九年的民宿,不只强调建筑的家园美学,以及民宿的在地精神。更难得的,当然是怀抱有机的理念经营。过去我偶遇民宿主人,或有生态观念甚佳者,嘴上喃念环保,但往往力行有限。那天晚上,针对有机理念,我便进一步探询庄主在此自给自足的理念。
原来,男主人姓卢,绰号即叫老五,从小在郡坑的乡野长大。年长后,他到城市的银行上班。女主人过去也是上班族,担任山叶钢琴的老师。后来,他们厌倦紧张而忙碌的都会生活,十多年前决定搬迁回老家。
这样的返乡背景,其实在台湾各地比比皆是,并不特别。但接下来的遭遇,似乎才值得反思。返乡后,老五因为爱喝茶,决心从事茶叶的栽植。他先在日月潭畔购地种茶,起初也洒农药,但他渐渐困惑,农药真能治虫吗?小时候认识的害虫现在依然生生不息,反而是农药必须不断推陈出新。更令他沮丧的是,家乡早已质变,不再如儿时那般淳朴。
“其实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因为人的要求太多。依大自然的法则,农作物只能收成一半,但人全都要,就必须洒药,然后赚比较多的钱,再去买卡拉OK、喝酒……结果呢?没有啊!生活富裕了,精神却变弱了。我们这儿的人年纪轻轻就中风,体态也全都走样了。”没读过生态学的老五,从生活中累积的体验,摸索着人和自然的关系。
他得到一个结论,大自然有平衡的机制,便决定栽植有机茶叶。只是当时有机之风未开,较高的售价使得茶叶销售困难,没想到又遭遇一场土石流,将茶园冲毁大半,迫使他走向民宿经营之路。
为何要盖一间和风味十足的民宿呢?其实,老五只是怀念小时候的乡村,期待有一栋色泽可以搭配自然环境,同时非水泥的建筑。结果跟建筑师讨论后,搭建出了今日黑瓦白墙的模样。如今不远处,他自己和一些友人,利用工作假期,正在兴建另一间屋舍,更充满节能、环保精神。
也不只建筑带着绿色思维施工,连庭园维护亦然。比如,农庄辟建前原有一条长满水草的弯曲圳沟,过去地方政府花钱疏圳,全部铺上水泥,“九·二一”地震时崩毁。老五自己开“怪手”清理,转而以石块重新铺砌河岸,恢复水草多样生长的世界。桃芝台风来袭时,即使大水淹没庭园,溪流仍安然无恙。老五笑说,比水泥还省钱。我们以为那是生态,但那时他其实没涉猎多少生态知识,只是执著地想要恢复儿时所看到的溪流环境,有溪虾和小鱼栖息。
还有草坪上,仿佛种植了许多园艺植物,其实不然。庄主都坚持本地的原生树种,搭配民宿的内涵。我们远看犹如清静典雅的京都别墅。细观之,才知是充满生态内涵,尊重物种的乡土农舍。
隔天清晨,我们喝当地出产的羊奶,吃手工全麦馒头和蔬果色拉。原本一大早想赶去日月潭,因为喜爱整体民宿的环境,又好奇庄主夫妇的理念,遂刻意再留一些时间,继续和他们深聊。
我有一个不解,想从他们口中获得答案。台二十一线贯穿的信义乡,还有紧邻此乡的这里,大抵是每回台风时,屡屡发生土石流的地方,也是生态学者诟病,地质最为脆弱,山坡开发最为严重的环境。夏季一落雨,许多游客都不太敢前来。他们为何坚持在此条件相当不利的环境经营民宿,还要倡导有机呢?
老五的回答很干脆,因为这是祖先的家园,世代在此成长。
除了实践自己梦想中的屋舍,他还希望带动村人一起进行自然农耕,渐渐让家乡的土地变干净。经营民宿不仅能吸引旅客到来,购买当地的物产。透过直接接触,农民发现愈来愈多消费者询问作物是否有机,因而更会思考转型。反之,拜访产地也让消费者认识作物的真面目。
保护土地也维护自己的健康,将来下一代才能继续在此安身立命。老五深刻体认,有机无法一个人单独完成,大家一起不用药,整个环境才可能改善。
早些年,他在乡间,听过许多喷药的可怕案例。比如,有人到葡萄园摘葡萄,当场吃了两颗,嘴巴就麻了。还有一个笑话更离奇,一位小偷摸进农园摘果物,偷了一阵后,结果当场倒地睡着了。莫非是太累了?非也,而是周遭刚刚才喷洒农药,小偷在里面待太久,被熏昏了。
经过他的不断劝说,身体力行,时日一久,周遭的邻人也发现,有机耕作的成本反而比喷洒农药低,又对身体好,遂逐渐认同他的理念,放弃了惯行农业的栽种方法。如此,一个接着一个,好几户都跟他站在同一条阵线。
于是,六七位志同道合的农民相互合作,在这片简窳之地悄然地组成了上安自然农耕队。他们尝试以友善对待土地的方式,种出各种安全的蔬果和农产,宣扬生活中实践环保的重要。
他们种的果实仍是附近的特产,只是梅子没附近的青绿,葡萄亦不如丰丘的肥美。但这些农作对土地、对食用者、对他们生长在这块土地和农耕的人,都是健康安全的。
以前我常疑惑,有机家园的梦想,在台湾会不会是纸上谈兵?在这儿,在台湾最不安稳最恶质的环境,一个从乡野摸索土地伦理的民宿经营者身上,我隐然看到,这等仿佛不切实际的高远理想,早已在默默地辛苦摸索,而且是从民宿的经营出发。
“八·八”风灾时,信义乡再度遭到土石流重创,水里亦遭波及。坐落陈有兰溪畔的老五民宿,还有农耕队还安好吗?后来得知此地安然无恙后才宽心。诸多熟悉的灾区,却特别关心它,无疑地,我们早把这里,这栋偏远小村的黑瓦白屋,当做生命里很重要的旅次之地,也认定是未来偏远地方理想家园的地标。
[责任编辑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