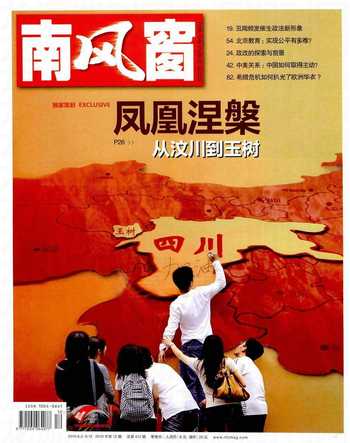似近若远看日本
赵 坚

日本古代自然灾害频仍,经常发生食粮匮乏,为了减少“口粮”负担。老人和幼子首当其冲。弃老戕幼,这在以“孝”、“仁”为人伦中心的古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一衣带水”就成了形容两国距离的“专用词”。的确,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就能从上海飞到大阪;两国的旅客往来,光上海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一天飞往日本各地的航班就有近百个。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2009年到日本旅行的中国大陆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加上港台的150余万,华人游客稳占第一;而同年日本抵华观光的游客更多,有330万人以上,居中国大陆海外入境人数之最,如果加上220万旅行港台的日本游客,人数超过550万。鉴于日本对华游客的进一步简化手续,以及上海世博会的举行,今年两国互访的人数如果首次超过1000万,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中日之“近”。除了地理距离,还包括生活文化方面。我们的主食都是米饭,共同流行面食,而且主餐具都是陶瓷碗盆和竹木筷子。两国的民众都爱喝米酒和烧酒,都喝绿茶,中国有工夫茶,日本有茶道。日本的和服与我们的汉衣、唐装属于同一源流,尤其是女装,都旨在突出女性的温柔婉约之美。日本的住宅建筑,梁柱构架、砖墙陶瓦、飞檐翼角,又和江浙一带的明式建筑十分相似。至于日本庭园和中国园林,皆重视小桥流水,花木草石的布局也如出一辙。日本到处都是佛寺,晨钟暮鼓,梵诵呢喃,香烟袅袅,让人仿佛置身“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光景。涉足山间道左,也不时可见地藏菩萨和双体道祖神的塑像,让人感受华夏的古时光。总之,衣食住行,中日之间初来乍到者,会体会到一种“亲近”的感觉。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正式使用汉字汉文,至少有1600年历史,虽然日本人辅之以“假名”系统,并且有来自“大和”古音的“训读”系统和独特的语法体系,但中日之间有着大量读音相近、字形相同的共同词汇,路标、站名、标题新闻等,大体能彼此了解,即便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也不至于“如坠五里雾中”。对汉语来说,日语是世界上最为接近的语言,虽然从语言学角度论,它们分属不同的语系。而朝鲜半岛上的南北两韩,其语汇60%以上来自汉语,但因为现代以来改以“谚文”(Hangul)书写,国人完全无法辨识,成为一种完全异质的话语系统。
日本崇尚儒学,《论语》家喻户晓,是很多德目的渊源所自,和本土的“神道”一起,构成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日本从政和从商的佼佼者,如首相经历者吉田茂、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小泉纯一郎,以及商界巨子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都谙熟《论语》,不时引用,并用以治国和置业。除了《论语》是永恒的畅销书之外,《论语》类书籍在日本也一直旺销不衰,这也让重兴国学热的中国知识界颇感熟稔。
乍看很“近”,其实很“远”
但是,中日之间,举凡地理、社会和人文现象,乍看很“近”、甚至一模一样,其实很“远”、相互难以沟通的例子,其实更多。
北京、上海与东京、大阪,地理上接近,市民心理却异常遥远,这并不奇怪。柏林围墙隔开东西两个德国的时候,从波恩到伦敦和华盛顿,远比到柏林近;台湾海峡“三不通”的时候,台北的旅客要先去香港甚至东京,换乘飞往大陆的航班;从平壤到首尔,相距不过260公里,而彼此之间仍然视为“畏途”,重要的会谈还需跑到800到1000公里之外的北京去举行。中日两国、尤其是民间,从清朝和江户各自锁国以来,隔阂渐大,怨忿渐深。根据2010年初发表的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世论调查”,2009年在那么频繁的两国政要互访之后,日本国民的“对华亲近感”还是只有38%,只比上年多了8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自2002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对日亲近感”调查,数值一直没有多大变化,2008年对日本“感到亲近”的只有6%,而感到“不亲近”的却超过58%。两国国民间的彼此“不亲近”程度相当一致,只是在中国感到“亲近”的人数更少而已。
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在表面相似的背后,也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中国菜重视油炒,溢脂流香,分重量足,食客多求饱腹;现代日本料理重视水煮,自然清淡,原汁原味,不忌生冷,分轻量少,食客不求满腹。中国的茶文化,重视饮茶的情趣,佐以说书弹唱,热闹非凡;而日本的茶道,重视供茶和饮茶之间的情缘,浅斟慢啜,在静谧安详的品茗之际,体悟茶的禅机。中国人喝酒,常常是为了联络感情,增加友谊,甚至还是工作和生意的延续;日本人喝酒,往往为了排遣孤寂、发散紧张,酒场不分上下尊卑,一杯落肚,可以放浪形骸,不拘规矩。
中国的汉字传到日本之后,虽然有不少保持了原义,但更多的发生了“橘逾淮成枳”式的质变。像“手纸”(信柬)、“御汤”(热水)、“勉强”(学习)、“怪我”(受伤)、“油断”(大意)等都是有名的词例,其它词形完全相同(近),而词义相去万里(远)的词例,在日语中俯拾皆是。如“心中”一词,意思是“自杀”,“心中未遂”是不成功的自杀,“一家心中”是厌世者把家人杀了之后自杀。“无理心中”是强迫家人和自己一同自杀。“交欢”在中文里指男女媾欢,而在日语里只有“联谊”的意思,“交欢试合”译成汉语是“友谊比赛”,而“交欢会”就是我们的“联欢会”了。再有,日文中“拘束”指“逮捕”、“拘留”,“约束”指“预约”、“允诺”,“结束”指“团结”、“连带”,这些同形异义词汇的似是而非现象,是中日之间“似近若远”关系的一种典型折射。
思想史方面更是如此。儒学对两国文化皆有巨大影响,在中国,儒学是“体”,构成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盘。儒学起源于家庭关系,这种关系概括起来就是“父仁子孝”,尤其“孝”在中国是一切德目的本源。有“孝”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在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會选择尽“孝”。而在日本,儒学是“用”,就是所谓的“和魂汉材”。飞鸟时代的日本人吸收儒学的同时,也将佛学和道学一并阑人,构成日本文化的实用理性框架,其本质仍然是起源于绳文时代、神秘非理性的“神道”。日本是多山地之国,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以一家之力,难以筹措有效的农业生产,而需要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协作,所以非血缘的集团,往往重于血缘家族,而作为血缘纽带的“孝”,也就没有像作为集团内部上下关系纽带的“忠”一般受到普遍重视。
日本古代自然灾害频仍,经常发生食粮匮乏,为了减少“口粮”负担,老人和幼子首当其冲。日本曾经有过“姥拾”或者“姨拾”的风习,一些村落共同体有一条不成文的“提”(潜规则),规定在发生饥馑的时候,70岁以上不能再事生产的老妪(姥或姨),必须被送往深山,等待非命的死亡。与此同时,日本各地还经常
发生“子返”、“子杀”等戕害幼童的惨事,民间统称为“间引”(原指禾苗生长过密,农民拔除一部分,使得剩下的部分能得到足够的养分,后来转引为“处理”多余的幼童)。当时的人们认为,婴儿出生后到7岁,一直还是“神之子”,在粮食危机的时候,将幼童处死,就是将他们的生命“返归”神祗,因而毫无“罪恶感”。日本一些神社和寺庙至今还保存着这类题材的图绘,图中神情安详的母亲们,将生下未久的婴儿按在地上,让其绝气,就像在处理小家畜一样。弃老戕幼,这在以“孝”、“仁”为人伦中心的古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汉高祖刘邦为了自己逃命,不惜将子女推出车外,其部属夏侯婴舍命捡回,史官司马迁加以特笔记载,就是旨在批判挞伐这种违反“常理”的举动。
历史观和生死观的殊异
在历史观上,两国的持论也相去甚远。中国古代一直认为历史的发展,在冥冥之中受到“天命”的左右。不主“一姓”、“一族”的“天命”,循环不居,唯德是依,成为“异姓革命”的主要口实,如商纣失德,周武王就取而代之。日本人则认为其天皇一族。来自“神代”的神祗,从“天照大神”到“天孙”迩迩艺,再到初代神武天皇,一脉相传,“万世一系”,皇族就是神族,是国家的守护神,绝无可替代性。
在生死观上,两国之间更是迥异其旨。传统儒学重视“养生”,希冀“安死”,但对死和死后,感到“畏惧”和“悲哀”,不予深究。儒学还认为人生可以通过“立德”、“立功”和“立言”,追求死而不朽;“有德”的人生,可以将“生死”打通,而成为“永恒”。佛教传来并经过改造以后,有了“转生”之说:有德者转生为菩萨,最后成佛,升入“天国”;失德者转生为禽兽草木。在“轮回”中历尽苦难煎熬。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神教”。认为天下“万物有灵”,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没有“善恶”和“是非”的绝对二元对立。最多只有“洁白”和“污秽”之分。“污秽”可以通过“修禊”,净化,受苦、服刑也是净化,而死则是最大的净化过程。中国人“惜死”,对死的态度比较“消极”,死了“一了百了”,是一种无奈的“终结”。日本人比较“崇死”,对死的态度相对“积极”,死是对“今生”的清算,“重生”(来生)的开始。儒家和佛家强调“积德”、“修行”以抵达“彼岸”的永恒世界,神道则认为死了就能“成佛”,再“污秽”不过的人,死后都可以转生为“无垢”的婴儿,将“前愆”全部洗净。
日本有一句熟语叫“遙远的邻居”,纵观上述诸象,日本确实是我们一个非常“遥远”的邻居,它近在“一衣带水”,却又远在“天涯海角”。日本显“远”(距离),是因为我们不能辨识其“近”(现状),而把握其“近”,或许还得从“远”(文化、历史)人手。通过厘清其历史、文化和信仰诸“荦荦大端”,也许我们能把“近”在眉睫的邻国日本看得稍微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