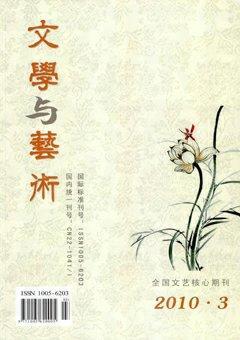小议电影中的“生存”感知
李 劢
【摘要】从到“永恒”与“短暂”的哲学范畴,到电影造就的大众性、娱乐性的直观感受,从“追求——幻灭——追求”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文章对电影中潜存的“生存”做出感知与思考,提出,电影不仅仅是精神的愉悦、审美的享受、境界的超越、人格的升华、灵魂的净化,更多的则是对“生存”的感知与思考。
【关键词】生存;永恒;短暂;追求;电影
“永恒”与“短暂”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对立统一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有时可以在短暂而有限的一生中实现对生命的永恒超越,有时却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巨大困惑。我们可以在悠美的《蓝色的多瑙河》中尽情领略自然界的伟大胸怀,在凡高的《向日葵》中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和对生活的执著: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的审美空间时,定会引发人生的短促和对生命的焦灼。
人类的追求是永恒的,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实践不能肆意而行;美好的爱情是永恒的,尽管仅发生在刹那间;真挚的感情是永恒的,哪怕是深埋心灵深处,历经百年也会历历在目;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虽然经过海水的长年侵蚀,但风采依旧。我们在这无限的空间感知“生存”, 是艺术的、是自然的、是真实的、是触动灵魂的。
在许多人看来,“电影文化”是与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我们以“生存”反思的视界和文化视野的状态,来看待电影文化,便会给予它全新的感知与阐释。电影很多时候,以其不同的表现手法与方式,将人与人地碰撞、故事群体的构架、冲突点的揉合,统统加入了感知度的二律悖反,对生命本体意义作出了电影视觉的体现。在空间中,带有异同性的“生存”感知,将每一部电影表涂出各自的色彩。对于电影大众文化于意义的消解、价值的削平、深度的瓦解、本质的颠覆等,人们虽不乏深刻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却也能够站在“反精英”的立场上给予足够的理解。的确,对于看到的许多电影作品,我们无法甚至也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精英文化阐释模式加以学院化的解读。人们欣赏和接受的电影作品,期望和实际得到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工作时间以外的身体放松、精神愉悦和思想休闲,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思考。
追求——幻灭——追求,是人类生存境遇的生动写照。人类正是在追求与幻灭的不断交替中实现自身的终极超越和永恒 发展 。追求与幻灭也因此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常性话题。正是因为不断追求,保尔才在困境中实现生命意义的升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因为追求生存的权利,“老井”村民才世世代代不忘找水,尽管是历经磨难(《老井》):正是因为追求人性自由和做人的尊严。“我奶奶”才不顾世俗的反对和道德的谴责,果敢地与“我爷爷”野合于那片高梁地: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地冲向日本军车(《红高梁》)……然而,有追求就有幻灭。人类正是在一次次的幻灭中走向理性和成熟(当然也不排除“幻灭中的绝望者”)。人类无法回避幻灭,所幸的是人类并没有为幻灭所羁绊,而是在幻灭中不断地追求。老渔民圣地亚哥外出捕鱼,尽管遇到了鲨鱼群的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放弃,而表现出了不畏艰险的“硬汉精神”,与鲨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虽说那条特大马林鱼最终只剩下了空空的骨架。谁又能说这是一种失败?(海明威《老人与海》)“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俨然,这正是人类不断战胜自然、超越自身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向度和思想支撑。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撞冰山的确是个悲剧。但是老船长那刚毅的眼神、露西对真爱的执著、乐队的临阵不乱和对岗位的坚守、落水者的苦苦挣扎、发掘队十年的艰辛努力等,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人类不会在幻灭面前低头.人类绝不会放弃追求。只要信念执著,不断追求,继续奋斗,人类就会铸造真正“永不沉没”的“生命之舟”。时光在电影中浓缩了起来,将一瞬间的感知点燃了。
电影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从特殊的视角去表现眼中(外在世界、有形世界)和心中(内在世界、无形世界)特有的世界。以艺术的形式对外部现实世界作出直观反映,同时还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人的心灵世界,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思索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充斥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人类既有追求又有幻灭,既有成功又有挫折,人生在短暂与永恒的二律背反中演绎着一幕幕悲喜剧。电影世界所表现出的既有人类驾驭自然、追求永恒、期待成功的欣喜与梦想,又有不遂人意、失却永恒、归于失败的无奈和惆怅。电影能够客观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人类生存空间的特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停滞的而是变化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一维的而是多元的,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生存的价值是什么?尽管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每一部电影也以不同的解读方式,给予着不同的回答,但却在不断地在向观众作出特有的暗示。价值的判断和判断的价值潜在地贯穿着电影的始终,导演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嵌入了关于人类生存价值的宏大主题。
在电影的世界中,我们对于“生存”的感知,还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生命学说,电影的本体生存、文化产业的持续生存都是我们感知与思考的范畴,电影传达出了对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感悟,娓娓的叙述中蕴含了哲理,情节变幻中体现着思辨,从而使“电影文化”超越了普通的意义,成为承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以至人类生存价值、意义的航船。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2]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3]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