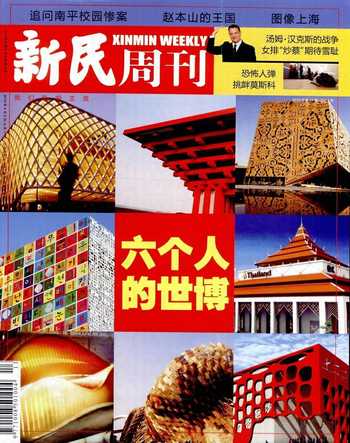政改不能寄希望于乡政府
于建嵘
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一个问题,从哪里改起?从中央改,还是从地方改,从司法制度改,还是从选举制度改,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改?有时候,人们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基层的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闯出一条新路,然后可以得到肯定和推广。就像最近四川巴中白庙乡公布了政务开支明细,大家就在探讨此事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上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地方的基层官员身上。
这是三个原因决定的:第一是地方改革的动力不足。地方领导进行改革的动力无非三种。第一种是压力,当地人事关系复杂,派系斗争激烈,社会管治困难,地方官员只能搞改革;第二种是个人因素,不少地方政治改革中都可以看到那些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基层官员的身影;第三是出于政绩方面的考虑,如果一个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经济搞不上去,官员出于政绩考核的需要,会想办法从其他方面下功夫,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地方搞政改,空间也有限。搞政治改革有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底线在什么地方。政治改革不同于经济改革,后者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有一个硬指标,也即GDP作为考核的依据,政治上的刚性限制很多,随时可能被否决。比如步云县搞乡镇选举,就有人说他们违宪。地方官员搞政治改革,与其说是试验,不如说是试探,试探底线在哪里。
第三是制度化程度低,人走政息。地方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主事者的个人因素太大,改革措施不能制度化,下一任官员完全可以不理前任的这一套。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改革才有幸存下去的希望:前任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最高层面的肯定;或者前任官员升迁,直接领导现任官员;或者媒体、学者和上层不断关注,改弦更张的成本较高。
20多年来,各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探索,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正是由这些原因决定的。在今时今日,政改需要中央做出安排,没有这个环节,中国的改革就只能是一种媒体和知识界内部的共识,无法转变成普遍的社会行动,最终只能变成五年一轮回的心理安慰。
这个过程中,建立两个共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在宪法的基础上解决权力来源和权力监督问题。第二,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监督基层的权力运作,改变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
政治改革之所以应该把目标定在基层,因为上层和中层的改革很困难,不仅没有动力,也没有路径。过去20年里,我们谈政治改革,注意力都在村一级,但村不是一级政权,乡镇的权力也不完整(起码没有司法权),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县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
中国的县是很特别的。县以上的官员都是管官的官员,不用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只有县政权是直面民众的权力。这一级政权没什么钱,财力大多被上级或更上一级政府抽走了;也没什么人,官员流动性很强。我去过的有些县,所有的县委常委都不在当地生活,都住在邻近的大城市里,一到周末,一个人都找不到。看上去,县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无足轻重,权力很小,但实际上,有些县委书记什么事情都敢干,拥有无边的权力。
这些年来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很多群体事件都是在县里发生的,县政权是群体事件中人们诉求的主要目标。县里的压力很大。以维稳为例,不管是省级还是市级政权,维稳的压力不会涉及所有官员,唯独县里存在一票否决制。县里的官员,在维稳的问题上,人人有份,谁工作做不好,谁就要丢乌纱帽。
这种压力已经迫使我们要尽快改变县级权力的来源方式,尽快完善县级权力的监督。第一步应该从人大制度开始,缩小县人大的规模,让人大代表职业化,排除官员当人大代表,以便人大监督政府。第二步要让县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在人、财、物上与地方政府脱钩,用独立的司法来制衡县政府的权力。
当然,我们用人大和司法来制衡县政府的权力,也应该把本地事务的决策权还给县政府。
最后还应该检讨目前异地为官的任职回避制度。本地官员不由本地人士担任,这种制度在皇权时代是有效的,也不无必要,因为官员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与地方利益切割开来。有这个制度,很难培养对地方有责任有感情的地方政治家,老百姓说“第一年换人,第二年捞钱,第三年调动”,每一任官员都要重新熟悉情况,有百害而无一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