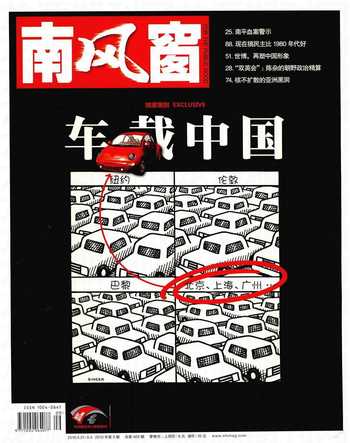“政府俘获”:权力寻租的高级形态
卢正刚
长期以来,我国腐败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执行性的腐败,即政府公职人员在执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有意降低或者提高标准以谋取私利。一般来说,从事这种腐败行为的官员主要利用法律法规赋予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规定的上下限之间给行贿人方便。直到郭京毅案曝光,人们才窥知权力寻租的高级形态:“政府俘获”。
据公开资料显示,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巡视员郭京毅在《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两部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故意通过含糊性和难以操作性的条文为外商能够逃避监管进入敏感行业留下漏洞。3月18日,郭京毅案正式开庭审理,从法庭查明的案情来看,所涉金额并不很大,但该案却是我国目前为止查明的唯一一起证据确凿的“政府俘获”案件。
所谓“政府俘获”,通俗讲就是立法腐败,可以解释为负责立法的政府公务人员接受企业(或集团)的贿赂,有意识地为企业制定有利于其获得长期利润的法律法规。它有以下几个不同于其他腐败案件的特点:
一、“政府俘获”是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渗透的升级化,是政策法规制定者和行贿者之间的买卖政策法规制定权的行为,能为行贿者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与执行性腐败相比,“政府俘获”对企业或集团来说是资本权力化的过程,对法规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则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这表明权力寻租双方不满于过去的“小打小闹”,而是朝着更深层次的利益结盟方向发展。
二、“政府俘获”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相对来说,执行性的腐败只要官员换人,漏洞就可以弥补,而“政府俘获”却很难弥补,法规政策一旦被“定制”,会导致整个产业市场为某些企业集团所垄断。郭京毅的行为更直接导致中国的产业市场被外资所控制,据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称,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市场控制程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这其中固然有我国原来法律政策滞后的因素,但上述两部法规的出台显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政府俘获”行为具有更深的隐蔽性。长期以来,由于从事法规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整天与企业直接打交道,因此对这些公务人员的监督是目前我国反腐败的重點。而制定法规政策的官员一般与企业没有直接的联系,常被认为没有“油水”可捞,所以至今不是纪检监察部门重点防范的对象。这次郭京毅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其同学兼同伙张玉栋被其恼羞成怒的情人执意告发才得以揭露,否则,法律制定过程中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等足以作为借口遮掩其非法的行为。
四、“政府俘获”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虽然,郭京毅案是我国目前为止查明的唯一一起证据确凿的“政府俘获”案件,但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如一些城市出租车市场垄断就和出租车公司对相关政策制定者的收买相关,直销行业的立法和直销牌照对国外少数企业的颁发等。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乔尔·赫尔曼等人在1999年对前苏联和东欧等22个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后发现,“政府俘获”现象在转轨国家普遍存在,其中11个国家非常严重。
但现状却令人尴尬,对这类腐败行为,中国的刑法缺乏针对性的罪名,只能以受贿罪论处。而这类犯罪行为可能受贿金额不一定很大,但危害却极大,如果以通常的受贿罪来论处,尚不能准确反映其罪行。有媒体提出以受贿加汉奸的指控而对郭京毅处以叛国罪,也不合适,因为“政府俘获”行为既可以向外商出卖政策,也可以向国内利益集团出售。
根本上降低其危害,要通过加强对法规政策制定者权力的监督,并分散其立法权来实现。长期以来,我国部门性立法具有权力集中和不透明的弊端,加上立法权本身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公众很难参与,为“政府俘获”留下漏洞。对此,人大应强化立法权的行使,重要法律尽量自己制定,可以吸引专家学者参与,甚至可以外包。对于由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法规要加强监督,严格程序规定,特别是充分听取吸收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诉求,公布草案接受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实现由极少数人垄断立法权向公众参与立法的转变。
另一方面,在具体人事安排上,应推动政策法规制定人员的岗位交流。郭京毅在外资政策制定岗位一干就是20多年就是一个典型,这为其利用对政策的谙熟和长期的人脉资源来寻租提供了条件。
乔尔-赫尔曼指出,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是一种内生性病症,是资本和权力联合的深化和发展,它将阻挠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改革者的努力。这就是在具体的对策背后,真正的挑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