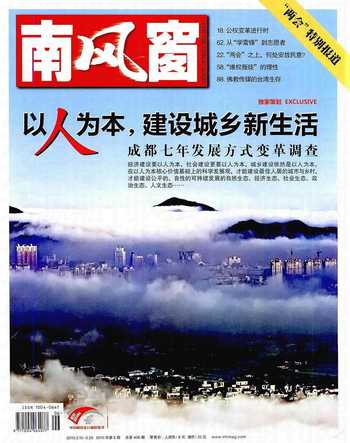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水
尹鸿伟 魏 晨

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成都市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限设定为“长久不变”,为日后土地有序流转、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奠定扎实可靠的基础。农村产权改革实际上是艰难的利益调整。
成都下辖的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村口的巨幅宣传牌上“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两行大字赫然醒目。新春刚过,开满油菜花的鹤鸣村表面看似宁静,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已经令其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这里的农民的生活主题就是每年奔向大小城市打工。如今,随着农民对于土地和房屋确权完成,农村社区开始复活。
成都市从2008年开始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准确地触及了土地这个本质话题。“农村发展钱从哪里来?”这是成都自2003年开始城乡一体化改革就一直思考的课题。成都的改革者认为,农民实际上是端着“金饭碗”过着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日子。改革者希望,把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与维护农民利益结合起来,促进土地要素市场化,进而带动“农村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成都造就新型城乡形态的关键环节。
从试点开始的改革
2005年夏天,成都市农委对全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全市集体经济年收益达到10万元以上的村占8.35%,5万元以下的村占38.11%,无集体经济收益的“空壳村”比例达到35.24%;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益能分配兑现到农户手中的仅占39.33%。
鹤鸣村地处肥沃的川西坝子,2007年,连接成都至青城山的成青快速公路经过鹤鸣村,昔日的“边角地带”变成了“香馍馍”。这一年,村里40多亩土地流转出去了,“粪都不浇一下就有钱进”,过去外出打工抛荒的村民开始找村干部,想要回退耕的承包地。
这确实让鹤鸣村村干部很为难。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不愿意种地了,原因很简单:打一天工就可以买10多斤大米。在鹤鸣村八组,长期抛荒的土地就有五六亩,组长只能把抛荒田地需缴纳的税费分摊到其他村民头上。而村委会主任余跃每年多了一个任务:挨家挨户恳求村民耕田种地。
“土地联产承包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可土地上刨不出‘金娃娃来。”2001年开始,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开始试点,到2006年,农民不仅不再交各种税费了,每年还有种粮补贴。土地上能够产生的好处又让不少村民心动了。
距离鹤鸣村几十公里外的大邑县韩场镇兰田社区,这些年来食用菌产业风生水起。到2009年底韩场镇流转的4000亩土地中,大部分集中在兰田社区。
成都希望土地流转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增强,闯市场的本领进一步增强。可农民闯市场的动力在哪里?早在2003年,成都部署城乡一体化战略时,就提出探索建立农村与城市同步增收的渠道,通过土地规模经营等形式,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但一个现实的难题又摆在成都市面前:尽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民个人所有制的集合,农民是集体产权的最终所有者,但农民个人并不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手中拥有的土地权利虚置,资源难以变成资本。
在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看来,症结在于农村没有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要素市场没有形成,土地、人、资金没有真正激活”。2007年2月,成都市委召开了一次城乡一体化工作会议,“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的观点正式抛出。
“产权改革过程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利益,但对整个农村的发展有好处。”在孙平看来,农村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调整。“过去政府花很小的代价从农民手里拿到土地,转手可以增值好多倍。政府在中间拿大数,却没有去实际解决农民的问题,这也是‘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实质所在。”
一位参与改革试点的学者透露,改革中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非常大”:“成都郊县包括那些有产业项目支撑的村镇,地方政府就不太愿意搞确权。不搞确权,如何维权?又谈何产权制度改革?每次开会研讨产改,部门与部门之间唇枪舌剑,叫争吵都不为过。”他表示,成都甚至有某官方研究机构专门出报告,表面上肯定农村产改的核心就是确权,实际上却希望借农村产改“变相”回到以往的土地制度,“这实际也反映了地方高层对改革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不可否认,这给改革带来了很大压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敏感”,成都市决定在双流县、温江区、都江堰市、大邑县首先进行试点,而都江堰市在平坝区、沿山区、山区,选择了不同产业类型的6个镇20多个村试点。试点内容包括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房屋所有权进行确权登记,明确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到村或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确权到户。
“产权制度改革刚开始时,我们村干部就分析,第一轮土地联产承包改革让农民吃得起饭,第二轮土地联产承包让农民有了定心丸,这次改革应该还是有好处。”作为最早的试点村,村支书刘文祥表示,刚开始时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改革就是要摸清村里的家底。
刘文祥说:“搞农村基层工作的人都知道,对农村来说第一难的事是计划生育,但其实调解土地纠纷比计划生育还要难。过去由于农业税、打工潮等很多原因,一些农民把土地弃之不种,别的村民把地种了、把农业税交了,但这块地到底该算是谁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村干部调解起来十分头痛。”新的起点突出公平
2008年3月的最后一天,余跃和鹤鸣村7组的34户村民首批拿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以及与城市房屋同证同权的《房屋所有权证》,他可能是中国此轮农村产权改革中获得确权颁证的第一人。
和余跃一样,全村574户农民每家每户都拿到了三证。少数有林地的还多一份林权证。除了“四证”,大家还领到了“两卡”,即耕地保护卡和养老保险卡。成都市在产改中提出,创新耕地保护机制,由市、县两级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安排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提供养老保险补贴,从而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
都江堰在产改中确定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联社和乡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分别作为组、村、乡镇一级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仅统一规范了所有权主体,而且建立健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随后,成都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两个引擎_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和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成立,决策者希望用政府有限的启动资金撬动金融及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向现代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
确权后,农民手中拥有的权证“含金量”在于:持证的农民可以将承包地以多种方式流转进而获取各种收益。对此,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形象比喻道:农村产改“相当于揭开一个蜜蜂窝,当我们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制度后,就如同把蜜蜂都驯服了,我们才能享受蜜蜂窝中的蜂蜜”。
2008年10月28日,成都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了综合性的农村产权交易所。交易所将为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项目提供专业服务。2009年,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基本完成,市级耕保基金筹集全部到位,254个乡镇发放耕保基金11.4亿元,惠及109万农户,涉及耕地384万亩。农村产权交易流转2.7万宗、金额21.2亿元,制定出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办法。
2009年11月,鹤鸣村村民手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全部更换了承包年限:土地承包截止期限从“2027年”变为“长久不变”。土地问题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认为,成都建立的耕地保护基金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系,为产权“长久不变”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完善工作还在继续。成都市委、市政府要求,一定要做到地、账、证、合同、耕保金“五个一致”,只有坚持确实权,才能为日后土地有序流转奠定扎实可靠的基础。
变化还在继续:2009年,韩场镇被确定为大邑县产权融资试点镇;2010年3月,兰田社区两户村民将凭着确权后的《房屋所有权证》,在大邑县产权流转担保公司的帮助下,获得5万至10万元不等的融资贷款。
在鹤鸣村,确权后的村民,自愿加入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项目。村里引进了一个135亩的鲜花基地,一户村民不愿意流转自家的土地,在自家的承包地上继续耕种喜欢的粮食作物。兰田社区村支书李俊江认为,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民腰板更直了,愿不愿意参加土地流转,自己说了算。村里只能尊重村民的决定,但对引进企业确实有影响,只能继续做村民的工作。
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家泽表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再造,离开了这一步,农村改革就是建立在沙滩上,没有稳固踏实的基础。
平实有序的民间智慧
2008年3月,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鹤鸣村调研时问刘文祥:产改中的矛盾是怎么解决的?刘的回答是:我们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李春城再问:你这里就是最基层了,怎么还有基层?刘又回答:我们的基层就是各个村民小组成立的议事会调解小组。
村民议事会伴随着产改应运而生。成都市要求,参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干部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宣传动员时,部分官员对如何解决确权中的财产或使用权公平分配问题,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是到了村组开座谈会时把问题和政策交给群众,群众一参与,问题反而迎刃而解。
鹤鸣村成立了议事会,每个小组成立调解小组,专门调解村民间的确权纠纷,调解小组由各小组按照每5~15户产生1名村民代表投票选出来。鹤鸣村调解小组制定了五条原则:一是“要公道,打颠倒”(相对公平);二是“多比少好,有总比没有好”(先来后到);三是“吃笋子要一层一层地剥”(循序渐进);四是“说话要算数”(诚信);五是“大家同坐一条船,要同舟共济”(友爱互助)。
但村干部也有头痛和委屈的时候。听说要确权颁证,鹤鸣村常年外出打工丢出承包地的村民开始回来找村干部要承包地了。村民罗廷贵,1998年全家外出打工,土地丢给村里时写了一份承诺书:30年内不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听说产改开始后,他从几百公里外赶回来了。
村民只知道自己有多少亩承包地,可究竟村里有多少承包地,有些村组的村民不清楚。鹤鸣村四组原来的村民小组长去世前一直没有向村民发放承包地合同,他去世后,小组村民的承包地合同和原始资料找不着了。确权时,四组新任组长只得重新登记、造册,重新建立每家每户的承包地档案。
经过近一个月的登记、测量、公示过后,鹤鸣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到村或组。而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则全部确权到户。为了显示透明,柳街镇从600多年前的“鱼鳞图”获得启发,开发了“鱼鳞”数字化系统,通过测量和结合卫星地图等,精确地确定了农民土地的权属。鹤鸣村每家每户都在全村土地“鱼鳞图”上面按上指印,看起来就像鱼鳞一样。在这张全村地图上,每一块房屋、宅基、承包地、林权的归属都显示得一清二楚。
产权改革确权时,罗廷贵的要求被鹤鸣村议事会成员驳回。他找了刘文祥三四次,后者的回答是:议事会决定的事情,村里不能更改,“不能让种田的老实人吃亏”。
成都市国土局官员杨珍惠表示,没有承包地的农民要求调整承包地,这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权利,而减少的人员不退出承包地又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与不调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邑县农发局工作人员贺定胜表示:在2009年,大邑县有500多名村民到县里上访或咨询,“为什么有的人没有承包地而有的‘死人种活人的地?”
2008年产改开始时,听说要重新测量调整承包地,补足承包地补足农户田块,大邑县韩场镇兰田社区15组村民刘汝林坚决反对。刘汝林老两口耕种了6亩多承包地,远超出村里人均承包地标准。他儿子考上大学,承包地没有退出;女儿出嫁,承包地也没退出。
尽管有村议事会和调解小组多次做工作,刘汝林底气很足:确权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颁发给我了,无权再更改。村支书李俊江道出了刘汝林的“小九九”:2009年,兰田社区引进了一个企业建花卉基地,每亩土地流转金折合800斤大米,刘汝林担心:如果发流转金,这部分钱就发到其他村民手里。
刘汝林决定上访,可上访两次,有关部门实地调查后,给他的答复是尊重村议事会和本组调解小组的决定。2010年2月23日,刘汝林改变了主意,他主动找到镇上,同意退出一亩多的承包地。有人猜测,议事会决定的事情既然征得村民同意,大家肯定对刘汝林的做法有意见,每天在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刘汝林心里也不好受。
产改中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但因为发挥基层的主体作用和智慧,整个过程相对平缓。而政府在其中也非常注意不能激化矛盾的导向。这是成都农村产改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