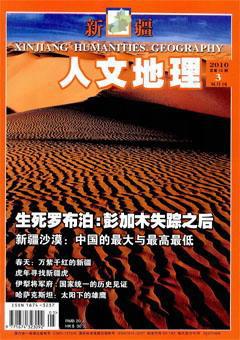打马球俑与木亭模型:西域唐风中的文明碎片


“打马球俑”和“木亭模型”是唐代盛世文化的代表,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见证,一武一文,一动一静。全方位地体现了唐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全方位地表明了新疆与内地的渊源,以及新疆是中西文化交汇地。
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内举办的“智慧长河”中国文物精品展,所展文物都是从全国各省市区精选的、最能体现中华文明和智慧的国宝级文物,闻名中外的《清明上河图》原作也在展品之列。
新疆人选的两件文物珍品“打马球俑”与“木亭模型”,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一同亮相。这两件入选文物均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葬出土,艺术地再现了昔日的唐风遗韵,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深刻影响。
阿斯塔那古墓群分布在吐鲁番市东南40公里的阿斯塔那村北和哈拉和卓村东。墓葬分为三个时期,前后延续五个世纪,最早者为晋泰始九年(273年),最晚者为唐大历十三年(778年)。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发掘二百多座古墓,出土数千件珍贵文物,包括丝毛织品、陶器、木器、钱币、泥俑、墓志和文书等。
西域“打马球俑”的文化魅力
在中国唐代,马球运动非常流行,从宫廷到民间都广泛展开。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唐代马球运动遍布全国,关中地区、江南一带,就连南部的桂州和西部的沙洲都有记载,更西的当属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打马球俑”了,它是打马球运动在西域流行的最好物证。
打马球,又名击球、击鞠,目前有波斯和吐蕃传入两种说法。无论从这两地中的何地传人,但马球从西传人是肯定的。
参展上海世博会的“打马球俑”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高29.2厘米。马上人物蓄八字短须,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紧身绛色长袍,脚登黑色高筒皮靴,右臂前伸内折,手握一木棍上扬作击球动作,骑在四蹄奔腾的白马上。击马球者所戴幞头在唐代文物和墓葬壁画中都常见,是当时男性普遍装束;所穿圆领紧身绛色长袍及脚登高筒皮靴的样式,都与中原出土的墓葬壁画中的打马球服装无二,就连马的装束也与中原地区一致。通过这些,人们又分明感受到打马球运动是全国性的运动,这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文化背景。
唐朝在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交流,西域的文化艺术对中原有重要的影响,唐朝以开放之姿吸纳这些多元文化,形成了博大包容的唐文化。“打马球俑”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展现了驰马挥杖强体魄的大唐雄风。
“打马球俑”不仅是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考察唐代马球运动规则的重要资料。根据唐代文物和文献资料分析,打马球必备球、球杖、球场、球门、良马,还有球衣、类似看台的楼亭以及分队比赛记分取筹的规则等。仅从一件打马球俑,我们便可直观地得知当时打马球穿的服装都是紧身衣裤,衣服是窄袖,裤子也不肥大,腰带紧束,足登高筒皮靴,以及马的装束和球员击球瞬间的姿态。虽不可知球杖具体样式,但也能大致得出球杖的长度。
马球从西传人,球的制作似乎与西域也有关,唐代西域安国进贡的马球为当时珍贵的马球。“球”通“毯”,看其形旁可知球的材料与毛有关,制作大抵先编毛结团,在外面裹一层皮革,再施以彩绘,使球更为美观,在激烈的比赛中更加醒目。球杖制作也极为精良,尾端取惬月之状,正所谓“球似星,杖如月”。
唐代马球运动十分普及,打马球的场地也遍布各处,从皇宫街市,到山野树林,随处可见马球比赛。皇家贵族的球场十分气派,不仅有专门球场,还有观战的亭台楼阁,为了避免打马球时尘土飞扬,还在球场上面洒油。与皇家的排场相比,普通百姓就没这么讲究了,只要有一块宽阔平整的空地就行了。敦煌歌辞《杖前飞》专门描写了打马球的场面,其中有一句“毬似星,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冲穴”,这个“穴”应当是球门了,马球直冲穴,穴应当在地面。
唐代打马球取分比赛的规则,两队加起来大致有十来人,分别穿不同颜色的球衣。
既有“打马球俑”出土,打马球风想必也在吐鲁番出现过。可能“打马球俑”墓主人酷爱马球运动,希望去了另一个世界后,仍然能银镫金鞍,驰马挥杖。
展现唐风遗韵的“木亭模型”
亭,体型小巧,造型优美,作为建筑小品,由亭基、亭身及亭顶三部分构成,其造型可以变化万千,灵活自然。亭的平面形式多种多样,除了一般常见的四角方形,还有六角、八角亭,以及圆亭,亭顶也有攒尖、歇山和重檐多种形式。亭由亭门、亭檐、亭壁、亭身雕刻、亭顶、亭窗、亭廉、亭中设置等要素构成,但不是所有的亭都俱全这些要素。从材料上看唐亭有石亭、木亭、竹亭、茅亭等。
“木亭模型”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501号墓,宽24.4厘米,高27厘米。整个木亭充满盛唐气韵,外形酷似世博会中国馆。该亭为随葬明器单体建筑,木质材料。亭子平面为正方形,八柱,进深各为三间,柱头连接亭顶部分比较复杂,柱头有卷刹,柱间以阑额相连,柱顶铺作平座华拱后尾,以榫卯相连,没有亭顶,根据亭子平面推测,这应该是一座四角亭。亭子四周有木质勾栏,正面中部和两侧尾端各有一出口。这座木亭模型十分明确地展示了唐代栏杆、柱式、斗拱等的具体做法。唐诗中出现四角亭的形象最多,不知是因为四角亭为唐代诗人所喜欢而多次援引入诗,还是因为唐代的四角亭明显地优于其他形状的亭而广泛构筑,总之可推测四角亭的广泛存在是肯定的。
亭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其广泛,或是构筑于园林别业之中,以为日常休息游宴之所的园林亭;或是建于山林风景区以便倚亭观望绝美风景的风景亭;或是置于交通要道之处,以为邮驿传递战报、信件等重要信息及为羁旅游子居宿之用的邮驿亭。其中以园林亭数量最多。这座亭为木质,四周有勾栏,亭台一体,理应为园林亭或风景亭,置于文人住所的水景边,或置于风景绝佳的山林中。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文治武功,震烁古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西域与中央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并互相影响。唐文化吸纳各种文化,形成具有很强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因此唐中央与周边的文化共性占主导地位。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大量文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大量文书出土说明,唐时期吐鲁番地区通用的文字为汉文;各种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所着的服饰与中原地区一样,包括女性化妆,以胖为美的风尚也清楚地体现出来;绢画和各种俑表现的娱乐活动在中原都能找到对应。“打马球俑”和“木亭模型”只是众多文物中的代表,一武一文,一动一静,全方位地体现了唐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以唐为鉴,只有国家安定统一,各民族相互团结,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使国家富强,走向繁荣,这也是这两件参展文物所承载的重要思想内涵。
(贺婧婧:文物工作者;刘玉生:文物工作者、摄影人;丁禹:文物工作者)
文物背景:唐太宗贞观14年(西州640年),唐朝政府平高昌王国,设立安西都护府,从此,唐朝进入统治西域的历史时期,因此,西州时期,正是唐朝开始统一西域的重要标志。夸天的吐鲁番地区正是当时唐朝西州所辖高昌县。阿斯塔那古墓群正是以那个时期的墓葬为主的古墓群,位于今天的吐鲁番市东南40公里的阿斯塔那村北和哈拉和卓村东,此届世博会上展示的两件文物均出土于这个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