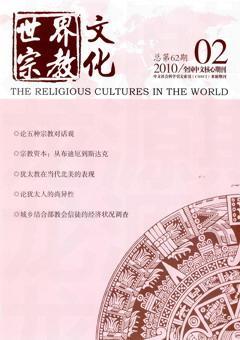宗教感与历史情怀:中西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及其思考
周建漳 王志华
内容提要:超越以死亡为标志的存在有限性及其所导致的整体生命意义的缺失是人类普遍深刻的内在冲动。在中西方文化中,超越性各自表现为典型的纵向一横向、外在一内在的神圣宗教与世俗历史方式。在形上意义上,人类个体存在有限性的关键时间,宗教与历史之为超越方式的要义则是以“永恒”或否定有限意义上的“无限绵延”为此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途径。历史情怀在超越性方面对宗教感的功能替代性可以为解释中国人宗教感淡薄及其历史观、家族观乃至生育观等文化现象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关键词:个体有限性的超越时间宗教感历史感超越方式
作者简介:周建漳,1954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志华,1978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08级博士生。
一、宗教与超越
人类存在有限性最直观亦最切身的表现就是死亡,西文中称凡人是“必死者”(mortal being),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最本己的能在”。人这样一种存在最终会不“在”的必然性是我们关于自身有限性最深刻的体验。“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它引发古往今来多少人的心灵震颤与慨叹。对人类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生物来说,对死亡的恐惧既属生物性本能,亦具有超生物本能的形上意义维度。死亡最深刻的悲剧性在于它将人置于意义空虚的深渊。
意义是非实体性的关系范畴,正如诺齐克(Robet Nozick)在《价值与意义》一文中所说,意义涉及将某一事物置于自身之外更大参照系中所获得的某种联系,因此,意义常与目的相联系。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关联通常表现为活动所追求的目的。在历史中,如丹图(Arthur Danto)所说的那样,人们“通过参照一个更大的时间性构造而将事件认作是有‘意义的,这些事件乃是这一结构的组成部分。”从叙述学的角度看,“追问某一事件的意义就是追问只能在某一故事的整个上下文中才能回答的问题。”故事总是有头有尾的,其中结尾至关重要,它令故事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有澄清前此种种曲折与晦暗不明之处的认知功能。意义预设了结构的完整性。以文本意义为例,任何文本都应该是有头有尾的,有头无尾的文本不能构成完整的意义单元,结尾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令文本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并且,结尾与开头之间还存在着内在因果乃至逻辑关联,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特定文本以融贯的意义。根据当代欧陆哲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结构主义、解释学、叙述学),人类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作为意义结构进而同样可以被视为文本。广义言之,无论是用墨写在纸上,还是以血汗写在生活里和历史中,这些实践活动都是“故事”,满足同样的意义成立条件。
在这一维度上反观死亡,未来的终结者令我们在生命中所追求的各种目的虚无化,从而导致人生作为一个整体意义的缺失。表面看来,人生是有首尾的,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由物理时间标示的始末,却非意义完足的有机构成的首尾。在意义层面上,毋宁说人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来自于‘尚未有的幽暗,又将回到‘不复存在的晦冥”。因而,人的一生实质上只是一个缺乏完整首尾的残缺“中段”。当我们在这样的层次上谈论人生意义问题,所涉及的不是人生中的意义(meanings inlife),而是人生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meaning of life)。维特根斯坦曾经说,“世界的意义必定是在世界之外”。同理,人生意义必在超越人生的层面上,人生的整体意义须在死亡中见之。
面对死亡,无神论者所持的态度往往是“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谓之命”,而各种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试图“了生死”。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伊斯兰教,都为人这样一种“必死者”许诺了永生(immortal)的希望,这也就是通过对神的信仰而得救的基本含义。不论这样的永生仅仅指的是“灵魂”之不朽,或者是灵肉合一的。作为“两个世界”的理论,宗教对人超越人世生命之上灵性生命(after death life)的肯定为原本残缺的人生续上了有意义的首尾,从而令整个人生成为首尾连贯、意义完足的有机整体。基督教《圣经》由《创世记》始到《启示录》终,佛教中所谓“前生”、“来世”的轮回观等都代表着人类在自身之外寻求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神圣救赎途径,其可能性则是由超越性神灵如上帝、佛陀的存在来保证的。在形上意义上,死亡所触及的人类困境的本质是时间,生命的有限性即存在时间的有限性,“今日脱鞋上床去,不知明日穿不穿”。死亡让明天不复存在,仿佛是在时间上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因此,“刹那生灭”和“一逝不返”成为人类关于时间的基本体验。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其实就是对时间的超越,而各种神圣存在如上帝、真主或佛陀以及“天国”和“西方极乐世界”均具有在时间之外(永恒、不坏)的特征。在此,永恒不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也不是时间在数轴上的无限大,而是在时间之外,是对时间的根本性超越。假如我们对此宗教的神圣存在具有信仰,那么,对死亡的超越就获得一个神圣的解决。暂且搁置信仰(或不信)不论,笔者强调宗教本质上具有超越现实政治、经济的文化意义,在根本上涉及生命超越这样非世俗性的形上问题。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宗教所提供的答案也许是虚幻的,但这并不妨碍其所触及问题的真实性与深度。因此,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将始终伴随人类,其对于人类存在处境和整体意义的言说,对于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不无启示作用。
二、历史之为内在超越
对自身存在有限性的超越,是内在于古今中外所有人类心灵的形上冲动,中国人亦不例外。但是,中国人在超越问题上所循的是不同于宗教的历史路径。正如一般所注意到的那样,中华民族似乎从来就缺乏深刻的宗教感。孔夫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确反映了中国人疏远神明的现世态度。并且笔者还注意到,在人类古老文明中,古希腊与印度这两个具有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对历史的意识是相当薄弱的。史学在西方尽管有着长期的传统,但一直到近代为止却始终不入学术殿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与中国具有同样长期不间断历史的印度文明并没有像中国这样诸如《二十四史》的丰富史学记载传统。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作为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民族则缺乏宗教感,这提示我们,宗教感与历史意识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替代性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宗教在西方文化中所承担的形上超越功能,是为不同于前者“外在超越”的“内在超越”。
众所周知,当今三大世界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无一原生于中国。考虑到人类早期神话思维的普遍性,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且体量庞大的文化体却没有像在其它古代文明中那样顺理成章地发展出自己的原始宗教,这显得尤为引人瞩目。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由道家思想演变而来的道教则以其明确的现世性与超越性尚有一间之隔。甚至在天主教及佛教等外来宗教传人中土之后,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仍然更多是现实功利性的而缺乏明确的超越倾向。中国的善男信女们有事到庙中求神问鬼与找官府中人求情的心理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以关系手段获得现实功利目的的达成,由此才
出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样的机会主义态度,与宗教教理从而超越追求了无干系。因此,中国人于各种宗教的态度亦颇为轻灵活泛,释道耶三教合流、并行不悖,这一在对宗教持虔诚态度者看来难以想象的事在中国则甚为常见。中国以儒家为首的主流文化传统与超越性宗教的疏离关系表现在思想层面,正如余英时所总结的:“中国思想家从来不看重灵魂不灭的观念……中国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肯定人生”。于此可见中国文化浓重的世俗人文性特征。
人们对中华民族超越性宗教情怀之淡薄有各种的理解与说法,其中常常被提到的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缺失、儒家思想的统治及祖先崇拜情结等因素。李泽厚指出:“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与特征”,而“中国的实用理性使人们较少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从幻想成仙到求神拜佛,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冯友兰先生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解释是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言之有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看法与其说是对中华文化缺乏宗教超越性维度做出理论的解释,不如说是对此现象本身的进一步阐发。因为,这些思想观念与宗教感的薄弱本身是同一层面上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互为说明,前者并未在更深层次上对后者的原因提供说明。本文要点则是试图在文化层面上依功能替代的思路对之提出理论解释。
超越生死之为“不朽”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理解。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其落脚点是“灵魂不朽”,其背景是现世与来世的圣凡二分。而中国文化的不朽观念明显具有现世人文主义色彩,其典型表达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春秋时鲁国叔孙豹所谓的“三不朽”,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三不朽”直接说来可以被概括为“精神不朽”,而其实质则是在时间中亦即在历史中不朽”。无论“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所追求的都是身后的“千秋万代名”,对身后之名的追求,正是古代中国人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的独特形式。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屈原的《离骚》讲:“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文天祥的名句把中国人的历史感与超越生死的关系表达得最为明快透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极端的形式上,对身后之名的追求甚至表现为如曹孟德那样不惮“遗臭万年”。当然,“三不朽”只是极少数圣贤进入历史(官修正史)的方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进入“先贤祠”或“凌烟阁”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不过,名列青史并非进入历史的唯一方式,在较低的层次上,民间地方史、野史乃至作为裨史的民间故事为更多的中国人提供了进入历史的另一途径,数量远较正史繁多的各种地方志、口述史,乃至牌坊、碑铭、口碑均属于历史记忆的范畴。如果说即使是地方史对一般人仍然门槛过高,那么,族谱与家谱为所有凡夫俗子都提供了进入历史最为普及的可能性,当然,其最低条件是不要让自己因各种言行进入“不肖子弟”的行列。就这样,从官修正史到地方史、族谱、家谱乃至各种野史、裨史的广义历史为国人的超越性历史情怀提供了覆盖式的服务。
如果说,广义历史在不同层次上构成中国人内在超越的文化方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国人生殖观念与行为因其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构成了个体生命超越的某种独特的“生物学方式”。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生殖行为兼有种族延续及个体“基因复制”的双重功能。作为前辈生物基因的携带者,某一个体的生物学信息通过子女在外貌、脾性甚至疾病各个方面获得复制和表征,父辈的生命从而在子女身上超越其自身寿限得到某种意义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人知识水平的限制,子女曾长期被认为只是男性(父系)基因的传承者,母亲(女性)被认为在其中只起辅助作用,因此,中国人在生育取向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重男轻女取向。这种在生育取向上的“重男轻女”与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歧视妇女有本质的区别,它不但受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其深处关于“传种”或“绝种”的文化考虑。除了生男或生女之外,生多或生少的意义在于其确保基因复制的牢靠性不同,一线单传跟拥有更多男性后裔比其基因遗传成功的概率明显变小。对于一般人来说,在显意识的层面上,支配一个人关于生儿或生女行为的也许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而在其潜意识中,关于生命传承的焦虑显然是更深沉的动机。由此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中对一个人最为严重的诅咒是“断子绝孙”,为什么普遍且始终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或“多子多福”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这些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显然是不存在或至少不典型的。必须指出,生儿育女行为在中国文化中兼有个体生命的生物学延续与历史记忆的双重意义,父辈不但在后辈身上实现生物学意义上的传承,并且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得传“香火”:有子孙的人死后有人祭奠,同时在家谱和族谱中可以始终保持记录,否则就成了令人同情亦遭人鄙视的“孤魂野鬼”。总之,不论是各种层次的历史或通过生命链条的延续,在广义上说都可归之为历史性的超越方式。由于前述历史的超越个体生命限度的时间性本质,它可以为个体的超越情怀提供真实的慰藉。
东西方文化由于复杂的原因在超越问题上取径不同,但是,不论是向上寄托于神圣存在,还是向外寄托于社会历史,其要义都是对个体存在有限性的超越,因而具有内在的文化可比性。在非宗教的世俗意义上,超越要求的实质可以被理解为以生物本能为基础,但最终超生物性的整体生命意义探求。由于其所实现的文化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两种超越方式间具有替代性关系,从而在东西方文化中宗教与历史两种超越路径各自成为文化的主流。这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体现了文化的某种“经济”法则。不过,二者在同一文化中亦未必是绝对互斥的。也就是说,对于信仰神圣救赎者,进入历史对其同样具有形上慰藉意义,而一个无神论者也未必不希望存在神圣救赎的可能性。当然,二者之间始终不是平等并列关系,东西方文化因此在宏观上呈现不同的主导性色彩与样貌。
三、几点探讨
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笔者围绕本文论题提出某些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首先,超越的本质在于时间,宗教与历史超越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个体存在时间有限性的超越。前者以永恒克服有限,后者则以无尽绵延对抗消逝,总之都是基于对时间的超越,进而在此基础上令有限人生在更大的“神圣时间”或“历史时间”框架内获得其意义的确立。就其相异性而论,神圣时间的本质是时间本身的消失即无时间性,它表现为刹那永恒即永恒的现在,而历史时间则是在对任何个体有限性的否定中呈现出来的无限延续,总之均具有超越时间的涵义。
其次,以上本文所讨论的外在性宗教超越方式与内在性历史性超越方式同时具有纵向超越与横向超越的不同意义。纵向超越是在人神之间两个相互垂直的层面上实现的,而横向超越则是在超出个体之外世间横向社会历史平面中展开的,二者的区别分别可以由指向天空的教堂尖顶、佛教高塔与大地上的坟墓两类不同的建筑物获得其象征。由此返观通常关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说法,如果将这里的“天”理解为自然界,固然似乎可以彰显其现代生态意义,但按照这种由今说古的说法表述出的中国文化的正面意义即使成立,也难免给人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何况,如果在这一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亦未必是天人分裂的。或者说,文明的本质必定包含一定程度的反自然倾向,与自然合一的是动物而非人类。退一步说,就算对“天人合一”作生态友好性的解读,这样的理念似乎并未引出实际上的生态友好效应。笔者同意李零从神人关系的宗教角度对“天人合一”命题的阐释,认为“天人合一”中的“天”和“地”照字面理解分别指的是神圣之天与凡俗之地。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或弱宗教性特征恰除是纵向维度上的“绝地天通”而非圣凡合一,倒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宗教文化因其内含的纵向超越维度而实际上是“天人合一”的。当然,在以儒家为主的主流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宗教不发达,或者说宗教没有像西方那样曾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潮流,但这与下层社会各种民间信仰及方术流行并行不悖。要言之,我们说中国主流传统缺乏宗教感,主要是指在儒家文化主导下民族心理中形上超越性的一面很弱,而实用性的方术却并不缺乏,但这仍然是出自于对待宗教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最后,宗教与作为显学的史学在中西文化传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对各自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启宗教之蒙的人文主义世俗化运动,中国启蒙面临的背景已然是宗教式微的人文主义传统,双方所面临的问题大不相同。因此,不存在相同的“路径依赖”,盲目对西方文化采取依葫芦画瓢的态度只能导致南辕北辙的效果。至于宗教式微对中国文化之利弊,长期以来人们之间存在着争议。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宏观文化历史现象,恐怕很难做出一边倒的利弊评价。笔者既不同意依简单的科学或迷信二分法处理问题,也不同意直接用某一现实指标如是否引发宗教战争为准谈论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认同因宗教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削弱世俗王权或有助于西人平等思想的形成等正面效用而主张通过引进宗教达成同样结果的主张。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宗教本身的存在,同时对其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具有的利弊影响有客观清醒的分析,从而在可能的情况下达成兴利除弊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