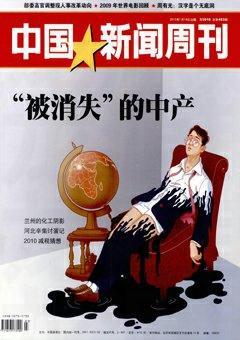兰州的化工阴影
王 婧


2009年1月7日,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303厂发生爆炸。如今看来,爆炸并未对周边的环境产生直接影响。但一个背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目前中国至少有2000家化工企业处在居民区包围中或者城市饮用水源的上游。一个常规性的化工事故稍处理不慎,就会被放大成对一个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
“砰”的一声巨响,正在厨房做饭的王帅被震得差点摔倒。他看了看时间,1月7日17时25分。“出事了!”他赶紧跑到楼顶看个究竟。在他家的西北角约1.5公里处,火光冲天,一朵黑色的蘑菇云腾腾升起,从蘑菇状慢慢散开成一大条黑带,再逐渐弥漫成一大片黑烟。
爆炸发生在与他们为邻的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简称兰化)303厂。厂区一个装有轻烃的储罐爆炸,并在瞬间引燃了周围另4个储罐。5分钟后,警笛大作,消防车、救护车呼啸而来。王帅专心地用手机拍爆炸的视频,约40分钟后,传来了第二声巨响,紧接着是第三声。
爆炸导致了6人死亡,22人受伤。17公里以外都有明显震感。不过根据随后甘肃省环保厅监测数据显示,现场没有有毒气体排出,爆炸未对兰州市的地表水造成任何污染,未引发流域水体污染次生事故。
占地27.84平方公里的兰州石化,总资产34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620亿元,每年贡献的税收占到了甘肃全省的10%以上。这样一个“巨无霸”的石化企业,历史上大小事故不断,幸运的是从未超标污染过黄河,历次事故在环境问题上均有惊无险。
但与其为邻的人们,却时刻有种“坐在原子弹上”的感觉。
当天,王帅下意识地拍下了环绕在他家周围的近百个大罐子。爆炸的那个属于303厂,即兰州石化橡胶厂。往西是兰州铝厂(现已停产),西南是兰化化肥厂,接着是兰化的大苯胺罐区群和14个大乙烯罐。往南是燃料罐和“毒品库”,村民不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传说是氢化钠。东边则是兰州市自来水公司,那里供给着兰州317万市民的生活用水。他的头顶还有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各种不同颜色不同粗细的管线和输水管道。这些管线密密匝匝的,让这里看上去像一个外星的城市。
这里是兰州市西固区桃源村。这里1100人居住在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的300米走廊中间,他们称这里是兰州石化的“厂中村”。
“共和国长子”
“厂中村”和兰州石化的界限,仅仅是一堵约3米高的土墙,上面还有一道约1米高的铁丝网。
这个模糊的界限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末。彼时,这堵墙从桃源村六社的孔家穿过,将孔家大院分成两半。大的一块被征用,留下一个小角落,供孔家居住。
桃源村六社原名“牟家堡”。据当地老人介绍,牟家是明清时期从天津迁过来的大户,至今仍保留着清代的一些小土房。
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中,有16个布局在甘肃。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偕同苏联专家来到兰州,确定将兰化建在兰州市西固区。在兰州市西固区一地,当时就规划了兰州炼油厂、兰州石油机器厂、炼油化工设备厂等6个“一五”重点建设项目及其配套工程。
孔家大院的地几乎是无偿地被计划给了兰州橡胶厂。“当时也没有什么补偿,给了点儿木料,让我们自己再盖房子。”
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村民们为这个被称作“共和国长子”的兰州石化能够在此落户而“深感骄傲”。
兰州随即成为新中国第一座石油化工工业城。在这里随后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桶“争气油”——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航空润滑油和重质燃料油。彻底打破了前苏联专家“用中国的原油绝不可能生产出特种润滑油”的断言,结束了中国用洋油的时代。
这样的历史,在今天仍被当地人津津乐道。
离不开的邻居
兰州石化来做邻居之后,孔家院子里仅剩的两棵苹果树结出的苹果越来越小,后来就干脆不结了。
在多位老村民的记忆中,兰州石化自建成至今始终事故不断,“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对于一些小的爆炸,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
上世纪80年代一次事故之后,下了场酸雨,一夜之间当地所有的蔬菜全黄了,而王帅家一个鱼池里所有的鱼,也全部翻了鱼肚。
村民们开始意识到,兰州石化在给他们带来骄傲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他们逐渐试着要求补偿。80年代末期,村民们开始向区政府反映情况。1989年,当地村民一夜转成“蓝印户口”,从此摆脱农民身份。彼时的“蓝印户口”,政府公开价是7000元一个,当地人算是沾了便宜。
但当年包产到户分到的土地却自此撂荒了。这些零星的土地散落于厂区周围,看上去都是肥沃的黑土,但往下一挖,全是贫瘠的黄土,上面的一层黑色,是多年累积的煤灰。在这里种的菜,逐渐卖不出好价钱,到最后除了他们自己敢吃,别人一听是西固区的菜,都不敢买。
务农的人越来越少。上世纪90年代初,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兰州石化开始有意识地吸收当地劳动力入厂。当时“厂中村”共有居民500余人,兰化至少给每户人家解决了一个人的工作。“自此每家每户都与兰州石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进入兰州石化工作的人,如今每月能拿到2000~5000元不等的薪水,从而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围绕着这个有3.7万人的“巨无霸”企业,“厂中村”的人们“靠山吃山”。厂区周边的小饭馆,多是村民开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人满为患。附近的废品收购是个好生意,爆炸之后的这几天,有人因为捡被炸飞的铁皮,就小赚了一笔。
这些年与化工厂相伴的村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为了半个化学家。他们知道哪个罐子最危险,“氢化钠是剧毒,闻到就会死”;他们会辨别各种气味,苦杏仁的是硝基苯,臭鸡蛋的是含硫物,甜的是芳香烃,他们还懂得从火炬塔来判断厂里的生产情况。火炬塔熄灭了,说明停产了,火炬塔冒黑烟,说明加大了生产了……
而让当地居民最惊悸的是,只要一出事故,就需要对那些错综复杂的管道进行“吹扫”。
吹扫意味着将会产生很多化学废料,对周边的环境造成直接污染。
管道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即使只相隔两米,两个人说话都听不清。这样的“吹扫”甚至有可能持续近一个星期。王帅称,一到“吹扫”,他就需要服用神经类药物,才能勉强维持睡眠。
此外,2006年,兰州石化在夜间检查管道设备时并未及时通知当地村民,导致有村民夜间出行被伽马射线误伤。为此,兰州石化还给过该村民24000元的补偿。
在1月7日的这次爆炸中,巨大的冲击波扫过厂中村后,即使是当地最为高档的小区,也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不仅如此,连铝合金的门框都变了形,水泥墙上裂开了好几条缝,天花板上直接震出了大窟窿。一些房子直接成为危房,还有居民被震落的玻璃砸伤。
当地政府官员出面安抚居民,保证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出这样的事故了。“但这样的话我们听了几十年了,当下一次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周围居民们都说。
与险为邻
最初,搬迁并不是居民们主动提出的要求。在2005年吉林石化苯胺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时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对107个石化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排查,在一项涉及兰州石化的项目中特别提到,要求对周围20余户居民进行搬迁。
而搬迁最终没有实现。当地的居民称,“我们从明清时代开始就住在这里,怎么能说我们是违章建筑,而且不给补偿地就让我们搬迁。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兰州石化还没有呢!”
如今,居民希望借助这一次爆炸的巨大威力,彻底把搬迁问题也解决了。但如何安置居民,也许尚不是政府当下最关注的事情。让政府最焦虑的是爆炸是否会对环境造成直接的污染。
一个无法回避的前车之鉴是2005年吉林石化苯胺爆炸,造成了松花江污染。此事件直接导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引咎辞职。兰州石化位于黄河岸边,所处环境与吉林石化相似,并且同样拥有7万吨的苯胺生产装置。若对黄河有污染,影响的将是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爆炸发生后,甘肃省环保厅派了两辆应急监测车赶赴现场,对空气和消防水的流量进行监测。测数据显示,现场无有毒气体排出,未引发流域水体污染次生事故。
当天晚上8点20分,兰州市政府发了一百万条短信告知市民此次事故未造成环境污染,以免发生大规模的恐慌。在2006年兰州石化发生爆炸事故之后,该市居民曾因害怕水源遭到污染,疯狂储水。
整个兰州市的生活饮用水的水源就在西固区的桃源村。兰州市自来水公司始建于1955年,当时铺设了两条输水自流沟。它们都从兰州石化的“厂中村”经过,后来兰州市政府还在此立碑,“兰州市城市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这成了此后埋在兰州人心中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但凡西固城有个风吹草动,整个兰州城的市民都是神经紧张。
在城市上游建设化工厂的例子在中国为数不少。比如重庆的长陵化工,1998年曾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剧毒氯化钡泄漏到长江。2004年4月重庆江北区的重庆天原化工厂氯气罐大爆炸并未被有效阻止,氯气飘散导致了当地15万市民紧急大转移。
解决这些重工业企业的长期污染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搬迁。但要搬迁类似于兰化这样的庞然大物,所需资金必然是个天文数字。
目前中国至少有2000家化工企业处在居民区包围中或者城市饮用水源的上游。一个常规性的化工事故稍处理不慎,就会放大为对一个城市安全的威胁。
而对于兰州而言,当地政府尚无“壮士断腕”的勇气。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张明泉教授称,在10年前环保专家就提出过将兰化等企业整体搬迁的方案,“但大型企业的搬迁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常困难,目前这个方案依然搁浅。”
“厂中村”的村民们并不关心这种布局是不是合理。一方面他们仍然以与“共和国长子”为邻而骄傲,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也是一种奉献。在当下,生命安全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不奢望兰州石化能够搬走,“他们不走,我们走,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