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非主流”画者
杨 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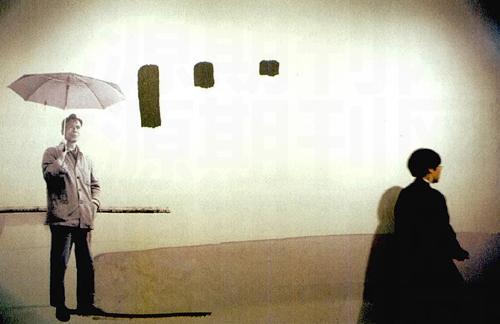
艺术何为?——祭画者吴冠中
他的一生独钟艺术这一件事,除此无任何爱好。他视画画的形式之美高于一切。然而在“内容决定形式”“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单纯地画画”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在与体制和政治环境无奈的纠缠中,他执拗而孤独地遵守着内心的“艺术之美”
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北京蒲黄榆地铁站门口有一片极为嘈杂的路段,小贩把仿制的LV包挤满便道,荒腔走板的歌手在为商场开业吆喝,穿过这段满是果皮和痰迹的街道,向左一转,是一片建于2000年左右的小区,楼房外墙斑驳,没有保安更无须登记。走进去,凉面摊子前坐满喝啤酒的房产中介,有老人在楼下遛狗,问他们,“知道吴冠中住在这吗?”他们回答说,“哦,那个画画的,死了吧?以前看他有时候在这溜达,总有来录像的。”
这是6月26日傍晚,小区一如既往的平静。居民们从报纸上知道,前一天深夜,自己的邻居吴冠中去世,在悼念的报道中,他被称为“大师”。
难以融入主流的法国留学生
走进楼内,楼道狭窄,电梯逼仄,只能勉强容下五人。吴冠中家门紧闭,屋内安静。他的大儿子开门问明记者来意,颇有些为难,“我母亲身体不好,她还不知道。”客厅墙壁上挂了一张吴冠中的黑白照片,前面有些鲜花。
吴冠中的夫人在卧室问,“谁来了?”儿子们就走进去说,“有人来照相,没事。”把老人再哄回屋内。这位陪伴吴冠中走完一生的老人,因脑血栓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到此时,她仍以为老伴还住在医院。
逝者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发出讣告,称吴冠中为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并提及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以及政协常委的头衔。这是“组织”对于吴冠中的盖棺定论,但六十年前,吴冠中回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与这位画家之间似乎一直缺乏润滑。
1950年,经过多日考虑,公费赴法留学已4年的吴冠中决定回国。那年他31岁。对于新政权,吴冠中和其他留学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向往中混杂着恐惧。
经香港回到老家宜兴不几日,吴冠中就急忙奔赴北京。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设在西单旧刑部街,这是为留学生联系工作的部门,也是吴冠中进入新体制的第一个必经站。首次到京的吴冠中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故宫和红墙,也看到了“行人如蚁,一律青灰衣衫。”他感觉自己的西装革履残留着太多法兰西的气味。报到完毕,他直接去往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布制服,换下西装,“才可自在地进入人群。”这个微小的细节成为了某种预兆,从此,吴冠中开始努力与体制磨合,但始终不得要领。
最初,吴冠中本想投奔当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刘开渠,回到杭州母校任教,但在北京友人家中意外碰到同学董希文,两人叙旧的第二天,董希文挑选了几张吴冠中所作人体油画带走。十天后,董希文将画还回,并告诉吴冠中,“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同意聘用你。”
彼时,央美由徐悲鸿主持,因其一味主张写实,所以与杭州系学生水火不容,而吴冠中自法国时便看重绘画形式美,他问董希文,“徐悲鸿怎能容纳我的观点与作风?”董回答,“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吴冠中于是答应入职央美,但他并不知道董希文此话的意义,也更不了解,自己受聘还需党委通过。
吴冠中全家来到北京,租住了两间平房。他教一年级某班素描,如今的美协官员靳尚谊、詹建俊等人都在这个年级。和吴冠中预想的一样,学生们忠于理性写实,他在课上开始鼓励差异,启发个性。但这一套并不为所有学生接受。那时,新政权刚刚建立,文化艺术被当作稳定政权的工具和武器,连环画、宣传画是美术的重头,苏联式的写实为正路,而强调形式美则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学生们将苏联的列宾奉为偶像的时代,吴冠中坚持在课堂上向同学展示现代主义的画册。
与吴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评家贾方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客观地讲,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不入主流的吴冠中经常做出一些自己事后都认为“荒谬”的举动,比如,他喜爱自己班上一位极有灵性的学生,但那位学生积极参军,吴冠中十分惋惜,还劝阻其不要去。事后他回忆说,“这样的教师早晚要被赶出课堂。”
“逼上梁山”画风景
吴冠中并没有被真的赶出课堂,但他很快就以另外的方式见识了课堂以外的政治。新政权决定规训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冠中被编入高校教师土改参观团。
在湖南,他终于亲见了阶级斗争的阵势。有与他同去的画家很快画出了表现“土改”的作品,吴冠中也开始努力向组织的要求靠拢,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一位很入画的北方农民,将其请到家中作为模特,画中,他为农民画了大红花,还让一个孩子趴在其肩头。他还给作品起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名字《爸爸的胸花》,以此来描述土改后农村参军的景象。但是这幅作品仍被定性为强调形式,多次修改均不合格。自此以后,吴冠中逐渐萌发了画风景的念头。
“像一棵树,长的时候有石头压着,就从另外一个缝里钻出来。”批评家贾方舟这样描述吴冠中转画风景的原因。多年之后,吴冠中自己称改画风景为“逼上梁山”。
吴冠中在央美前后只工作了两年。第二年初始,文艺界整风日盛,对于美术界讲究形式美的“形式主义”被坚定地上纲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在一次全院教师大会上,院长徐悲鸿发言,“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吴冠中也明白自己在中央美院恐不会长久。
果然,不久之后,央美人事科长致电吴冠中,要其办理调职手续,清华大学建筑系决定聘用吴冠中任教。这是吴冠中第一次调动工作,也从此开始频频转换单位。
油画专业出身的吴冠中,一心想将西方油画的神髓传授学生,却不得不为建筑系学生教水彩。艺术上的不得志却让他在政治上觉得轻松。多年之后,他回忆央美的日子,将其称为“擂台和左的比武场”。
清华建筑系的工作相对轻松,吴冠中开始有闲暇探索风景画创作。50年代,风景画因无法为政治服务而极不入流,但因周扬一句“风景画有益无害”,而让吴冠中看到了政治上的安全地带。彼时,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时瞄着政治的眼色,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建筑史第一堂课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掏出一个小红本,向大家声明“这是我的工会会员证,我是工人阶级了。”而吴冠中正坐在下面旁听。
清华大学的工作不及三年,吴冠中再次面临工作变动。那时他仍然想回到真正的艺术圈,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图画制图系准备改为美术系,需要聘请专业教师。其系主任卫天霖的艺术主张被认为属资产阶级印象派,也因此卫天霖对吴冠中十分赏识,力邀其加盟。不久,美术系与音乐系独立出来合并成为北京艺术学院,卫天霖成为主管美术的副院长。
受到赏识的吴冠中将此次调动视为难得的机会。他再次将中央美院时期批判过的美术理论搬上课堂,给班里学生偷偷看西方画册,开讲形式美。同时,他也一直为自己的风景画寻找出路。
经过思考之后,吴冠中决定到井冈山写生。井冈山已成革命圣地,到此处写生既能满足自我喜好又有向革命靠拢的借口。而这样的中间路径确有成效。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一套井冈山和瑞金写生的明信片。自此,吴冠中的风景画创作逐渐受到关注。西藏叛乱平定后,美协组织画家入藏写生,经董希文推荐,吴冠中也一同参与,并创作了《扎什伦布寺》。“1961年《美术》杂志发表了那幅画,现在看应该算他最早的代表作,奠定了文革前他的基础,那一期杂志同时发了吴冠中谈风景画的文章,他从此扬名。”评论家贾方舟说。
“谁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
吴冠中在北京艺术学院稳定工作了8年时间。直到1964年,文化部决定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基础上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其他科系拆散打入其他高校。吴冠中因此被转到了中央工艺美院。
“张仃很器重吴冠中,点名把他要来的。”吴冠中的好友,画家乔十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彼时,张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但多年以后,张仃与吴冠中两位老友因艺术观点不同也曾一度交恶。
1964年,乔十光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吴冠中也同时调入学校。乔小吴冠中19岁,很快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吴冠中生前出席的最后一个社会活动就是乔十光的个展。
客观地讲,调任工艺美院的吴冠中再一次离开真正意义上的美术界。工艺美院的主修是装潢和设计,吴冠中只任教基础课程。但因为该校以设计为主业,对于形式美的探索也相对宽松很多。“他私下总会和我说起来形式美的事。他说,艺术家不谈形式,就是不务正业。”乔十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但吴冠中因此前患上了严重的肝炎,无法参加政治运动。也由于此,他在自传中自豪地写道,“在我的历史上决无政治污点”。
“他其实有他的幸运。文革的时候,艺术学院解散,到了新的单位,就溜过去了。”批评家贾方舟说。他曾经教过的北京艺术学院学生早已各奔东西,不可能到新单位对他进行批斗,而他本人的名声又局限于绘画界,之于以设计为主的工艺美院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逃过一劫。文革中最大的劫难无非是和同事一起到河北农村劳动,养鸭子时被人污蔑“殴打一只鸭子致死” 。
而对于吴冠中来说,更为深刻的苦难是无法画画。
“跟他就只能聊艺术,他没有任何一点别的爱好。”贾方舟说。晚年的吴冠中甚至拒绝过年,去年大年初二,吴冠中一早就来到乔十光家,两人一起躲在工作室画了一天画。“他到晚年对生死、人事看得很透,总有点凄凉的感觉。他很少出席活动,怕见人,怕说那些套话。他总觉得很多人之间都只是勾心斗角。”乔十光回忆着与吴冠中最后的交往。
对于这样的性格,无法画画似乎是最重的刑罚。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气氛突然松懈下来,吴冠中开始能够背着粪筐到田地里写生。
1978年,在逐渐回归正常的气氛中,吴冠中再次发言,他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解放美术领域的奴才”,并于第二年,在《美术》杂志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引发激烈讨论。1979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份,一边美术界极左的惯性仍在,另一边已经出现“星星画会”这样争取话语自由的民间活动。此时,吴冠中的发言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旧思潮对撞的引信。虽然再次遭到批判,但毕竟政治运动的大势已去,吴冠中当年被选为美协常务理事。这似乎是体制内对其认可的一个标志。
“1979年到1984年是吴冠中最辉煌的一段。”贾方舟对记者说,“他是憋了三十年,不得不说了。”
1985年的“八五美术新潮”运动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更年轻的一辈艺术家身上,吴冠中被这群热衷“后现代”哲学的艺术家所忽略。直到两年后,他的作品以超过百万元的高价成交,再次被捧为明星。
进入晚年,被体制和市场都视若珍宝的吴冠中却对双方都表现得深恶痛绝。他曾多次炮轰“美协”和“画院”的僵化体制,甚至将过热的艺术市场比作“妓院”。他曾对贾方舟说起,“我现在就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而半个世纪前,他回国后的梦想是“能像唐僧一样,安静地译经”。他的一生似乎像一个无法咬合的齿轮,始终与时代、与政治、与体制、与内心磕磕绊绊。
2007年,贾方舟为吴冠中在798策划了一次个展,让许久消失于人视线的吴冠中再次成为新闻话题。实际上,在此之前,吴冠中自己曾偷偷考察过宋庄画家村和798。此时,他已经将近九十,向故宫、中国美术馆等捐赠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而自己仍居住在简单的两居室单元内,三个儿子无一人学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