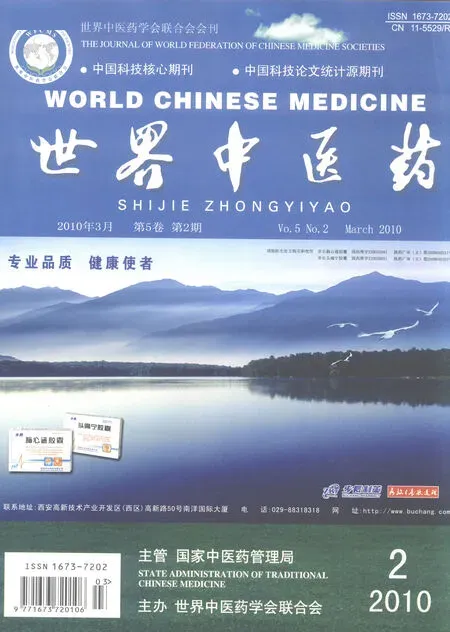张云鹏学术思想介绍
杨悦娅 周 晴 徐燎宇 余恒先 郑宜南 邵明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上海市瑞金二路 156号,200020)
“张云鹏临床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课题之一。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立项计划和要求,我们系统整理总结了张云鹏的临证经验、思辨特点并加以提炼。现介绍如下。
1 崇尚仲景学说 领悟辨治精髓
张云鹏教授从事中医临床和研究近半个世纪,逐步形成以仲景学说为经,诸家论述为纬,兼收并蓄,融合汇通,坚持发展,重在实效的学术思想。先生精通伤寒,崇尚仲景学说。
1.1 整体观念是《伤寒论》的基本精神 《伤寒论》六经分证,是在《内经》阴阳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具体内容上,涉及到经络、气化、部位、脏腑等理论。《伤寒论》六经,是正邪 、病性、病势、病机、病位等的总和,是从具体病象中归纳概括出来的综合性证候类型,是从整体出发的比较全面的辨证论治的学说。仲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重视病者的体质,如酒客、喘家等,及其疾病的复杂变化,若属坏病均有启发性的提示。
1.2 辨证准确是《伤寒论》的精髓所在 《伤寒论》在各篇论证中,为了明辨疑似,鉴别清晰,从主客关系论辨证,条文之间,有主有客,主客的关系,也就是辨证的关系。太阳病篇,既有白虎汤,又有四逆汤,阳明病篇有四逆汤,少阴病篇有四逆散,都是为了辨证。当然,证候分析,是一个很重要的辨证。《伤寒论》六经分证的核心是对证候的辨别,如分寒热、察汗出、审口味、辨下利、析厥证。
《伤寒论》的论脉法,主要精神是“凭证辨脉”“以脉合证”。先生简言有以下数端:1)凭证辨脉。论中大多数是先详言症状,然后再谈脉法,再次讲到方药。2)从证舍脉。凡疾病轻浅的,大多数脉证相合,疾病深重的,往往脉证不符,治疗则衡量机宜,以症状为主体。3)从脉舍证。病机以整体为主,脉象的变化是正气盛衰、心脏强弱的标志之一,所以有从脉舍证的情况。4)凭脉审机。脉象是审辨疾病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一种诊断方法,它阐明病机,提示预后。
1.3 论治严密是《伤寒论》的关键之道 《伤寒论》从整体出发,既原则又灵活,既果断又谨慎,方药组成严格周密,先生概括为以下几点:1)治病必求其本。2)总的因势利导。3)治有先后缓急:里实有表,先表后里;表证为急,先表后里;里虚有表,先里后表;里虚为急,先里后表;表里同病,表里同治;表里错杂,审证处治。4)果断与谨慎相结合:仲景在立方用药上,既胆大又心细,既果断又谨慎,能巧妙地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他在治疗学上的又一特色。5)组方严格而周密:《伤寒论》收载方剂只有 113方(内缺禹余粮方),应用药物,仅有 82种,但组方严格而周密,配伍有一定的法度,加一味药,减一味药,都有明确的指征,井然有序,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 六经提纲是《伤寒论》的辨证要领 《伤寒论》是以六经辨证为核心,各经均有提纲挈领的条文,作为辨证论治的要领,在六经分证中具有指导的意义。正如徐灵胎所说:“仲景六经各有提纲一条,犹大将建旗鼓,使人知所向,故必择本经至当之脉证标之,学者须从其提纲以审病之所在。”因此,有必要逐条深入进行研究。
1.5 合病并病是《伤寒论》的常中之变 《伤寒论》的六经分证,每经都有它的主证主脉,井然不乱。但是病情变化,有时也不会这样机械固定,相反,往往出现错综复杂的证情,不能单纯地用六经来归纳、表述。仲景在六经辨证外,复提出合病、并病之病,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合病、并病与六经主证的关系,先生认为可以把六经主证视为纲、为经、为常,合病、并病是目、是络、是变。六经主证与合病、并病,经纬纲络,纵横交错,知常达变,揭示了疾病本来的复杂面目,给《伤寒论》辨证施治提供了依据。
1.6 汤证对比是《伤寒论》的临床鉴别。《伤寒论》将辨证论治法则融于理法方药中,组方严格而周密,用药精炼而灵活,被后世医家视为处方的规范,称为“经方之祖”。先生用经方,活泼而非生搬硬套,可谓深得立方之义,方论之理,变而为用。如善用小柴胡汤,并不局限于《伤寒论》列举小柴胡诸症,而是根据其病理机制抓住病在少阳之契,凡有少阳经之病证,辨证切实,均可用之。有一患者,耳鸣如蝉,低热有时,众医皆从肾阴不足而补其真阴之水,然终不解其苦。求诊于先生,师用小柴胡加减,7剂而效。小柴胡证条中虽未列耳鸣一症,但在 265条中言“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可见耳为肝胆经所过之处,少阳症可有两耳无所闻,则耳鸣也当推之应为或有之症。加之患者潮热阵作,自觉定时发热,心烦,也符合往来寒热,心烦之少阳柴胡汤主症。故用是方则有是效,是理所之应也。”真是领师一席话,胜读 3年书。
2 重视系统观念 主张多元辨证
张云鹏教授非常重视系统科学的发展及其与中医学理论的相关性。认为:系统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整体性”“巨系统”“母系统”“子系统”“多层次观念”“加和性与非加和性”“综合性原则”等,在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天人相应”“三因论”“脏象论”“元气学说”“辨证论治”等中,几乎都可以找到某种原始思想。中医把人、病、证,视为一个整体,把人体与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把疾病看作病因作用于人体的整体反应。这些都包含了系统论的等级秩序原则。
先生从系统观念出发主张多元辨证,提出从多层次、多侧面、多因素、多变量、多方位考虑疾病的始因与变化,运用系统观念的“关系”,辨人、辨时、辨地、辨病位、辨病因、辨病态、辨病机等。对疾病的认识不但要看到现在症状,还要了解过去症状,同时要预测未来的症状。医者,必须整体出发,全面审察,统筹考虑,优化选择,不能执一而论,失之偏颇。在多项式的辨证过程中,必然运用综合调节原则。疾病是复杂多变的,证候的显现有真象也有假象,故有“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理论。还有,在治症、治病、治人上,何者为先,何者为急,都必须在系统整体观念上,采用综合的原则去认识疾病、分析疾病、处理疾病。
先生曾治风湿性心脏病伴心肾衰竭,见全身浮肿,心悸气促,腹胀难忍,不能平卧,小便五日不利,舌质暗红,苔少,脉沉细而散。中医辨证心肾阳虚,水湿泛滥,气机升降失常,脉络瘀阻,阳气欲绝。属绝病类的心绝、肾绝。急予扶正与祛邪相兼,理气与化瘀并举,药用附子、肉桂、葶苈子、黑丑、白丑、茯苓、木香、丹参等药综合调节,挽生命于顷刻。药后患者解出小便 200~300mL,效不更法,后水肿退,脱离危险出院。
总之先生对疑难杂病尤宗综合调节,从本施治的方法。
3 阐发毒邪之源,倡立解毒为先
先生在逾半个世纪的临床实践中,建立了“毒损肝络”之说,倡导“解毒为先”的治疗大法。主张:去邪为先,开拓邪路,给邪毒气以出路。金◦张子和有:“先论攻其邪,邪去而正气自复也”。先生对此发挥有加,认为不论是侵入机体的湿毒、热毒、疫毒、酒毒、药毒,还是由内而生的痰毒、瘀毒、秽毒、浊毒,都会影响脏腑经路机能失调,若时肝络损伤尚轻,即“亢害承制”在发挥着调节,随着湿毒、热毒、疫毒、酒毒、药毒聚而不解,可进一步产生痰瘀秽浊等病理产物,此时若不及时解毒清源,邪气存留体内,则会加重肝络损伤。气滞血瘀,瘀血内阻,壅遏络道,毒瘀痰阻,肝络癥积,病势深重,久则难愈矣。故主张去邪清源为先,抓主要矛盾,整体辨证,先取主证,挫其病势,断邪之路,截断扭转。只有祛除邪毒,才能恢复脏腑功能。在辨证用药上,无论新病实证或宿病新发,只要辨证确切,则果断重剂,祛邪为主。他常教导门人,病有新旧,证有主次,无论沉疴还是暴疾,只要辨得证谛即要果断用药,应重则重,直取主症,主症解决,病科转大半矣。
对于去邪清源,张师善用攻下法,曾与理气开结法合用治疗肠梗阻;与化痰降脂法并用治疗脂肪肝;与利湿逐水法合用治疗肝硬化腹水等均有显效。对于黄疸,也善与清热利湿之法配合,以攻下通腑,利胆退黄。对于湿热郁蒸、热毒内盛之黄疸,有助于衰其邪盛之势,清其湿热之蕴结,疏通胆腑而退其黄疸。
4 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的理论与实践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各自不同的功能在生理上即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如一旦外感六淫之邪,上受时行疫疠,或内伤七情郁结或气化功能障碍,产生痰、饮、水、湿、浊、瘀等病理产物(也可称为内毒之邪),导致脏腑、三焦、气血、经络功能失调,则疾病应变而生。取决于疾病是逐渐向愈,还是日趋严重,其中的关键所在,是人体的邪正态势。医者要能洞察这种态势的变化,正确掌握驱邪与扶正的关系。先生正是善于从众多的症状中抓住要领,分清邪正盛衰,主次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正确观察疾病邪正的走势,不失时机地运用有效的攻与补,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
先生对攻下驱邪法临床应用颇有经验,归纳有清热攻下法、开窍攻下法、理气攻下法、活血攻下法、凉血攻下法、化痰攻下法、逐水攻下法、解毒攻下法、泻肺攻下法、利胆攻下法、温阳攻下法等十一法。大凡温病、温疫多为时行疫毒、温热、湿浊,或痰瘀互阻,或脏腑壅塞,先期亟予驱邪,遵循吴又可“急症急攻”的主张,大胆地采取“数日之法,一日行之”的紧急措施。“驱邪为先”“先治其实”,并不意味着不要扶正。如治一位肺炎患者,先予麻杏石甘汤治疗,患者服药后症状有好转,但发现患者面色苍白,汗出较多,脉细无力,表现为阳气不足。先生认为:此患者有邪实的一面,但不能忽视阳气虚的另一面。故采用麻杏石甘汤中加入附子治疗,果然药到病除。
5 研析疫病共性 提出证治通则
先生学宗仲景,旁及诸家,既悟经方之旨,也集时方之长。对汉唐以后的各家学说,善于吸收,研究各家学说不先存成见,而是独立思考,临床验证,为我所用。先生治咳喘,寒者从《伤寒论》选用小青龙汤,热者从《景岳全书》选用桑白皮汤,不囿一家之见。
先生也熟悉叶天士的温病学说,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推敲总结,如治疗昏迷、谵语患者,既遵《伤寒论》阳明腑实症以攻下通腑,又从温病逆传心包理论,配以芳香开窍之药;又如治邪热壅肺,既用麻杏石甘汤清泄肺热,也加用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从而提出“伤寒温病统一溶化论”,创热病分期分类的辨证纲要。
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席卷大江南北之际,先生被邀参加并成为“上海市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中医专家咨询组”和“上海市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中医药科研协作组”专家成员,亲临一线,给患者辨证处方。2005年东南亚个别国家出现禽流感,上海邻近省又发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先生反复思考“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从现代医学病原学的角度,其各有不同,但从中医角度,则统称为“疫病”。因此可从证候学研究出发,探讨疾病的属性、病位、传变,进行辨证论治。这些疫病的发生发展,先生遵循“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精神,应用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的方法,明确疫病、疠气所包括的热、毒、湿的共性,依据疫病的传变规律及预后,提出“中医疫病证治通则”,这是先生从事热病研究的延续。
如今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但从不满足已学,而是不断学习一切时代新知,为临床所用。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不存门户之见。主张中西医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