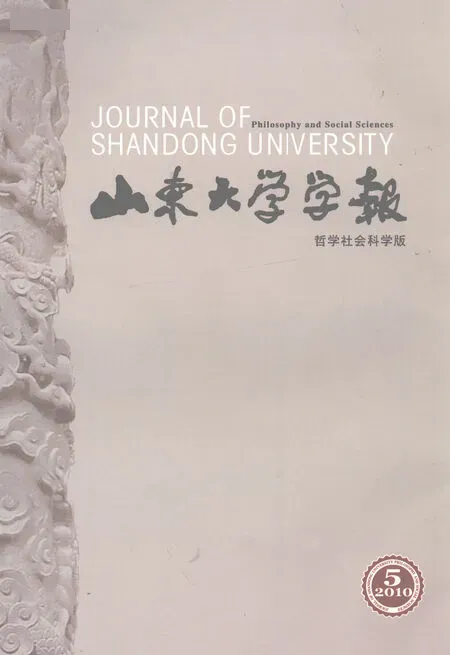论女性创作的地缘情结
张 岚
论女性创作的地缘情结
张 岚
女性作家与地域文化有着天然的脐带关系,积淀着浓厚的地缘情结。与男性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不同,女作家的地缘情结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这些具有性别特征的地域文化创作在使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苦难和压抑的同时,又对女性创作的纤小、琐细和庸俗化起到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时,女性创作的“地域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女作家在表现地域文化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而应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超越地域的局限达到与人类精神的共通。
女性创作; 地缘情结; 地域性超越
文学作品中的“地缘情结”是作家对故土或长期生活过的居住地的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这一情结之“根”是地域文化及其与作家个性气质的复合体。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人们活动与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物产等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影响下的行为方式、审美爱好、价值观念等等。它是中华文化的多样绽放,更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得以薪火传承、多元互补、综合创新的内驱力,它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地理和心理的依托。由于大地是人类的母体,它以母性的博大、宽厚、不计得失、不求回报地承载养育了难以数计的芸芸子民,所以大地与女性有着天然的象征关系;加上女性的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较大,因此女性创作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更多更深。但是以往的评论和研究对作家创作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论述并不鲜见,但专注于女性文学与地域文化独特关系的却几乎没有。本文旨在通过现当代女性创作地缘情结的剖析,对这方面的缺欠略作弥补,并期望借助这一视角拓宽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为女性文学的本土化研究略尽微薄之力。
一、女性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气候环境复杂,民俗风情迥异,由此可划分成许多不同的文化区域,而每个区域又都有着各具特征的文化形态。东方的“海洋文化”和西部的“高原文化”自然不同,北方的“大漠孤烟”和南方的“杏花春雨”也风情迥异:“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①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下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626页。由于地域不同,民风不同,文风也有差异:“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②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73页。不仅区域不同造成文风不同,而且男女两性作家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也不尽相同。女作家们在各自的文化空间,用既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柔性化文化符号,又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个性化、地域化文化符号创作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
第一,女性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表现在对现实文化地域的外部描摹上。女作家们往往将特定的某一区域文化作为作品的外部物质环境或某种叙事载体,传达她们对本地域文化或赞赏或怀念的审美感情。在具体描述上,女性作家一般比男作家观察更为细腻,描述更为精致。萧红笔下那天寒地冻寂寞的“呼兰河”小城和绚烂多姿的“火烧云”,迟子建笔下壮观的冰排和令人兴奋的鱼汛,都寄托了她们对东北故土的热爱和怀念;张爱玲、苏青、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十里洋场”气息,方方、池莉小说中武汉“九省通衢”的喧哗,范小青笔下温婉甜腻的苏州小巷故事,都无不充溢着女作家对本地域传统文化的依恋。有时候这种依恋显得毫无理由,如同对文物的观赏和收藏,但是从她们丰厚的地域风情的客观描述中,读者所得到的是“异域情调”的审美满足,在地域特征的对比中形成的审美落差造成了地域文化外在客观性表现的审美效应。
第二,女性创作地域文化特征还表现在特定地域内人们的精神内质上。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外在地域风貌的客观描绘而不能揭示丰富的精神内涵,那无疑等同于“风物志”和“地方志”,它不是文学作品描摹地域特征的目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一种历史文化地理风貌的描绘其实都代表着某一“类”生活或体现着一“类”人的精神特征,影响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王安忆在《“上海味”和“北京味”》中这样形象地描述过:“可称作‘文化’的那种东西”,体现着一个地方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它“决不仅仅是指将‘太阳’说成‘老阳儿’;将‘你’说成‘侬’;将‘他’说成‘伊’;将‘玩’说成‘找乐子’或者‘白相’;将缺心眼儿说成‘二百五’或者‘十三点’”。*王安忆:《“上海味”和“北京味”》,见《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之四·散文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89页。所以,对地域文学作家而言,不仅仅要写出一个地方的外在风貌特色及当地奇异独特的风俗习惯、方言俗语,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开掘特定的地域人心,写出构成时代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的性格、精神和灵魂,思考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人精神的影响。黄旭峰的《茶人三部曲》就是浓郁茶文化精神与吴越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的小说。作者将吴越茶文化融进人物命运的演进之中,糅合在人物性格内,以茶的品行喻人物精神,如儒商杭天醉既有茶文化中坚韧、冲淡、平和、仁爱的一面,也有茶人身上颓废、羸弱、阴暗的一面,成为茶文化精神与西子湖飘逸灵秀的柔美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诠释。王安忆的《流逝》、《好婆与李同志》、《“文革”轶事》、《长恨歌》等更在对上海市民习俗的细致描绘中揭示了沪上人家舒适、优雅、细腻与精明、实惠、浮华结合的市民意识。同样,由于武汉地处“九省通衢”的独特地理位置,那里的民风就呈现出驳杂的色彩。北方的粗犷和南方的精明融汇成武汉人的亦刚亦柔、亦粗鲁亦幽默的民魂。方方的《风景》、《落日》,池莉的《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等熔夸张、想象、粗俗、幽默于一炉,表现了武汉市民大喜大悲的浮躁性格,跃动着武汉民间鲜活泼辣的生命活力,蕴含着化人生烦恼为风趣油滑的生活态度,以及大冷大热天气磨练出来的武汉人的坚强神经。这些对杭州、上海、武汉等不同地域人们生活方式、民风习俗和市民性格的描绘,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城市之魂的所在。那是一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它不因战火、天灾而寂灭,也不会因“新潮”的追逐而消失,它体现了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内群体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其间的人类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地理环境等外在条件和民俗民风等内在传承,除构成女作家特定的话语体系,影响作品人物的精神气质外,它们还是创作主体生生不息的精神栖息之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地域女作家的人格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精神特征和文化品格,由此也影响了她们的创作风格(当然,同一地域的作家由于创作主体个性的不同,创作风格也不尽相同)。残雪作品那神秘、奇丽、狂放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荆楚文化的哺育。荆楚之地,居两湖一带,自古是一片水乡泽国。浩渺的水乡滋养了楚人敏锐的感觉,丰富的感情又孕育了浪漫的民风。而楚人信巫,好幻想,善奇思,更助长了瑰丽的文风。这样,自由活泼的生命力,狂放、孤愤、奇异、富有想象力的浪漫主义特征,神秘魔幻的巫风巫俗,不仅孕育诞生了屈原的《楚辞》,也同样影响了陈衡哲、谢冰莹、白薇、丁玲、杨沫以及残雪、蒋子丹、叶梦等一批批湘女作家。残雪自己就曾直言:“我信仰的是一种神秘之物,我用有点神秘的方式来实践我的信念。”*残雪:《黄泥街·自序》,见《黄泥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在她的笔下时不时会涌现这样奇幻的想象:“那梦是一条青蛇,温柔而冰凉地从我肩上挂下来。”(《黄泥街》)“那是我的小弟,他在一夜之间长出了鼹鼠的尾巴和皮毛。”(《天窗》)这类扑朔迷离、奇异幽怪的故事,夸张、变形、荒诞、隐喻的手法及大量的梦呓和超现实幻境的描写,曾被评论家称为“先锋派”的东西,实际上更多的是吸纳了荆楚民间文化的资源,具有浓厚的古代荆楚文化蛮荒幻奇,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遗风。同样,白山黑水、林海雪原的大东北自然条件也哺育了极富特性的东北民魂:严寒砥砺了坚忍、豁达的民性,沃野养育了朴实、豪放的民风,密林催生了奇幻、浪漫的信仰,而这一切同样造就了萧红作品的厚重与迟子建作品童话般的自然崇拜。
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不仅成为许多女作家的创作对象,成为构筑作品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影响、规定着作品人物的思想情感、行为习惯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演进,同样潜在地影响着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和创作个性。
第三,女性作家笔下的地域文化还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当然,地域文化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是没有性别区分的。但同样的地域文化在男女两性作家的笔下却各有侧重,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相对于男性作家,女作家笔下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柔性化特征。
其一,在创作题材上,女作家的地域性创作对象多以女性为主体。她们习惯于将视角聚焦于本地域的女性人生以及与女性生活相关的风俗民情上。90年代以描写南方特区都市女性人生为特点的广东女作家张欣的作品就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有所不同。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都市蓝图和全景描绘,也很少有商战的风云和开拓的激情。由于长期生活在广州,张欣更深刻地体会到都市繁华背后的个中三味,而不像有些初来乍到的外地作家轻易迷乱于广州这座都市新贵表面的奢华;作为女性作家,张欣又注重以都市女性(大多是都市白领丽人)为主人公,以她们在事业、爱情、友谊上的追求和失落为情节结构故事。可以说,张欣的“都市情结”始终是以“女性情节”为核心,在她那一个个温情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对造成都市女性误区的男权文化的批判。
由于女性作家更专注于表现本地域的女性人生,而一般女性人生中的两件大事就是结婚和生育,所以女作家们也就更热衷更娴熟于和女性人生相关的婚姻民俗和生育民俗等事象的介绍和描摹。20世纪40年代苏青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曾以真挚、富有生活情趣的艺术个性获得了读者和同行的高度好评。而这种生活情趣的表达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贯穿整部小说的民俗文化的出色描写。小说女主人公苏怀青上轿前后到拜堂成亲所要遵循的民俗礼仪,诸如出嫁前夕与母亲同睡、花轿进门前新娘不准下地、轿神考察新娘贞洁、讨喜包乃至新娘下厨、戴珠冠端坐等不一而足;之后催生、满月、过节等习俗也都围绕着女性人生而展开。由于民俗事象通常表现在地域性社会群体的常态生存形式中,是最富民间特征的文化存在形式,所以,女作家对民俗事象的细致描写使作品显得生动、真实、富有生活气息,且从中暗示着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其二,女性创作的地域文化“柔性化”特征还表现在女作家们往往用“柔性思维”去观照脚下的那片土地,用细腻、温馨的女性眼光选择所要表现的地域风情。原本相对稳定、属于审美客体的地域风情一旦进入女作家的审美视野和情感世界,便沾染了女性特有的审美理想和生命气息,成为女作家个性化的文化载体。与茅盾笔下的金融界风暴、交易所角逐和工人大罢工的“冒险家的乐园”——雄性、喧嚣、疯狂的大上海不同,在张爱玲、苏青和王安忆等女作家那精微的器官感觉中的“小上海”则折射出许多温情。她们用一种属于女性的温婉、琐碎的语调叙说世俗、窘迫的都市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乐趣和无奈,用精致、孤寂、苍凉、忧伤的感觉展示大都会中的真实人生,为“海派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本。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就作过这样的表述:“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梅雨季节潮粘的风,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叽叽哝哝的沪语,也是专供女人说体己话的。这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人的衣袂”*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53页。。当然,“海派”文化具有女性化特征尚可理解,而向来以雄性气质为特征的东北大地在人们的印象中应该是苍茫的旷野,剽悍的民风和铁骨侠肠,可是它在女作家的笔下竟也飘散出女性温柔的气息和诗性想象。迟子建的“北极村”就是一个极富灵性和柔情的北国小镇。在那里,不仅有无尽的松林、奔腾的漠河,还有神奇的鱼汛、流泪的鱼、具灵性的马、通人气的狗,以及碧绿的青草和醉人的都市……,而且这些奇妙的景致常常被笼罩在北方特有的雾幕和极光之中,这就使得干冷、坚硬的北国边塞小镇有了江南水乡般的灵秀和滋润。女作家以她那柔情的笔触,传达出对本地域文化的一份独特体验和领悟,也为中国文坛提供了别一种带着温柔、静穆之气的女性抒情文体。
二、女作家地缘创作的审美价值
不仅地域文学的“女性化”为文坛提供了新的文本价值和意义,而且女性创作的“地域化”也为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创作视野,拓展了女性文学的内涵,使日益琐细、纤小的个人化女性创作走出偏狭,走向厚实和开阔。
第一,女性作家通过笔下地域文化特征历史演变的描述,使读者不仅饱览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风俗画面,而且感受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脉搏的跳动及其发展变化历程。由于“地域”这一概念并不单一指向地理空间的意义,而是涵盖和包容着这一地理空间中具有历时性特征的人文内容的沿革。“地域文化小说不仅是小说中‘现实文化地理’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在描摹者。”*丁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而“历史文化地理”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随着时代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沿革、变迁的。就上海这座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城市而言,由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呈现出开放的海洋文化特征,因此在保持自身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比其它内陆地区更易吸纳他域文化成分,体现了适应时代变迁,善于变革创新的“海味”文化传统。所以,同样的“海味”女性创作,张爱玲、王安忆和“70后”女作家卫慧、棉棉笔下的风格就不尽相同。与《传奇》中飘荡在租界上空没落贵族的颓靡、怀旧的叹息不同,与《长恨歌》里爱丽丝豪华公寓的罗曼蒂克故事及平安里小巷的日常人生不同,年青的小说家卫慧、棉棉笔下充满了“上海宝贝”们黑夜里温柔的蝴蝶尖叫声。虽然作品流露的对物质的热衷、对欲望的追逐、对城市生活的迷恋与她们的前辈一脉相承,显示了上海人追新逐异的现代品格,但是对于深度和高雅的拒绝,对通俗和无序表达的执着,以及个人化的微观叙事方式等,则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比她们的前辈更加叛逆而大胆。当然,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对“海派文学”的新贡献抑或是“海派”文化负面影响的扩张尚有待历史的考证,但地域文化时代性变迁的脉络却非常清晰地隐含其中,我们可以由此窥视到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轨迹和人性的畸变过程。即使在同一部作品里,我们也可以从地域文化风貌的演变中感受到这一点。《长恨歌》就是王安忆将上海城市与女性成长相结合构造而成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它叙述了上海“淮海路”上一个名叫王琦瑶的女孩从十六岁一直到死于非命这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其间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演进。而这一演进又是在上海风俗的演变中渐渐推进展示而成的:从窗幔低垂、灯光幽暗的“爱丽丝公寓”那绫罗和流苏织成的世界,到革命缝隙中“平安里”小巷内冬日围炉而坐,品尝着芝麻和糯米粉的浓香以及糖炒栗子的甜糯,再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淮海路上女孩子平直头发下一点弯曲的发梢、蓝布衫里一角假衬衣领子,以及满大街流行的喇叭裤等特定历史时期的风尚,无不溶入了时代与社会的投影,寄寓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普泛感受。这种将社会风貌、风土人情、人文内涵和历史沿革等方面作历时性展示的作品,在给读者带来地域情调的审美满足时,还能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的时代风貌。
第二,女性创作的地域文化色彩还有助于对女性文学的纤小、琐细和庸俗化起到一定的匡正作用。20世纪30年代,萧红的小说以对呼兰河畔愚昧麻木灵魂的刻画和塑造,站在了对民族、历史审视的高度;当今文坛上,在藏北高原度过了11年军旅生活的女作家毕淑敏,带着昆仑山的冷峻和凝重,带着雪域生活中青春的悲壮、生命的刚烈和对死亡的冷静,创作了《昆仑殇》、《阿里》、《君子于役》、《最后一支西地兰》等震撼读者心灵的作品,她的创作以生活积累的厚实、人性开掘的深度和崇高美的审美品格而倍受读者和论者的称道,为当代女性创作增添了壮美的一笔。在散文界,曾几何时“小女人散文”泛滥文坛,许多女作家(包括一些男作家)大多局限于写个人的经验世界和情感天地,虽然写得很细腻、很精致,也很感人,但从整体的精神和社会内涵来看,毕竟太单薄、太狭窄。而女散文家素素的总标题为“独语东北”的系列散文却以女性少有的大气超越了“小女人”散文的琐碎纤细,以一种不失女性色彩的阔大和沉郁的风格,将悠远而纷纭的大东北历史文化笼于笔下,展现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对历史的反思能力。这种“大散文”风范与她笔下苍茫、辽阔的大东北地域文化融为一体。女作家们在保持女性细腻、敏感而极富诗情的笔调中又增添了地域文化的浓墨重彩,使得她们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深度和厚度。

综上可见,无论是地域文学的“女性化”还是女性文学的“地域化”都为女性创作添加了一道迷人的风景。女作家浓厚的地缘情结使她们在侧重家庭生活、私人生活的叙述外,对所处的地域文化或进行历史道德的判断,或进行审美的文化评价,使人们通过作品不仅感受到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承受的男权压抑,感受到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感受到女性创作超越单薄和纤小的内在文化张力,为作品增加了另一重厚重的美学力量。
三、女性创作地域性的超越
在探讨了女性创作“地域文化”色彩的重要意义后,需要指出的是,“地域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女作家(包括一些男作家)在进行地域文化创作时,应该既“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应将地域文化特征与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情节发展有机结合,在表现上也应适中,切忌剑走偏锋。过分刻意地局限于对某一地域色彩的孤立描摹,过分地依赖于地域性,把地域性作为文学追求的主要目标,地域性可能会变成局限性。一方面可能造成审美感觉上的“隔”,无法进入高度和谐自然的审美境界,另一方面也很难将地域文化精神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最好的地域文化小说可能是那种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再进入信马由缰的无意识层面的小说家的超越境界。”正如“‘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是审美超越过程一样。”*丁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这种超越不仅能达到和谐自然的审美效果,而且也能使女作家突破自身的创作局限,抵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境域。具体地看,这种地域性“超越”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物理地域的超越。作家在进行地域文化创作时不能画地为牢,应在丰富的人生阅历基础上既立足本土又能超越之,以不同的地域文化视角互参关照生存其中的人的精神特征和文化品格,这样才能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张抗抗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启示。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张抗抗已然达到了完全超越的境界,但是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她能够立足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审视各地域的人、人的精神,这样她的文化视野就摆脱了狭窄而走向开阔。生于杭州、青年时去东北插队,后又远嫁北京,每一块生存过的土地都浸透着女作家对本地域文化人格的思考。她惯于以一个南方人的眼光去审读北方人的生存方式,又从一个北方人的视角去评判南方人。所以无论是对南方文化还是北方文化,她都能以一定的“审美距离”对笔下的对象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准确的把握,她的《时间永远不变》、《塔》、《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等,或回忆北大荒的知青经历,或勾画江南水乡的浪漫故事,或讲述京城“作女”们的“另类”生活,这些作品使张抗抗能够不拘囿于本土文化,不拘囿于某种固定的地域眼光,而跳出“庐山”,反观“庐山真面目”,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去审视和打量生活,也使她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都能够拿出与时代同步的作品。类似的还有张欣。她是江苏人氏,有过北京的生活经历,现在广州工作且以广州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由此她获得了以多种眼光探视南方都市生活内蕴的独特视角。面对商业化社会的价值更新和道德巨变,虽然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张欣比其他描写都市生活的年轻作家少了些浮躁和茫然,多了些沉潜与执着。她身处都市却能跳出“都市规则”,老老实实地用颇为传统的技法,演绎着五光十色的城市社会风情,《女性误区》、《深陷红尘,重拾浪漫》、《你没理由不疯》等作品,在对严酷现实题材的处理上,流露出女作家对纯朴和真实的执着向往,弥散着对往昔美好的怀旧气息。
第二,是思想和精神的超越。对地域文化的超越并非意味着创作主体必须浪迹天涯,必须站在一个地域去审视另一个地域的文化形态,只要作家在思想和精神上不拘于一隅,能对历史和现实作全方位的鸟瞰与审视,即使长期立足于某一特定的地域或执着于这一地域文化的深刻挖掘和描写,也可以达到超越,达到与人类精神相沟通的境界。萧红的一生在空间地域概念上虽也跨度很大,出生在东北呼兰河畔,安葬在香港浅水湾,但是她关注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故乡的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男人女人们孤寂的人生。在她的代表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排列着一片片可怕的东北乡村生活图景:“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萧红:《生死场》,《萧红小说全集》(上),第452页。“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生死场》,《萧红小说全集》(上),第450页。他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古老的乡村无声无息,人们按照单调呆板的习惯惰性麻木地生存。在那里,生命的诞生成了“刑罚的日子”和灾难的开始,“充实”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是“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全是“为着神鬼,而不是为着人”*萧红:《呼兰河传》,见《萧红小说全集》(下),第547页。。在这些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们时时感受到生命的无奈。女作家通过对北中国土地上这些愚夫愚妇们蚁子般麻木生活的叙述,揭示了亘古不变沉寂荒凉的乡土人生,揭示了在毫无意义中轮回的沉滞生命,由此她将对呼兰河畔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上升到对民族历史的深思,上升到与现代世界进行对话的形式。在这种现代文化的审美背后,蕴含着她对生命和历史的热烈焦渴,这使她“终于同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对文明、对国民灵魂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彻大悟。”*钱理群语,转引自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8页。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才显示出一种不随时光推移、社会变迁而褪色的美学价值。同样,当我们撩开残雪作品那神秘的地域文化面纱时,也会发现女作家关注的聚焦点始终是对人的终极意义的关怀。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罗兰·詹森在他的《残雪的疯狂冲击》一文中这样评价道:“残雪标出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还未被她的中国同代人探讨过。她的小说超越了本土,而又未失去对日常生活的执着。”*《残雪文集》卷首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由此可见,真正高质量的地域文学,不是一种异域风情、方言习俗的大拼盘,而应表达一种文化意识,并最终超越地域界限成为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它应该以地域性为基点,以民族性为中介,以世界性为目标,既有地方内容、地域文化精神,又有普遍意义和人类精神。地域性因素只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的可能前提,当然,有地域性要比无地域性更有优势,但是,女作家在运用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时,应该把地域性作为创作资源和思维方式的优势,以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博大的情怀去反观和审视地域对象,使之最终超越地域的局限。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就是从江浙地域文化意识走向民族意识,由民族又走向世界而成为具有超越时空局限的人的一种精神特征。女作家的地域文化创作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既突破空间的局限具有人类性,又突破时间的局限具有永恒性。
当今,在日益强盛的全球化浪潮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性;同时,工业文明和现代文化的发展也扫荡着乡土中国的传统,扫荡着老城的特色,代之以千篇一律的现代气息。但是从上述女作家的笔下我们仍可看到她们对历史记忆的追述,对逝去文化的挽救和对鲜活的富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描绘。她们将笔下的女性人生与独特的地域文化相结合,使作品显示了稳定、淳厚、隽永、历久不衰的深厚生命力。这种对地域文化的尊重和追求,不仅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客观需求,也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源泉,它有助于使女性创作摒弃纤弱走向厚实,摆脱狭隘走向广阔。当中国女性文学在着重探讨女性性别问题,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能同时张扬民族文化、增强地域文化的色彩,将使女性创作更加充满生机富有魅力。
[责任编辑:刘光磊]
OnRegionalComplexinWomen’sLiteraryWritings
ZHANG L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0, P.R.China)

women’s literary writings; regional complex; regional transcension

张岚,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舟山 3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