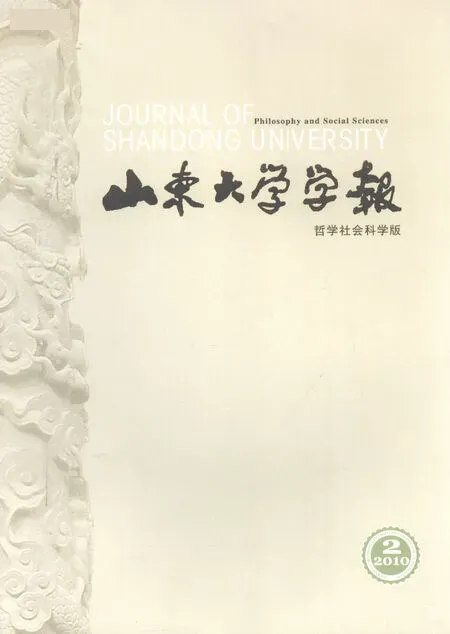利簋铭文新释
张富祥
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到目前为止,仍是已知西周最早的有铭文铜器。其铭文共有如下32字:
珷(武王)征商隹(唯)甲子
朝岁鼎克闻
夙又(有)商辛未
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
此铭直接涉及武王克商的重大史实,历来受到高度重视。然学者的训释至今尚分歧无定,故此再就有关资料略加检讨,试提出一种新解释。
一、关于“岁鼎”
利簋铭文的史料价值主要在前 14字,本文亦只讲这 14字。以往各家训释的问题点,集中于“岁鼎克闻夙有商”7字,而尤以“岁鼎”2字聚讼最多。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以举出下列几种:
1.唐兰先生对“鼎”上一字不释“岁”,而释为“戉”,通“越”,以为“越鼎”即“夺鼎”,指夺取政权。①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第 8期。
2.释“岁”字为岁星,“鼎”训“当”,“岁鼎”意谓“岁星正当其位”。此说由于省吾先生提出②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但未坚持;张政烺先生有细致的申论,并谓“克昏夙有商”指“一夜就得以占有商国”③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此说,同时别存一种解释,以为“岁鼎”当讲为“岁星上中天”④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 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 44-45页。。
3.释“岁”字为岁祭,“鼎”训“贞”,即贞问。许倬云先生同意此说,以为“岁释祭名无疑,不能作为祭的对象”,又谓“武王伐商,奉文王的木主以征,……战事前以用戈杀牲的岁祭来致祷,也是可能的”⑤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 98页。。
4.杨宽先生释“岁”字通“刿”,训杀伤;“鼎”通“丁”,义为“当”;以为“岁鼎克”三字应连读,意谓“冲杀后当即得胜”;又谓“夙有商”指“快速占有商邑”①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5000页。。
这几种看法,以“岁祭”与“岁星”说影响较大,而近年尤其流行“岁星”说。此二说有冲突。张政烺先生认为“古人迷信,像征商这样大事,卜筮在所不免”;但在甲子朝,已陈师牧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周武王面对强大敌人,只能决战,不容迟疑,当无再卜问鬼神的余地,而文义绝非倒述兴师前的预卜,可见此鼎字不作贞卜讲”②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 1期。。杨宽先生则以为“岁鼎”事叙述在“甲子朝”之后,若释“岁”为岁星或岁祭,皆“未免文理难通”③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第 98页。。
“岁祭”说的难处,首先在与甲骨文、金文的辞例不合。甲骨文中用作祭名的“岁”字下,多接牲类、牲数或以“于”字介出祭祀对象之称,且皆为贞卜内容,而绝无以贞卜之“贞”字置于“岁”字之后者。若谓利簋铭的“岁鼎”为特例,则讲“鼎”字为贞问,其下“克闻夙有商”便成卜疑的内容。持此说者释读“闻”字为“昏”,以为指黄昏时候,如此则原文当点作:“甲子朝,岁,鼎 (贞):克,昏夙又 (有)商?”然金文中所见的赏赐册命文字皆为已有事实之叙述,又断不可能使用此类疑问句式。若说此所记录的只是占卜结果,金文中亦绝无此类事例。
持“岁星”说者,多以“岁鼎”与《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中的“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比照,以为“岁鼎”亦应是指星象,似乎有所依据。然据笔者考察,《国语》所记伶州鸠语问题极多,很难与利簋铭文相印证。其一,按《国语》原载,其文首叙伶州鸠谏阻周景王铸大钟,所说皆为儒家言;其下又记周景王问律于伶州鸠,伶州鸠的回答皆有关乐律问题,强调“七律”出于自然,并及于武王“吹律定声”的故事,实出于兵家言。前后所记思想并不一致,两段文字可能不出于一时。其二,伶州鸠所言天象皆基于天文学上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知识,而就现在所知,这类知识相当晚起。所谓“岁在鹑火”,当是战国时人用不超辰的岁星纪年法推算出来的,断非周初实测的记录,故亦不可能出于乐官世家的传述。其三,《荀子·儒效》篇所说的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太岁”,用的是极晚出的太岁纪年法(与岁星纪年法次序相反的虚构形式),照张政烺先生的说法,大抵谓“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④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 1期。,与伶州鸠语所说不属于同一系统。依《国语》韦昭注,鹑火之次指张、翼、轸三宿,三宿在二十八宿系统上属于南方,与“东面”之说并不相合。《尸子》记武王伐纣,鱼辛谏“岁在北方,不北征”,又恰与“岁星正当其位”之说相违。此皆出于战国秦汉间的“兵忌”之说,张政烺先生亦谓“迎岁”指“背岁”而言。其四,《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对伶州鸠语有逐句的解说,实是以伶州鸠语信而有征为前提,又据《三统历》用超辰的岁星纪年法所推得的日期佐证之,故在今绝未可以《世经》的推排反证伶州鸠语之可信。其五,伶州鸠语中包含有“五德始终”说的内容,其中讲“数”而专注于“七”,音尚大林 (林钟),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汉为火德”说相应。其六,伶州鸠语中的武王“吹律定声”故事,实出于汉代流行的“旋宫法”,亦即以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主音)以定不同音高之五声音阶及其他音阶的一种方法。根据上述几点,我们以为伶州鸠语所述天象本出于后世的托撰,因而是不可靠的,亦不能用以印证利簋铭文的“岁”字指岁星。⑤张富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东方论坛》2005年第 3期。
联系“甲子朝”及下文“夙”字来看,“岁鼎”二字仍当为时间用语,而不当作其他理解。学者多谓此“鼎”字用作“贞”,训“正”,此说至确。如是则“岁贞”读作“岁正”,“岁”、“正”皆为名词而连用为时间副词,盖为当时成语。由此推求,我们以为“岁正”实指商人的正月初一 (夏正),亦即岁旦,为“甲子”之日的说明语。《大戴礼·夏小正》云:“初岁祭耒,始用畼。……其曰初云尔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以“初岁”系于正月下,可与“岁正”对看。《周礼》中凡五见“正岁”一词,郑玄于《小宰》注云:“正谓夏之正月。”又于《大司徒》注云:“正岁,夏正月朔日。”后者尤可证“岁正”为正月初一,“正岁”可视为“岁正”之倒语。《周礼》中还屡见“正月之吉”、“孟月吉日”、“月吉”等词,郑玄皆以“朔日”解之。《后汉书·周磐传》云:“岁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李贤注:“岁朝,岁旦。”此当即古语之孑遗,又可与“朝岁正”对读。甲骨文中已常见“正月”之称,与“一月”并用,而“正”字单用多指祯祥。“正月”之称可能即起于以岁首之月的第一日为“正”的风俗,因这一天为全年的第一个吉日,故称“岁正”,或久而即以此月为“正月”。
要确切地了解此义,还须对“甲子朝”的具体涵义有恰当的领会。
二、关于“朝”字
各家解释利簋铭文,都讲“甲子朝”为甲子日的清晨,以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实则这个“朝”字别有意义,并非是指清晨。这点对理解利簋铭文甚为紧要,过去忽略于此,未免是个疏失。
“朝”字在西周金文与古文献中有特殊用法。如下列各例:
(1)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方彝)胐
(2)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尚书·牧誓》)
(3)唯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尚书·召诰》)
(4)粤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同上)
(5)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同上)
(6)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同上)
(7)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尚书·洛诰》)
(8)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逸周书·世俘》)
(9)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同上)
(10)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明》)
(11)会朝争盟,何践吾期?(《楚辞·天问》)
(12)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吕氏春秋·贵因》)这些“朝”字,前人基本上都讲为清晨、清早或早,未见得惬当。仅按词性而言,上举诸例大致可分为两类,这里权且称为甲类和乙类。甲类包括例(1)—(9),皆用作副词;乙类包括例 (10)—(12),皆用作名词。乙类的意义较为明显,“朝”字均指约期。例(11)以“会朝”与“践期”相对,盖“会朝”犹言“会期”,“会朝争盟”即践会约期而争相参与盟誓;例 (12)以“朝”与“甲子之期”相对,而“要”字之义即约。此 2例都以“朝”、“期”为互文,只不过前者是指武王伐纣传说中的盟津之会,后者则指克商的日期。例 (10)的“会朝清明”,疑与例(11)的“会朝争盟”同意,“清”或为“请”字之讹,“明”读作“盟”;若此例的“朝”和“清明”都讲为清晨,则词义重复,且失去“会期”的意义。古人称一日为“一朝”,以“朝”字代指日期容易理解,用为动词则即指会期。
甲类多以“朝至”连言,盖为周人熟语,尤当仔细辨析。陈梦家先生知此类“朝”字讲为清早不惬,故举出上引(2)、(4)、(5)、(7)4例,别出见解,以为“朝至”当讲为“东至”:
凡此洛、洛师、牧并成周由西土的周说来,都属于东国,所以朝至也者谓东至。金文朝字一旁象日出草中,一旁象水潮之形。日出东方为朝,故朝有东义;《考工记》匠人建国“以正朝夕”,《正义》以为“言朝夕即东西也”,《尔雅·释山》“山东曰朝阳”。①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 39页。
以此说解释上引甲类句例,大部分可以讲通;然例 (9)的“武王朝至,燎于周”,实指武王自东国之地西至于周,与陈先生所解释的“东至”不合。我们的看法是,“朝”的本义指早晨,在用为泛指的时间名词或副词后,已转义为初、始或先。《荀子·礼论》有“月朝卜日,月夕卜宅”之文,杨倞注:“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洪范五行传》有“日之朝”、“月之朝”、“岁之朝”诸语,注谓“自平旦至食时为日之朝”、“上旬为月之朝”、“自正月尽四月(疑当作三月)为岁之朝”。又《文选·东都赋》“夏正三朝”薛注:“三朝,岁、月、日朝。”这类“朝”字都已转义为初,“岁、月、日朝”犹言岁之初季、月之初旬、日之初段。以此解释上举甲类句例,则无一不能通顺。如例(3)的“王朝步自周”,可释为王初行于周或始发于周;例 (6)的“朝用书”,可释为初用书或始用书。其余诸例的“朝至”,则可释为初至或始至,言某日“朝至”即指某日到达;若谓“朝至”都是指清晨到达,则不合情理。“朝”、“初”古音可以相通。《史记·伯夷列传》索隐引传说,谓“夷、齐之父名初,字子朝”,质诸古人名、字相应之例,此恰可证古“朝”字有“初”字之义。
明白了古“朝”字的这一用法,即可引出对利簋铭文的新解释。甲骨文中的纪时词语,“朝”指“旦”(天亮)至“大食”(早饭)之间的时段,“旦”之前称“昧爽”(天蒙蒙亮),“昧爽”之前称“夙”,“夙”指前夜的最后一段①常玉芝:《百年来的商殷历法研究》,《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 41 -42页。。亦即由纪时而言,若用“朝”字而不用“旦”字,便应以夙 -昧爽 -朝为序。利簋铭文有“夙”字,显然是纪时词语,假如以“朝”字指早晨,则“朝”居前,“夙”居后,即与纪时的顺序不侔。《尚书·牧誓》只称“甲子昧爽”,“昧爽”也可说是“夙”时的末段。所以我们认为,利簋铭文的“朝”字仍当理解为“初”,虽为时间副词,而不是纪时词语。“甲子朝岁鼎”5字当连读,犹言“甲子初岁正”,意谓正当甲子岁旦这一天,或曰甲子日刚好是岁旦。如此乃文意贯通,全无龃龉。《逸周书》谓“甲子朝至,接于商”,意指周人于甲子这天刚刚到达牧野之地,就已与商人接战,“朝”亦为“至”之状语,而不是指早晨。
三、关于“甲子”的日期
利簋铭文的出土,无可置疑地证实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武王克商在甲子日是正确的。然本文即以此“甲子”之日为岁旦,因现在已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或不免令人生疑。不过这点仍可由传世古历法资料作些推导。
商、周历法的真实情况,如今已无法搞清。后人往往习惯于以大月 30天、小月 29天的朔望月体制推排古历法,其实直到西周时期,制历者是否已明确认识到“平朔”与“实朔”的区别,也还是有待证实的问题。笔者在另文中曾谈到:“过去刘朝阳等先生曾主张商代历法实行的是‘一甲十癸’之制,即一年通常有 360日,平分为 12个月,每月三旬,每旬皆始于甲日而终于癸日;没有固定的闰月,但有时因特种关系而附加 10日或 30日。自胡厚宣先生对此提出反驳之后,学者即多不之信。然而商末连续八九个月的征夷方历日,甲骨文的记载历历可见,仅按现有的认识,实际上非用‘一甲十癸’之说便不能排顺。……商代历法应该前后有变动,例如武丁卜辞中多有‘十三月’的记录,祖庚、祖甲以后却不见再有‘十三月’,可能即与历法体制的变动有关,不一定是由年中置闰所致;或者如刘朝阳先生所说,商代干支纪日与实用的四季记时原是两个系统,二者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们甚至怀疑商末历法曾迁就周祭,实行过平均每年 365-366日的纯阳历,有如古代埃及的太阳历。据卜辞材料,商人若果曾实行此种阳历,其历月安排既有可能是每月 30日而积两年加一旬,也有可能是大月 31日、小月 30日相间的;若是相间之法,则有可能是隔月加一日,且 31日之月的最后一天与下月第一天用同一甲日干支。商末征夷方历日,有相邻两月同有甲午日的,即可用此法解释,且不须置闰月。”②张富祥:《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问题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2期。这些都属于月首问题。至于岁首,则商、周是否即从一开始就分别建丑、建子,亦即分别以夏历的十二月、十一月为岁首,自来也无定论。清人陈厚耀《春秋长历》卷七就说过:“考之往古,《诗》、《书》皆用夏正,其以建子为月正者,实始于东迁后时王之制,非文、武之制也。”假如商周之际仍行用传统的夏历,并确曾实行过“一甲十癸”之制(或以此为基础而稍作调整的历制),那么其时每年都以甲子之日为岁旦就完全有可能。
《甲骨文合集》著录的 24440版,有“月一正曰食麦”之文,卜辞学者多谓指正月尝新麦。若依此说,因北方地区尝新麦当在夏历五月,则殷历的正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殷正当建午而非建丑。我们很怀疑“月一正”其实是指夏历的正月一日,“月一”即一月,“正”即一日。因这一天要吃面食,故称“食麦”,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固有传统。此版为一干支表,在“月一正曰食麦”6字下即刻一月份的日干支,始于甲子,终于癸巳;下接“二月父”(“父”二字的隶定和考释尚无定说),然后刻二月份的日干支,始于甲午,终于癸(亥)。两月皆为 30天,合于所谓“一甲十癸”之制,亦可作为甲子日即夏历正月初一的佐证。
武王征商的历日,后人纯按周正建子的朔望月体制编排,甲子之日的月份定位及所对应的月相必不同。《逸周书·世俘》篇谓“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可能实以“二月既死魄”为周正二月的末段,而以甲子日为周正的三月一日,以当夏正的正月一日;《世经》所录《尚书·武成》篇的逸文,谓“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三月”可能是“二月”之讹(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有此说),大概由于传抄者误认为甲子日即三月五日而擅改。实际上,“一甲十癸”制下的月相所对应的日期是不固定的,与朔望月体制下的月相所对应的日期相对固定的情况完全不同,后人若以旧有的月相及其所对应的日期记录改按时下的新历推排,则必致凿枘不入。现存《武成》、《世俘》篇中的武王征商历日之所以前后参差,无论如何变通都推不拢,根本原因即在此。《世经》全由西汉《三统历》推排,而定武王克商的甲子日为二月五日,又添置闰二月,更非周初实有的历日,尤不可较真。大概在春秋战国以前,此甲子日本为夏历的正月初一还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因此史不绝书,而后来这一事实逐渐湮没不彰,就连历法学者也竟不能知其所以然了。
四、关于“克闻”
最后需要解释的是“克闻夙有商”5字的意义,其中的关键是“闻”字。
“闻”字的隶释有甲骨文为依据,当不误。此字在铭文中不能作本字解,这是显然的;但以为此字通“昏”,用作纪时词语,亦大可商量,以“昏夙”连言的用法实属费解。张政烺先生谓“昏夙是从初昏到黎明前,指一个夜晚”①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 1期。,若果然如此,便与“甲子”指称白昼之日的常规意识不合。卜辞中的“昏”字指暮时,所指并不延伸到夜间,更不是指一整夜。所以“甲子”之日至多从昧爽时算起,并不能包括此前的夜晚时段;即使如有的学者所说,商人的一日从夜半算起,也涉及不到前一日的昏时。杨宽先生以“朝”、“昏”相对,以为指牧野之战从早到晚的一整天,此从情理上可通;然与“岁鼎克”连读已成问题,又别讲“夙”字为快速,恐与训诂及事实皆难相契。灭商之役可以是一整天,但此役商人倒戈,周人未必是到黄昏时才得以占领商城。若将此“昏”字与《逸周书·世俘》篇的“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联系起来,也讲不顺,因为“昏”若指“甲子夕”,则与“夙”字连用当言“夙夕”,而不当言“昏夙”。这些都与“朝岁鼎”的考释有关,此三字讲不通,则以“闻”字通“昏”亦难通。
按古今载籍,凡言周人灭商事,最常见的是以“克商”、“克殷”为言,例不胜举。毫无疑问,此本为周人习用语,故利簋铭文的“克闻”亦当循此作解,且为现今所见此类用语的最早实例。成王时的小臣单觯铭文,有“王后克商”之语,指周初第二次“克商”(平武庚之叛),正可与“克闻”之语相参证。照我们的意见,此“闻”字当借释为“衣”或“殷”,为“克”字的宾语,实指商人。自郭沫若先生发明“衣即殷城”②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 496、503页。之后,学者皆知商人原不自称“殷”,称“殷”出于周人的习惯,且在早于书面语中亦只写作“衣”而不写作“殷”,周原甲骨 H11:1即称商王为“衣王”。商人本出于东夷,在据有中原之后,夷人广布各地,故居处西土的周人率称商人为夷人。用作族称的“夷”字在甲骨文中本写作“尸”,因“尸”字与“人”字易混,故有时在“尸”字之外包加“衣”形作为声符而写作“”,“尸”(夷)、“”、“衣”、“殷”皆一声之转。周人称夷人为“衣”即由此而来,实是“”字脱落了“尸”之本字而只剩了声符。以“殷”字专指商人较晚起 (大约不早于周初成、康之际),继后“殷”字流行,“衣”的称呼遂废;但西周金文中称四方夷人仍用“尸”字,大概直到西周末至春秋初才逐渐改用“夷”字。《尚书·武成》篇的“一戎衣,天下大定”,“衣”字即当读作“夷”,句意实指周武王统一了西戎东夷各部,而自伪孔传及郑玄解释为“杀兵殷”之后,种种附会之说都不足据③张富祥:《殷名号起源考》,《殷都学刊》2001年第 2期。。依此解释利簋铭文,“克闻”之“闻”释为“殷”顺理成章,“闻”(殷)指商人的东夷身份,“夙有商”的“商”字则指商都。“闻”、“殷”二字古音皆属文部,自可通假;“衣”属微部,而微、文二部亦可阴阳对转。
五、结语
根据本文所考,现在可以对利簋铭文的前 14字作一总结。此 14字当标点为: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贞(正),克闻(殷),夙有商。
意为: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岁旦这天打败殷人,一大早就占领了商城。看来周人灭商,是乘商人过大年之机,长途奔袭而闪击成功的。商人无备,斗志松懈,故一触即溃,当天即灭国。由此可以考见好多问题。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于当年十二月由盟津渡过黄河,至二月甲子昧爽才到达商郊牧野。实则周人既取突袭之策,决不会行军这么久,从盟津到商都顶多不过十天左右,即使从周人始发兵算起,大约也不过个把月。同篇又载武王伐纣,“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 (拒)武王”。这说法对双方的兵力当都有夸大。他书或说武王用于牧野之战的兵力只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可能接近于实际。盖周人先以精锐突击,数千甲士即足可使商人兵败如山倒。商人仓促起兵接敌,很可能只有守城的几万人(或可达到七万人左右),其结果可想而知。商末连年征伐东夷,国力大耗,大概当周人伐商时,商朝的兵力也还多在东方,周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联合西部诸侯,一举灭商。利簋铭文原是很直白的,而以“岁鼎”二字记录了甲子日为岁旦的事实,是其最可贵之处。如今若不能看破这一点,便使铭文的价值大打折扣。至于以“岁鼎”与岁祭、岁星等扯上关系,反而使铭文的解释变得复杂化,更无法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