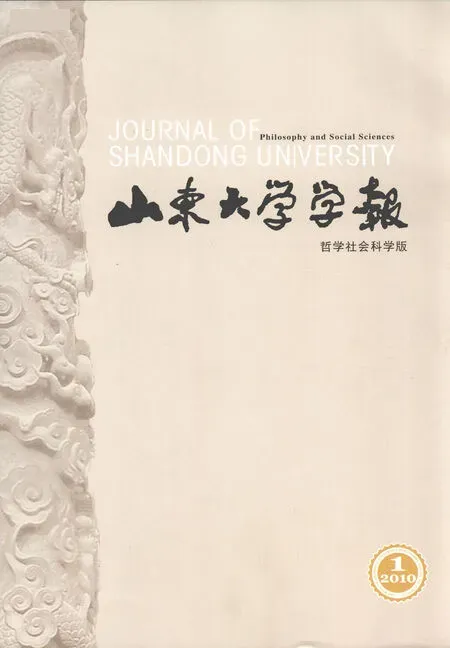近 20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郭震旦
当今历史研究领域最具颠覆性的事件恐非“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对“宏大叙事”、“大写历史”的反叛莫属。自从上世纪 60年代以来,以往貌似不可质疑、不言自明的历史研究范式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致命的狙击,像一个被击中命门的巨人摇摇晃晃。虽然现代史学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敲击下早已遍体鳞伤,但由于远离震源,仍然运行在现代史学轨道上的中国史学好像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狂风骤雨”,后现代这一魔鬼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屋门外的脚步声。但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殊不知后现代史学的幽灵早已将“特洛伊”木马“病毒”植入中国历史学,这一点我们从一些印有后现代主义特有胎记的词语在史学界的广泛使用就可以看出来,“文本”(text,巴特)、“解构”(deconstruction,德里达)、“书写”(writing,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铸造的词语早已成为连缀历史文章的基本词汇。众所周知,“文本”这个词最能代表后现代的旨义,单从字面意义上讲,“文本”与昔日惯用语“文献”(documents)或“作品”(works)并无二致,但其实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文本”意谓符码允许开放且多元的阐释进路,而“文献”或“作品”则代表作者与实体(reality,就史学而言则是史实)之间封闭或自足的实录,其解释系统即使不是固定的,也是有限度的。在被称为后现代“祭司”的德里达看来,“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而在人的“批判性阅读”中,文本是呈现无止境而多解的,只是语言符号的无限戏耍,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除了依靠残留的文本以外,并无过去的实迹可以依傍。①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 5、138-148页。可见,对“文本”一词的接受就意味着不知不觉间对那个危言耸听的“历史之死”说法的认同。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②参见仲伟民:《后现代史学: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光明日报》2005年 1月 27日。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③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1年第 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 35页。但随着史学工作者对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在学术关注点日渐散漫、学术动向“去中心化”的今天,对后现代史学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难得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加入到这一讨论中来。持中而论,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无论是从持续时间,还是从所发挥的显性以及隐性的影响来说,在过去 20年间,还没有一种西方史学思潮能够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所掀起的波澜相比拟。它已经促使大陆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史学观念、治史路径以及历史研究新范式的建立等方面发生大幅度的转移,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格局。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近年来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情况进行一次粗线条的梳理,以便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目前对大陆史学界介绍和后现代史学研究进行总结的文章主要有张仲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历史学述评》(《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以及张光华的《大陆学界“后现代与历史学”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08年第3期)。前文主要是对西方后现代史学的述评,仅在最后一个自然段梳理了大陆学界介绍和研究后现代的情况;后一篇文章主要关注点则在对几个后现代史学具体问题的讨论上,涉及的文章不多,与拙文甚少交集。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粗线条的概览,就难以面面俱到,一些重要的论作就有可能被遗落而无法进入讨论的视域。本文拟以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大规模翻译这三个层面作为观察的视角。
较早被引进的后现代史学经典文献当属 1990年第 6期《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刊登的安克斯密特的文章《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以及 1993年出版、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所收录的选自海登·怀特《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的 4篇论文,其中包括可说是海登·怀特著作中最具锐度的那篇《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正如大多数邂逅都没有在当时彰显自身的意义一样,虽然怀特文中有“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的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转变为一个喜剧境遇。……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这样离经叛道、直接取消历史学客观性的话语,但也许因为他在该书中是以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面目出现的,文章似乎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和反响。1996年,郑群在《世界史研究年刊》第 2期上发表了《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历史学》一文,这是大陆历史学界较早从理论上系统介绍后现代史学的文章。其后,对后现代史学的讨论渐趋热络,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直到 2004年达到高潮。②关于国内后现代史学的学术史梳理参见张仲民《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历史学述评》的相关内容。这一年广东的《学术研究》和北京的《史学理论研究》都组织了“后现代史学”笔谈。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王学典主持的《东岳论丛》“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专栏所开展的后现代史学讨论。这一讨论从该刊 2004年第 1期开始,为时长达一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次讨论是在国际间展开的,参与讨论的既有大陆的史学家,也有台湾地区学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文斯、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凯斯·文沙特尔等都参加了对话。这些重量级学者的参与,大大提高了这次讨论的学术水准。
总括起来,国内期刊所发表的讨论后现代的文章大都围绕着后现代史学的基本观点作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寻根溯源,重点介绍后现代史学的“始作俑者”福柯、海登·怀特、德里达等人的史学思想。③参见高毅:《福柯史学刍议》,《历史研究》1994年第 6期;刘北城:《福柯史学思想简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 2期;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陈新:《解构与历史——德里达思想对历史学的可能效应》,《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 4期;余章宝:《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 2期;黄进兴:《“文本”与“真实”的概念——试论德希达对传统史学的冲击》,《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等。关于福柯这名“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这些文章主要围绕其对理性霸权的批驳、对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反抗、对疯癫、疾病、犯罪和性这类“边界问题”的解读、对客观性的瓦解、对历史进步的质疑以及对历史总体化的拒绝等论题来进行;而对海登·怀特的介绍,则主要围绕他的四重比喻理论以及他对想象和叙事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的强调,突出其主导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的领袖地位;至于德里达,则重点介绍其所使用的“文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对历史真实的冲击。这些文章的刊行,清晰表达出上述三人思想实乃后现代史学的三大策源地。第二个板块则着重于后现代理论的述评④参见陈启能:《“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东岳论丛》2004年第 2期;张仲民:《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论》,《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张永华:《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杨共乐:《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程光泉:《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东岳论丛》2004年第 2期;韩震:《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等。: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修辞的转向”、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主要特征等方面,虽然对后现代的偏颇之处有所质问,但论者对于后现代史学在揭露历史书写中不为人所知的面相、敦促历史学家重新检查历史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促进人们对历史、对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理解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多持肯定态度。第三个板块则集中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尤其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上。①参见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 1期;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文史哲》2004年第6期;古伟瀛:《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新与旧的辩证》,《东岳论丛》2004年第5期等。鉴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研究造成的巨大冲击,这些文章普遍认为历史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后现代主义极有可能为历史编纂学的重大转变或新的转折提供了原始动力,因此找寻新的发展路径成为历史学的当务之急。具体到中国史学来说,后现代史学是挑战,更是机遇,如果将后现代史学看成是一种视角而非固定的严谨的方法,那么,在中国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互动过程中就完全有可能达致一定层面上的互补。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的介绍就带有浓厚的对民族史学的反省意识,其目的在于以来自异域的后现代史学为参照物来调整和改革现有史学模式。
除了通过论文进行专题性研究外,系统的专书研究也构成这一时期对后现代史学介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包括王晴佳、古伟瀛所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黄进兴所著《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三联书店,2008年),以及韩震、董立河所著《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一书包含“后现代主义简介”、“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三大部分。该书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而对于历史研究如何吸取后现代史学的合理成分颇具建设性。作者在书中特意探讨了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史学的挑战,虽然没有明确表白,但作者把后现代因素当成中国史学转折的一个正面促进因素是可以推论的。《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一书原在台湾出版,2008年由三联书店引进,在该书简体版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中,作者明言:“当下亟需一部立论持平且能为华文读者设想的著作,让我们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立足点,去评估其(后现代史学)功过得失,进而掌握自身史学发展的契机。”该书写作脉络是“首列主题,辅以学术源流,再举出代表性的人物,最后方予个人的品评,希望掌握其命脉,明了其得失。”这种设计,既能照顾到线的延伸,又兼及面和点的铺陈,做到了线、点、面的通合,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因而论述较为全面。该书颇为传神之处是,作者将后现代史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归纳为“往事不可追”。为了凸显后现代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冲突的张力,该书的篇章每取兰克史学以为对照面,通过强烈的对比来突出后现代史学的“非圣无法”。对于后现代史学中破坏裂度最大的福柯、海登·怀特以及德里达,黄氏专列三章予以介绍,并在每章中以“拦截后现代”为名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点评。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激情的呐喊,并无法取代理性的思维。史家若不想随波逐流,亦不想坐困愁城,犹得冷静面对后现代主义严峻的挑战,方不致进退失据,筹措无方。”
上述两书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都有北美留学或从教经历,贴近欧美史学实践的现场,因而能够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认识对象,准确把握后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而不是只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和表层批判上。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一书以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中心,系统阐述了后现代叙事理论、历史叙述的诠释性、后现代历史隐喻理论、以及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等问题。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为我们扬弃传统历史学、建构新的历史学理论提供了契机。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对后现代史学发出强力质疑而又对其抱以“同情之理解”的伊格尔斯在他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有关后现代史学的论述,成为大陆史学界衡论后现代史学的基本坐标,影响至深且巨。
随着后现代史学理念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大量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迻译在最近几年成为介绍后现代史学的主流,这构成了对后现代史学介绍的第三个层面。首先,被称为后现代史学旗手的海登·怀特的主要作品大多已经被引进到大陆,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一书在 2004年的面世。该书堪称最近几十年“历史哲学方面最具革命性的一本书”,②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第16页。是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后现代史学理论中最具颠覆性的一部文献,因而是后现代史学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由于西方后现代史学的很多命题都是由本书发展而来的,因而该书在后现代史学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构成了其他后现代著作的理论基础。该书的出版,对于国内史学界全面了解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中心人物海登·怀特的史学思想,进而准确把握整个后现代史学的性质助益匪浅。海登·怀特另两部重要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以及《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也已列入韩震主编的《历史哲学译丛》。①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还出版了由陈永国、张万娟翻译的海登·怀特自选文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列入该译丛的还有海登·怀特最坚定的支持者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以及凯尔纳的《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等后现代历史哲学家的著作。除此之外,杨耕和张立波主编的《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也已于 200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收录了《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历史的逻辑:把后现代主义引入视域》、《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等作品。编者在交代该丛书的宗旨和特点时说:这套译丛围绕在后现代视域中如何理解历史的本质,如何书写历史,以及历史叙述、历史表征、话语的修饰、想象、形式和内容等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一整套方法论思考,建构了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方式。
与引进后现代历史哲学书籍比肩而行的,是后现代历史作家们作品的输入。早在 1997年,商务印书馆就推出了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2009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一套“历史—人类学译丛”,所收著作包括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以及《档案中的虚构》。至此,被安克斯密特推许为后现代史学三大代表性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后现代史学三大名著的出版意义重大,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介绍以来,对中国大陆史学界来说,后现代史学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人们只能是隔着大洋举踵而望,所以虽然对后现代史学的讨论一直不乏热度,但是那更多是停留在一种概念和理论的状态之中。而现在,通过后现代史学三大名著在中文语境的泊岸,过去那些显得虚无缥缈的后现代意绪终于有机会得到归位和坐实。通过这些标本式著作,东方历史学家们就能够明了“小历史”、微观史、新文化史是如何在后现代历史学家的笔下展开的,往常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排斥和遮蔽的历史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作业方式下得以呈现的。
在此,有两本访谈集不能不谈,一本是《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由波兰女历史学家埃娃·多曼斯卡主编,内中收录了编者对当今世界史坛卓有声望的历史哲学家的访谈,这些历史学家包括海登·怀特、汉斯·凯尔纳、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耶尔恩·吕森、阿瑟·丹图、列昂奈尔·戈斯曼、彼得·伯克、斯蒂芬·巴恩等,可谓阵容强大,群贤毕至。虽然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们对待后现代史学的立场不尽相同,但访谈无疑是围绕着海登·怀特的观点来进行的。书中提到他的地方达 232次之多。正如阿兰·梅吉尔在为该书所写导言中说:“这些访谈提供了你所可能找到的有关 20世纪末叶历史学状况的最好不过的思索。”该书给人印象最深之处是西方历史学家在历史思维方面的活跃,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西方史学将往何处去,又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思考的问题。另外一本是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夫人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所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该书辑录了编者对 9位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中声誉卓隆的历史学家的访谈,其中对三位后现代史学的翘楚——卡罗·金兹堡、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的作者罗伯特·达恩顿——的访谈尤为引人注目。在访谈中,三位受访者分别谈了他们的思想轨迹、学术选择,也集中谈了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这一当代历史思潮和运动的看法,为读者了解他们的史学实践以及后现代史学的旨趣提供了第一手的知识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访谈是一种介乎思想和严谨的写作之间的文体,最易于捕捉运动中的观念。在这种文体中,历史学家更有机会表达严格的学术文体所必定要压制的思想和情感,将那些原本可能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情感清晰地展现出来。因而两本访谈录的出版,对于我们更切近的理解后现代史学大有裨益。
这样,从最初的披着文学批评外衣潜行到现在的成建制编队亮相,经过了十几年的“行走”,作为一种新知识形态输入的后现代史学终于完成了从远眺到近观的一个过程。
对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之旅做一个走马观花的梳理之后,我们有必要简要评述一下这一完全来自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新史学形态在中国流布的意义。众所周知,后现代史学的最大目标就是摒弃结构和元叙述,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史学表现出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因为历史研究中对结构和元叙述的追求,不可避免会限制人的活动。它消除了被作为公式的现代性以外的选择,从而使历史变得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作为西方后现代史学的族裔,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自然会或多或少体现这一精神的内涵。可以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解构和重构的两重意义。所谓解构,就是说从历史学的认识论特点出发来论证历史学客观性的局限,进而暴露过往那种民族国家历史模式的虚妄,并对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主义的方法表示质疑,从语言方面重建历史与文学艺术的联系。所谓重构,就是舍弃“宏大叙事”,努力挖掘被“大历史”、“元史学”所淤埋了的丰富多彩的下层社会的历史,从对社会结构的关注转移到人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从对线性的追溯转移到对空间的深度描绘,“从把历史视为能复现过去的实证主义历史观转到历史可以以某种方式构建过去的历史观”。①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第16页。可以看出,解构和重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现有史学模式进行改造,甚至是逃逸。这是其一。
其二,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当今世界史学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所谓‘新文化史’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史学研究的主流,而这一变化完全是由后现代史学观念推动的。②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作为对这一潮流的呼应,国内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其中“新社会史”的勃兴最具代表意义。“新社会史”虽然和“新文化史”名称不同,但双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完全相同,可以说,中国的“新社会史”就是欧美“新文化史”的翻版。同西方的“新文化史”一样,“新社会史”也专注于微观史的研究,把研究对象从对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对于边缘性问题情有独钟,医疗史、身体史、观念史、以及时间空间和心性等构成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新社会史”也追求“叙事史的回归”,强调历史写作的文学品性,最终使历史情景化。这两点在治史旨趣上与西方的“‘新文化史’的文化和语言转向”如出一辙。可以说,“新社会史”的方兴未艾,标志着在世界史学大合唱中,中国史学已经在担任着一个声部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