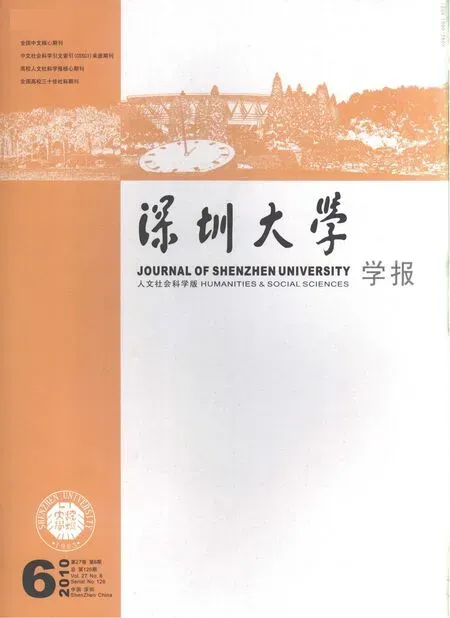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
(印)哈拉普拉萨德·雷易
(Haraprasad Ray)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
(印)哈拉普拉萨德·雷易
(Haraprasad Ray)
20世纪之初,印度就开始了对中国语言、文学及文化的接触、探索与传播。此后,在中印双方各界人士的共同致力下,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佛教研究和中印文化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印度学者也对现代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领域表现出了较多的关注。除此之外,一些新的研究维度也在出现。但研究视角仍需拓展,而一手研究资料的缺乏,或许是目前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中所面临的最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印度;中国学;中印关系
一、筚路蓝缕
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为印度历史文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为将东亚研究提升到学术高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当时的副校长阿修图什·穆克尔吉 (Ashutosh Mukherji)先生意识到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印度并没有能胜任的中文教师。因此,该大学委派一位曾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巴克齐 (Prabodhi Chandra Bagachi,即师觉月)去往河内、日本和法国,以使他更加完善其专业。师觉月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四卷本的《印度与中国丛书》中。前两卷以将近800页的篇幅,细致地梳理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中文译介。后两卷则对中国古代两大汉语-梵语辞典进行了批评研究。这两大辞典编纂于唐朝时期,供佛教学者使用。师觉月的著作为印度学家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其著作仅被译为英语。
1921年,伟大的诗人和教育家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创立了国际大学(Visva-Bharati University),在组织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该机构被作为东方人文大学来组建,而中国学研究则在课程设置中占据突出的地位。访问教授赛勒维恩·列维(Sylvain Levi)首开中国佛学研究的教学。1924年泰戈尔访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的研究。1937年,在谭云山教授和泰戈尔的其他中国朋友的帮助下,一个相对完备的中国学研究学院,即由谭云山主持的 “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a)在国际大学落成。通过各种资源在中国搜集到的图书,使一个比较大的中文图书馆得以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于 1939年访华,1942年,中国国家首脑①访印;此次互访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抗战期间中国不少大学迁往重庆,为大量中国学者出访印度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印度的出现激发了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兴趣。就在那时,浦那弗古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成立了一个小的中国研究中心。巴帕特(P.V.Bapat)博士和戈哈理(V.V.Gokhale)博士开始了对巴利文、梵文和汉文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
1944年,重庆印度领事馆总领事梅农(K.P.S.Menon)首次为大量印度学生赴中国学习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政府交换项目安排之下,一些印度学者来到重庆,同时,同等数量的中国学者前往印度的大学学习。日本投降后,梅农作为独立后印度的第一任大使回到中国,为印度学生赴中国进行专门学习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印度政府将八名印度学生送往北京自费学习,北京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全面的学习条件。其中三名艺术专业的学生师从中国著名的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学习绘画。1948年,在派送第二批学生去往中国之前不久,印度政府向北京大学派驻印度历史文化讲座教授两年,并委任师觉月协助北京大学建立梵语和印度学研究系。师觉月在京两年期间,也为不少印度学生在北京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1950年,国际大学的中印研究重新整合,与印度研究并入一个研究中心,由师觉月教授主持;中文教学仍由谭云山主持②。
印度文化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也推动了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该学院由著名学者罗怙毗罗(Raghuvira)博士创立并担任第一任院长。罗怙毗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洛克什·钱德拉(Lokeshchandra)博士,前国会议员继任院长职位。这一机构旨在出版所有在东方发现的印度文学脚本,既有藏语、汉语、蒙古语、日语等语言的原本,也有译本。许多外国学者应邀在此机构工作。
1954年,中印签订通商和交通协定③。此后,中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继之中印学者的往来开始正常化。尽管或有中断,总体趋势是持续的。这进一步推动和鼓励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进程,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
二、中国佛教和中印文化研究
在印度国际研究院 (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即现在的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建立之前,学者们所从事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中印佛教研究方面。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师觉月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一些具有梵语和巴利语基础的学者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略。比如周法(fa chow)的 《四分律 (Dharmaguptaka-vinaya)之四波罗夷法(parajika)和巴利经分别(Suttavibhanga)初探》;师觉月的 “《〈撰集百缘经>(Avadanasataka)及其中译本校注》;萨提拉衍·森(Satiranjan Sen)的《两部汉译药典论》。师觉月的《帕坦(Pathan)时期中国与孟加拉邦间的政治关系》,巴帕特的 《佛陀口述的〈义足经>(arthapada-sutra)》,载国际大学年刊第一卷,同刊第六卷还发表了萨斯特利(N.Aiyaswami Sastri)的《龙树(Nagarjuna)之〈十二门论>(Dvadasamukha Sastra)》。在国际大学的赞助之下,大量的研究也在筹备。包括拉马南(Ramanan)博士在汉文资料④的基础上所作的 《龙树的哲学研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云华的(Y.H.Jan,RanYunhua)的《中国佛教编年史》(国际大学)和《中国佛教的变迁》(以宋代的研究著作《佛祖同参集》为基础,未出版论著,国际大学)。师觉月所译的慧立⑤撰《释迦方志》,在其去世后,也由国际大学出版。国际大学的另外一位学者,B.D.穆克尔吉(B.D.Mukherji)研究了“德国佛教律宗(Vinaya School)中的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a)”。
从历史角度来看,N.C.赛恩(N.C.Sen)的“论唐王朝时期的印度和克什米尔”值得一提;H.P.雷易(H.P.Ray)则在汉文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15世纪的印度;谭中的“印度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较重要,属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ICSSR)课题(未出版)。
这里必须要强调国际大学的谭云山教授的非凡贡献,他放弃了在中国待遇优厚的工作,与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共同致力于加强喜马拉雅山双子——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联系。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创建了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中国研究院”,描述佛陀生平的壁画以及从中国的不同地区搜集而来的有关佛教、历史和其他经典的千余珍贵作品将整个建筑装饰得十分宏伟绚丽。他的贡献将被所有热衷于中国学研究的学者铭记景仰。
在谭云山的鼓励下,很多学者开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其中,国际大学奥利雅语(Oriya)与梵语系的布拉赫拉·布拉坦 (Prahla Pradhan)教授,对古汉语十分精通,并利用中文材料进行佛教研究及印度文字起源的研究。后来,该大学的布拉帕特·穆克尔吉(Prabhat K Mukherjee)教授,也即泰戈尔的传记记者,随赛勒维恩·列维学习中文,并著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传播》,目前该书印刷本已经失传。
三、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
随着50年代印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系的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纬度更充实了中印研究。此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涉及到诸多主题,其中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对印度革命的影响;欧洲人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曲解及对“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误解的颠覆;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家康有为与印度宗教-社会改革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即辨喜)的比较研究;对1949年之后第一个20年知识分子的研究;对中印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中国的科学政策、安全与防御及工人在管理上的参与等等方面的研究。
印度学者在对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方面的兴趣似乎并不显著。一些文学研究者虽然从英译本翻译了一些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但对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始于A.N.泰戈尔(A.N.Tagore)对中国五四运动后不同文学思潮的研究⑥。然而,在尼赫鲁大学举办鲁迅百周年纪念庆典时,认真的尝试是显而易见的。来自印度各邦的学者、文学家,来自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学习中国语言的学生递交了30余篇研究论文,内容不仅涉及到鲁迅作品的不同方面,也论及鲁迅的现代影响。H.P.雷易博士对鲁迅与萨拉特·钱达·查特吉(Sarat Chandra Chatterjee)的比较研究在尼赫鲁大学语言学院学刊(Journal of the School of Languages,JNU)上发表⑦。
四、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研究成果述评
无论是尼赫鲁大学的东亚研究系 (在SIS,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中国语言课程(在SLL&CS,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院),还是德里大学的中国与日本研究系,其存在历史之久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目前所有的这些研究活动都集中在德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现存的资料,尝试对中国学研究状况进行一个概观。
德里大学中国与日本研究系至1987年已经产出6篇博士论文⑧。其中,1篇关于中国与世界,4篇涉及到国内政治发展,1篇则着眼于中国的科学政策,也是印度的整个当代中国研究历史中唯一一篇此类论文。但是副博士论文(M.Phil)⑨却表现出较为多样化的特征。在28篇论文当中,有5篇聚焦于中国与世界,其余23篇均涉及到国内发展,其中论及经济问题的有4篇,以中国教育为主题的有2篇,关于农业的有3篇,还有1篇着眼于妇女研究。
关于德里大学的资料,谭中的博士论文不包括其中(《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立场》,成文于德里大学历史系)。德里大学有一些教师在国外修完博士学位,如 K.P.顾卜塔(K.P.Gupta)(康有为与辨喜研究),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中国革命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斯里玛蒂·査克拉博蒂(Srimati Chakraborty)(中国与纳萨尔派⑩)等。
在尼赫鲁大学,我们搜集到自1961年(或许第一篇是在以前的ISIS,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社会科学院)至1992年副博士与博士论文的资料。
在18篇博士论文中,6篇涉及到中国国内的政策,包括1篇探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的论文和一篇论及“四人帮”的论文。另外有几篇立足于编年史研究,还有1篇是关于西藏的宗教和政治;其他的均涉及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到70年代后期,副博士学位引入印度。第1篇副博士论文完成于1972年。至1992年共有70篇论文通过了审核。其中有26篇论述国内发展,4篇论及社会主义,其余则全部涉及中国与世界。
在以中国的发展为主题的论文中,2篇谈到西藏问题,3篇论及台湾问题,1篇着眼新疆问题,只有1篇涉及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1928~1937)。4篇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防御事务,4篇论及中国经济,并且每一篇都提及农民和教育。2篇以防御为主题,10篇以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为主题,除此之外,有4位学者着眼于中印关系 (1951~1955,1969~1979,还有1篇牵涉到达赖喇嘛的因素),1位学者关注中印边界问题,7位学者分别关注中国与其他邻国,如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1970~1975)、日本及越南的关系。其余学者则着眼于宏观国际关系方面,如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中国与不结盟运动、中国与西方国家等等,还有1篇论文涉及到印度的西藏政策。
五、评 价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在博士预科阶段,学者们关注了这一领域的不同方面,并且有一个多样化研究趋势正在萌芽。但是当他们涉足某些领域时,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比较复杂晦涩的中文资料,于是他们的兴趣开始集中于某些特定主题。这些主题或许在新闻业界被广泛地探讨,或者具有一定的时事价值,因此往往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种趋势的出现或许与缺乏原始资料有关。在利用中文原文第一手资料或者即便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二手资料方面,从预科博士阶段开始直至博士阶段越来越贫乏。在印度诸大学的论文中,鲜少有搜集了原始资料的痕迹。尼赫鲁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在结束5年硕士课程之后才可以开始博士课程,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中文语言学家,并会在未来几年里展示出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德里大学也开设了中文强化课程。这两所大学的学生有机会到中国进一步深造。如果他们不从原始资源中利用一手的信息,那就前功尽弃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几乎都由这两所大学担当,但目前他们的研究趋势使一些问题凸显出来。比如缺乏当下最急需的导向和合作等等。举例来说,中印关系,其悠久的历史,近十年的经历,两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等这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充分重视。过于强调政治,包括国际关系,只能导致理解上的失之偏颇。我们还应当充实这些研究,必要的时候,将触角探入社会学、经济、历史的层面,综合这些角度来全面地认识这个国家及人民。然而这些却完全被忽视了。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文素材极少被用于研究中,而且,确保学生扎根语言和历史的任务也没有给予充分强调。
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分类研究项目中,有一个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充分尝试对中印边界争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加尔各答大学的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博士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唯一学者⑪。事实上,一些外国评论家和记者已经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当我们发现一些博士级别的高级学者对中国关于其他地区的外部政策表现出过多的兴趣,而忽略了与我们最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会尤其感到不安。
对于1949年之后建立的中国与日本研究系,我们认为不应当仅仅归因于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出现。这种片面的观点已经导致了某些研究过剩,不管重复非印度学者的研究,还是保存二手资料,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于中国迅速变化的时局。而强调研究的意义有助于双方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互相理解发展实践、教育及其他领域的经验。人们将更倾向于关注更加基本的和实质性的主题。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表现出对汉学研究的兴趣。他们从事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并且将自己国家的学者送往中国大陆或台湾,进行语言强化培训,以便深入钻研中国学研究的不同精彩方面。我也曾梳理了明清时期欧洲人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从鹿肉、鹿皮、龟壳、货贝、燕窝等方面的贸易到肉桂贸易、锌贸易,以及其他商品贸易都在兴趣范围之内⑫。
六、一些新的维度
近期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中印关系史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1.我们可以根据中文、藏文和其他一些资源重构印度整个古代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历史。通过参考中文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古老名词如印度(Hindu)、梵(Brahma)、恒河(Ganga)的起源;并且为《往世书》(Purnans)和《本生经》(Jatakas)中地理政治方面的记载提供佐证。
2.在南印度朱罗(Cholas)王朝势力兴起的时候,中印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约从1015年起,王朝的历史学家和中国官员及旅行者的个人著述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记载。比如,朱彧撰《萍洲可谈》(1119 年);周去非撰《岭外代答》(1178 年);赵汝括撰 《诸蕃志》(对域外人士的记载,1225年);汪大渊整理了其于1330~1349年间亲历海外时的笔记,并在1405~1433年间随郑和下西洋的译员(通事)及官员所记录的15世纪旅行见闻的基础上,所撰的 《岛夷志略》(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简要记载,1350年);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岸的整体概览,1433~1435年)是现存郑和下西洋基本文献中最著名的一部,但并不是最好的一部。继最后一次航行90余年之后,1520年黄省曾所撰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 《西洋朝贡典录》(记录了西洋即印度洋国家的朝贡情况),因其记载最为细致真实,而堪称典范。该书连同另外的旅行见闻录,如巩珍的《西洋藩国志》(记录西洋异域各国情况,1434年);费信的《星槎胜览》(对海外诸国的整体概览,1436年,费信与马欢都曾造访印度)对沿海诸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反映。巩珍在很大程度上与马欢的论述是一致的,而费信和黄省曾则更多地为我们展现出很多珍贵的资料和有趣的史实,这些是其他著作所不具备的。通过其他的一些记载,我们还可以得到关于15世纪早期印度洋进出口贸易的更加详尽的信息。
3.中国把印度洋称为“西洋”。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获得与中国的关联成为一种力量迅速地在东南亚地区发挥影响。这个概念也产生了许多有趣的副作用,值得我们更为详细地研究中国在印度洋的地位。中国将东南亚国家视为被保护者,有时候甚至视其为封地。比如境外的国家越南。
4.我们已经发现,随着一些小而强大的国家在海岸地区或边界之上出现,中国对次大陆的兴趣也逐渐增强,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5.“纳贡国”体系相对于印度而言,是迄今为止印度学者从未认真加以研究的主题。纳贡国系统与境外国家在本质上截然不同。两种体系之下,政策执行的立足点也截然不同。15世纪的文献资料显然确定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中国永远不会将印度各邦视为其藩属。
6.根据佛教文献(主要是梵语佛教文献)研究中印关系,极有可能发现迄今为止仍然未知的,却具有启发性的资料,涉及到古代印度及其科学、天文学、医学、历史、语言发展、印度-雅利安语言的语义学、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许多其他的知识门类。例如,印度北部、西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历史地理学在中文记载中可以觅其踪迹。这些记载大多冠以佛教文献之名,而内容是世俗的,关系到印度学的方方面面,如雕塑、文学理论、修辞学、韵律学、音乐等等。
7.有关中国医学的论述大量引自西洋文献,所指的是印度和波斯。但是就其名称和其他一些内容看来,这来源就是印度。这些研究能平息那些对印度之于世界的贡献的质疑。单就音乐来说,就有数百种拉格(ragas,曲调)或被直译或被意译过来,具有了中国化的形式。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中国吸收了这些曲调,使其本来就已十分繁荣的音乐学更为丰富。在阐明古代韵律的奥秘和探索印度音乐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辞曲令音乐学家流连不已,比如,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的叙事诗《长恨歌》(永恒的情殇)中提到的《霓裳羽衣曲》,我们还曾在其他出处中找到《春莺传》、《苏幕遮》、《摩诃》、《兜勒》⑬等神圣美妙的音乐。这个课题非常有趣,云南大学的吕昭义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力图着眼于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应当关注的其他研究方向,并且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初资料逐渐成为从事区域研究的必要条件。
七、对现有一手资料的归纳
令学者们最为苦恼的问题就是无法确切掌握现有资料。这大多是由于他们和图书馆及档案文件的管理者之间缺乏沟通。大部分图书馆的检索系统都比较原始和混乱。大多数情况下语言部门的职员既无法为学者提供指引又无法提供中文收藏的详细信息。
因此,向汉学家和年轻学者提供一份有关东亚方面专门的藏书报告非常必要。报告中应包括德里大学中国与日本研究系、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和国家图书馆亚洲文会等机构中此类专门图书馆及藏书。这在本质上来讲,是旨在对中文和中印研究的学生有所助益的初步探索,也意在激发其他相关学者的兴趣。
注:
①此指1942年蒋介石访印——译者注。
② 见师觉月编,李华德(W.Liebenthal)校:“印度的远东研究”载《远东研究季刊》卷八,953-954,第112-114页。
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译者注。
④应指仅存的汉译《大智度论》——译者注。⑤应为道宣——译者注。
⑥并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战:1918-1937》一书。⑦第一卷,1990年。第164-182页。
⑧ 这些数据见马诺哈尔(Manohar Lal)的《中国报告》,第二十四卷,第4期,第481-85页。
⑨ M.Phil,研究式硕士,即Master of Philosophy,一般学制为两年。亦常被视为修读博士课程的一部分。校方对于申请博士课程的学生常会先接受其为M·Phil学生,若其研究绩效良好,则同意该名学生修读博士学位。因此,译者将其译为副博士——译者注。
⑩Naxalite,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译者注。
⑪卡鲁纳卡尔·古普塔博士于1974年出版了 《被隐藏的边界》,着重研究l947年印度独立后的中印边界问题——译者注。
⑫所有的这些论文包括作者对15世纪孟加拉与中国之间纺织品贸易的介绍,已由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的南亚学会出版。出版时的标题是《亚洲海上贸易中的商业中心、商品和商人,约1400—1750年间》,第141号。(斯图加特,1991年。)
⑬这是指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两首曲子,乐官李延年在其基础上重新创作了二十八首乐曲——译者注。
【责任编辑:来小乔】
Abstract: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century,India began to make contact with,explore and spread the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Since then,under the common efforts of the Chinese and Indi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the Chinese studies in India have further developed.The Buddhis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hot areas.Indian scholars have also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economy and foreign policies.In addition,some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began to emerge.Nevertheless,the research angles still need to be explored,and the lack of first hand materials is probably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to be resolved in the present Chinese studies in India.
Key words:India; Chinese studies; Sino-India relationship
An Over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India
Haraprasad Ray
G 04
A
1000-260X(2010)06-0010-05
2010-10-15
哈拉普拉萨德·雷易,印度汉学家,曾就职于尼赫鲁大学(新德里),后任加尔各答亚洲学会高级会员。
*译者简介:蔡晶(1981—),女,河南驻马店人,北京大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南亚文化及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