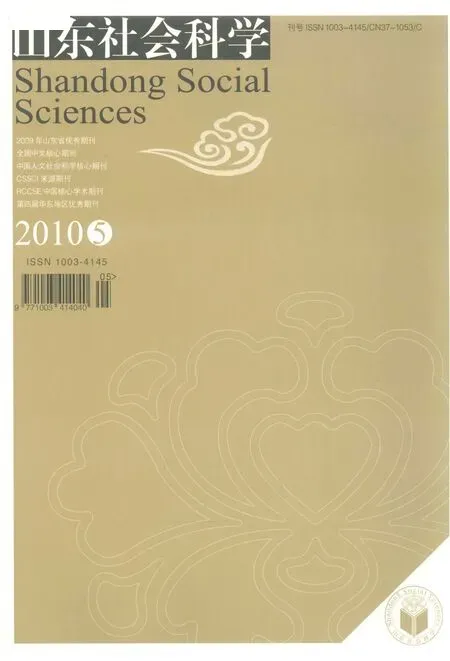苏联为什么进行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马龙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苏联为什么进行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马龙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社会学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苏联在 20世纪 20年代末到 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深入贯彻 1925年俄共 (布)文艺政策决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重温这一理论争论,对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准确领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对观察、分析并正确认识当前现实的思想理论斗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庸俗社会学;苏联史学;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社会学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苏联在 20世纪 20年代末到 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深入贯彻 1925年俄共 (布)文艺政策决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过去,中国思想理论界对这一斗争的研究和关注是不够的,今天重温这一理论争论,对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准确领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对观察、分析并正确认识当前现实的思想理论斗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所谓庸俗社会学,按照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 М.利弗希茨所做的概括,它“主要是在史学、艺术批评、文艺理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所做的一种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更广义些说,庸俗社会学就是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的真正损害,并导致错误政治结论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解;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漫画化”。①Л и ф ш и ц Ми х.С о б р а н и е с о ч и н е н и й. в т р е х т о м а х. т.2,М.,1986.- С.233.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庸俗社会学就是把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形态,只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作为经济和技术作用于一定阶级利益的直接后果,进行简单化的、直观的解释。或者按照《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庸俗社会学观点就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因而往往把有关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做出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②《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第404页。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理解,往往把社会阶级看作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疑应该对社会现象坚持阶级分析,但应该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不是戴上“有色的阶级眼镜”,把所有的一切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涂上阶级性色彩;像苏联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穿上阶级的衣衫。或者像庸俗社会学派的文艺学家那样,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而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待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伟大艺术家所做的评价那样。
在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里,代替真理位子的是集体的经验或阶级的意识,实际上他们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个性主体转变到了阶级主体。庸俗社会学像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潮一样,渗透着极端的能动论。历史主体的非理性的自我表述,在庸俗社会学体系里,就变成了阶级的自我表现。不言而喻,这种主观主义往往掩饰在党性的词句之下,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党性的一种歪曲。
一般的庸俗社会学也大讲并凸显阶级斗争,但它的阶级斗争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它更接近于尼采笔下的强者与弱者的厮杀争斗,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学者所描写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某种类乎兽性的搏杀。庸俗社会学把阶级斗争变成了各种自私自利的社会势力为争夺一块面包,为争夺一块土地而进行的种族厮杀,这本身就不是对待各个时代基本阶级矛盾的态度。
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 М.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①Л и ф ши ц Ми х.С о б р а н и е с о ч и н е н и й. в т р е х т о м а х. т.2,М.,1986.- С.238.
把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运用在文学艺术中,就是以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冒充马克思主义,用以解释作家的艺术创作和各种文艺现象。文艺创作被看作直接地、直观地、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地决定于经济;每一个作家都一劳永逸地被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好像要永远被牢牢固定在自己阶级的属性上,在所有的作品中注定是只能描写自己,只能表现自己本阶级和社会集团。20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В.Ф.彼列维尔泽夫,就是用这种理论解释作家及其艺术创作的。
庸俗社会学注意的焦点,不是分析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所体现的客观艺术价值;它的主要兴趣是集中于受体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在庸俗社会学看来,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预设的象形符号,其意义是以接受者为转移的一个可变量;每个时代、每种社会、每个阶级,都会把自己独特的意涵灌注进受体阅读的字里行间。一切艺术作品和其他精神文化现象,其存在状况无非有两种:或者是,它们都有其本身客观的核心内容,而受体在千变万化的感受和理解中仍然保持其核心内容不变 (因为它们以客观的现实形象为基础);或者是,社会科学丧失了衡量真理的任何标准,无法区分比如艺术真实和其他假象,就连对一些写手们制作的赝品,低俗的读物或者文牍主义的连篇空话,也无法对它们的真伪加以区分。在庸俗社会学活跃的社会环境中,艺术作品和精神文化现象只能处于后一种生存状态。
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对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及其活生生的呈现,而是把社会形态当作抽象的公式加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在学术界一度有过的所谓历史学科的危机,在历史教科书和史学著作中充满着抽象社会学公式的说教,而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
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阶级斗争的概念,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向农民无限制地挖粮征购,农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抵制反抗,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这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进行庸俗化,把“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进行压制甚至镇压、迫害的有力工具,这是有违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庸俗化现象。
庸俗社会学把阶级规定性的原则用来解释社会意识,往往将其扩大化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被做了绝对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应用到社会上,唯成份论成了谈人论事的唯一标准,其恶性发展,就导致到反动的“血统论”。庸俗社会学反映在政策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是旧文化的载体,因而对他们采取排挤、打击的政策。把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不加具体分析,一概视为剥削阶级的产物,采取统统排斥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或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密切相关。
二、庸俗社会学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相当流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障碍
庸俗社会学作为一种扭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庸俗化的思潮和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几乎贯串始终的一条又粗又长的思想线索。
早在 19世纪 70—80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 19世纪 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95页,第692页,第698页。
在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把“唯物主义”一词变成了一个套语,当成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就以为万事大吉。恩格斯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决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②《马 克思 恩格 斯选 集》(四 卷本),第4卷,人民 出版 社 1995年 版,第695页,第692页,第698页。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曾表示他与马克思也应对这种情况承担部分责任。他在《致约·布洛赫》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惊人的混乱……”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95页,第692页,第698页。恩格斯在晚年一系列书信中表明,当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庸俗化的情况,在他看来已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④这 些书信包括《致约·布洛赫》(1890年 9月 21-22日)、《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 1月 25日)、《致弗·梅林》(1893年 7月 14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 10月 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庸俗社会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块的。这股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早就通过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形成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粗暴歪曲传播到了俄国。由此,产生了巴枯宁对文化的急进主义批判。他是把文化作为同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贵族习气加以痛斥的。他在当年的言谈,大有毁灭文化的气焰。此外,特卡乔夫在 18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文章,也把经济唯物主义与本瑟姆⑤伊列米亚·本瑟姆(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对后来都有相当影响。
庸俗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实证主义观点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有时也受到新康德主义成分的侵蚀。一个应当注意的事实是,就连常常同庸俗化保持距离的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也能窥见 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的蛛丝马迹。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往往将文化史解释为由社会决定的带有必然性的一系列心理精神状态,而这种必然性就像苹果树要结苹果,梨树要结梨子一样,往往被说成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
普列汉诺夫的片面性,表现在把科学的文艺批评的任务仅仅限定为从发生学、起源学方面去研究艺术现象,而不允许在文学中用通常标准的方法进行艺术批评。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就是,普列汉诺夫力图“千方百计强调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客观主义,因此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即主观意志的创造性方面注意不够”。⑥Н. А. Т р и ф о н о в.А.В.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 ис о в е т с к а я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а.M.,1976. —С.532.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同苏联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 В.Ф.彼列维尔泽夫有着共同之处。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左”的庸俗社会学思潮主要由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派”集团所代表。依附于波格丹诺夫一派的,是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他们就是 М.波克罗夫斯基、В.弗里奇和 В.舒利亚季科夫等人。他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曾起过较大作用,但并不总是正面的、积极的。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获得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在苏联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得到的迅速广泛传播,以及部分旧知识分子对它无奈的适应和服从,进一步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使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给社会主义文化造成严重危险的现象。在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推动下,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在文化建设方面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达到了特别有害的地步。庸俗社会学采取荒唐可笑的形式,造成了巨大破坏性后果。它鼓吹打倒所有剥削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摈弃所有文化遗产,取消过去的学校,把过去官方的历史学公式完全颠倒过来。这样一来,伪皇第米特里成了当年那个时代革命力量的代表,而具有进步意义的彼得的改革,反而遭到了粗暴的否定;十二月党人非但不是捍卫人民利益的英雄,反倒成了地主兼粮食贸易商的代言人。在庸俗社会学派看来,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遗产都丧失了艺术价值,前者不过是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后者无非是与高等贵族沆瀣一起的中等贵族的代表;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是没有什么人类共同的珍贵艺术价值可言的。后来,“拉普”①即俄文“Р А П П”,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的简称。又接过“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某些极“左”观点,进一步以变化了的词句宣扬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在 20世纪 20—30年代,庸俗社会学为摒弃文化遗产,为各种极“左”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环境。这种极“左”的思想形态,把所有一切都涂抹上了阶级色彩,从宣传消灭过去时代的音乐,到把艺术溶入生产和生活的理论 (“列夫”②即俄文“Л е ф”,是“左翼文学战线”的简称。马雅可夫斯基为其首领。的主张),各种论调往往五花八门,离奇古怪。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片面性所引起的消极后果,造成其追随者进一步将其发挥、放大了他的失误,而出现庸俗社会学倾向;一是由波格丹诺夫受到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③约瑟夫·彼得楚尔特: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门徒,他们师徒一块都受到列宁的批判。社会学的影响,而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应该说后一方面是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倾向。
莫斯科大学教授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可以说汇合并承袭了这两股源流。苏联上世纪 20年代有一系列颇有名气的文学史专家,比如 П.Н.萨库林和 П.С.柯根等学者,就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点。以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这个庸俗社会学派,培养出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有才华的学者。这使他们的理论在苏联理论界和文艺界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使 1928—1930年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并未能完全铲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数十年间在苏联思想理论界一直存续了下来,而在苏联学校教育传统中保持得最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 80年代。④М. М. Г о л у б к о в.И с т о р и яр у с с к о й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н о йк р и т и к иХ Хв е к а(1920—1990-е г о д ы).M.,2008. —С.168.
庸俗社会学思潮在上世纪 20年代最盛行时,实际上几乎成了苏联文艺学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潮。当时,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从彼列维尔泽夫学派到“列夫”(“左翼艺术阵线”的简称),从史学到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都具有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口号,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其他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则与“无产阶级文化”无缘,只配受到排挤和打击。“列夫”则鼓吹“生产艺术”,认为惟有这样的艺术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拉普”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基因,主张在完全清除“旧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他们都倡导“集体主义”艺术,主张生产和艺术相溶合,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企图在文化艺术界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俄共的地位。“拉普”还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理。主张“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革命那样”,⑤П р а в д а,1 ф е в р а л я1925г.用类乎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其一派的领导权。“拉普”比“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加注重磨砺阶级斗争的“利刃”,主张在文艺斗争中要“果敢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要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⑥О ч е р к ии с т о р и ир у с с к о йс о в е т с к о йж у р н а л и с т и к и(1917—1932),М.,1966,С.395.这段话,对‘拉普”思想斗争的方针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他们对待来自旧时代的“同路人”作家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则处处袒护,实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
“拉普”宣称,俄共 (布)党还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他们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党员作家组织的纲领,应该成为党的文艺纲领,他们的政策应该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基本正确代表党的文艺政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的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 (被列宁委任主办《红色处女地》的负责人)沃隆斯基,为了捍卫党的文艺政策,对“拉普”进行了反击。这一下捅了这个“左派”的蚂蜂窝。“拉普”适时利用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形势,对沃隆斯基大肆反扑,一下搅乱了文艺阵线,混淆了党的文艺政策,于是,迫使党不得不成立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
在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领导人布哈林和负责国家文化教育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主持下,为俄共 (布)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草案。草案于 1925年 6月 1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为反对以“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思潮在文艺阶级性问题上的简单化观点,为贯彻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方针政策,《决议》特别载入了针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一段话:“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①《“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317页。
我们知道,无论“无产阶级文化派”,还是“左翼文艺阵线”和“拉普”,其极左的文化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庸俗社会学。这样,在 20年代中后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决议、纠正极左错误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庸俗社会学派的抵制和干扰。
事实正是这样。大约在 1926年或者是 1927年,在一次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当讨论到有关中学文学教学特点的问题时,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列维尔泽夫同卢那察尔斯基发生了“直接冲突”。接着,在1928年 1月 (不是像在《文学百科全书》中说的那样,在 1929年 1月②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н а яэ н ц и к л о п е д и я,т.9. М.,1935,С.502//Н. А. Т р и ф о н о в.А.В.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ис о в е т с к а я 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а.M.,1976. —С.527.)召开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当时,以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为首的庸俗社会学派是掌握相当权力的。从 1922年建立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艺术学部时起,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就是该学部的正副领导人;1925年改组后,他们两人又分别担任学部主席和学部秘书。他们作为老党员学者,在革命前就发表多部著作,一向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他们有一批弟子追随左右,形成了这个日后被称谓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当彼列维尔泽夫与卢那察尔斯基发生激烈争论后,他和弟子们为维护庸俗社会学派的观点,在 1928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们共同发行了第一个《文艺学》文集,在发行文集的同时,还在同舆论界的多次见面会中发表了他们的理论纲领。而此前不久,在高校教师的一个莫斯科会议上,彼列维尔泽夫还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总结性地全面阐述了他们的思想。此外,他还在另一场合向听众讲解,艺术形象的阶级制约性是通过什么机理,怎样具体发生的。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彼列维尔泽夫是一个活跃、固执并带有进攻性特点的学者。他利用当时在舆论界的名气和权威地位,在其坚持的观点上是丝毫不肯退让的。
这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派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展开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斗争。
三、苏联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始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维护 1925年《决议》的重大原则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 1928年 4月 30日至 5月 8日召开的第一次“瓦普”③即俄文“В А П П”,是“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的简称。代表大会上,针对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派的错误,做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状况和任务》的报告,④А. В. 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С о б р а н и к е с о ч н е н и й. Вв о с ь м ит о м а х. т.8,М.,1967. С.7-18,8.拉开了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序幕。
卢那察尔斯基从分析苏联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出发,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地位、使命、特点和具体任务。他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该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学精神”;⑤А. В. 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 С о б р а н и к е с о ч н е н и й. Вв о с ь м ит о м а х. т.8,М.,1967. С.7-18,8.他特别使用“科学社会学”一语,就针锋相对地同“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
接着,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进行怎样的“科学社会学”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的、最带规律性的经济关系,首先是劳动的形态。在广泛考察某个时代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努力给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⑥А. В. 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С о б р а н и к е с о ч н е н и й. Вв о с ь м ит о м а х. т.8, М.,1967. С.8-9.
但是,他又概述、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当问题涉及到某一个别作家或作品的情况时,倒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考察根本的经济条件,因为这里特别突显出了一个恒常起作用的原则,……这就是艺术作品只是在非常微不足道的程度上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们依存于生产方式是经过其他中介环节而发生作用的,这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和在阶级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心理。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该作家作为表现者的那个阶级的心理,或者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其他各阶级对作家影响而生发出来的某些复杂成分;这也是必须予以关注并进行分析的。”①Г. В. П л е х а н о в,С о ч и н е н и я,т.10,С.295-296.// А. В. 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С о б р а н и к е с о ч н е н и й. Вв о с ь м ит о м а х. т.8, М.,1967. С.9。
显而易见,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针对的是庸俗社会学观点,并一一进行了驳斥: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卢那察尔斯基则提出了“中间环节”论;庸俗社会学把一切文学现象都归结为“社会阶级制约性”,卢那察尔斯基则一一做了具体的辩证分析。他没有把作家及其作品钉死在该作家出身的阶级机体上,而是看到了艺术阶级性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正是俄共 (布)中央在 1925年《决议》中所指出的重要原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②《“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317页。
卢那察尔斯基针对庸俗社会学派分析一切文学现象都从经济形态和“社会阶级制约性”出发的庸俗机械论观点,提出分析作家及其作品要从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并据此提出了评价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标准问题。他反对艺术风格的“阶级制约性”观点,认为“绝不能否认研究文学形式的独立任务”:“事实上,作品的形式不仅是由该作品的内容决定的,而且是由若干其他因素决定的”。③А. В. 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С о б р а н и к е с о ч н е н и й. Вв о с ь м ит о м а х. т.8, М.,1967. С.10.在这里,他当然是指文学形式 (包括风格)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卢那察尔斯基对庸俗社会学所固有的一种方法论十分不满,就是把文艺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确定文学作品的社会根源,仅仅归结为去说明它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派别以及阶级发展状况。他认为,“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它隐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动机,它教育人们些什么,它的导向是什么……它在其产生的那个时刻具有什么地位,以及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富有生命力,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是有生命力的……而如果这是类乎像《战争与和平》或者普希金那样的生命力,那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善还是恶,而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善,表现在何处,又是什么意义的恶,其表现何在?”④原 载《劳动学校的国语和文学 》1928年第1期 ,第70页 ;转引自 Н. А. Т р и ф о н о в.А.В.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ис о в е т с к а я 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а.M.,1976. —С.528.卢那察尔斯基在批评的实践中,就是这样考察文学作品的。他不仅考察作家和作品的社会阶级特质,还考察其形象性格的个性特征;不仅考察作家作品所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内容,而且考察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人们中间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即人类所共同珍视的真、善、美的价值。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待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极其慎重地加以对待。
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报告中,批判的锋芒直指庸俗社会学派的整个理论纲领。这个报告在“瓦普”大会上发表后,接着立即于同年 6月在其机关刊物《文学岗位》和《新世界》两家大型刊物上刊载。这样,这位教育人民委员,正像他本人所说的,便在“并非听命于任何人的”⑤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н о е н а с л е д с т в о,т.82.,C.76//Н. А. Т р и ф о н о в.А.В.Л у н а ч а р с к и йис о в е т с к а я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а.M.,1976. —С.526.的情况下,倡导并发起了同庸俗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这场理论斗争。
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是在 1929—1930年全面展开的。在 1929年初举行的一次苏联语文专家会议上,苏联文化界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波梁斯基,也加入了同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论争。接着,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相继展开了这一批判,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学院语文系举行的专门讨论会上,也发生了同这一庸俗社会学学派的争论。第一阶段批判的高潮从 1929年一直持续到整个 1930年。
其间,经过大体一年左右的间歇,从 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再次展开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这一阶段的批判一直延续到 1936年。如果按阶段划分,这是继 1928—1930年第一阶段论争之后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批判。正是在这个阶段,先前方向基本正确的学术批判被扩大到政治领域,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开始着眼于上纲上线,政治论罪,而忽略了理论是非本身的厘清和划分,因而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虽持续数年之久,但理论是非并未彻底弄清,所以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不仅在直到上世纪 80年代的苏联,就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时期都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
以上就是从 20年代末到 30年代中期,苏联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大体情况和过程。
四、对苏联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当代认知
苏联所进行的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那么,当代应当对它如何认知并做出正确评价来呢?
这场批判在苏联上世纪 20年代末至 50年代初的无数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批判中,应该说是罕有的、极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辩论和理论斗争之一。这一理论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对庸俗社会学最集中、最有成效的一次打击,它对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灭了庸俗社会学派的气焰,阻止了庸俗社会学的蔓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由于这一斗争主要是在苏联文艺学领域进行的,所以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然而,这次理论批判的进程也经历了曲折。在争论的第一阶段 (1928—1930),进展是顺利的。卢那察尔斯基把论争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允许论敌答辩,没有影响他们继续发表文章和著作的权利。这一正确的方针使斗争避免了扩大化,把重点放在了分清理论是非上,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但是,在批判的第二阶段 (1932—1936),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理论斗争为苏联最高领导所利用,被用来打击政敌、改写党史、树立个人崇拜的目的,这样就把原本的学术论争扩大化,扭曲成了政治批判,因而走上了忽视厘请理论是非的错误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清算,造成理论是非厘清得很不彻底 (特别是在文艺学以外的领域)的状况,为日后留下了遗患。
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清算的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语言学领域。在 30年代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人类交际工具——语言,宣布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大肆宣扬语言的阶级性。这使庸俗社会学在语言学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没有稍显收敛的迹象。此外,苏联这个时期不只正确地宣传中小学人文课程的阶级性,还把阶级性特征扩大到化学、物理等自然知识课程领域,赋予自然科学以阶级性。语言学的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 50年代初,而学校教育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则一直延续到 80年代。
苏联在学校教育中存在这种倾向,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以米丁、尤金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一直宣扬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直到 40年代末还把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苏联批判庸俗社会学的不彻底性,不仅长期侵害到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和教育界,也严重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即上世纪 50—70年代的思想理论界。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着重在文学理论界对庸俗社会学进行批判,但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在整个社会上,在庸俗社会学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是不够的,因此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和社会上有时还抬头,沉渣泛起,余音回响。近年一股否定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噪音,应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因此,在学术理论界以至全社会进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必要的补课,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有必要的。
庸俗社会学既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加之因其长期存在而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危害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错误理论及其倾向的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地同它进行斗争。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伟大工程的建设中,需要注意纠正两方面的理论倾向:一是纠正从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歪曲和修正;二是纠正从左的方面,即庸俗社会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扭曲和侵害。离开了同这两种理论倾向的斗争,就会极大地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坚持。
附:关于庸俗社会学和庸俗社会学派的译文两篇
编译者的话
由于马克思主义所达到的空前科学成就,由于其博大精深以及它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和感染力,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思想界登上历史舞台之时起,它就以空前强大的磁吸力,吸引了欧洲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广泛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各个思想阵营的人们,从右翼的资产阶级学者到左翼革命家,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到投机革命的半吊子文人,都一无例外地被吸引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上来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人是当作革命的思想理论指南,来认真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有人是作为思想敌人,为讨应对之策而从事研究的;也有人是迫于它的影响力,为附和、投机而研究它的;更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为装潢门面,或吓唬他人而为之的……无论抱着什么动机和目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恢弘博大,义理精深,不少人是难于一时吃得透、弄得明的。更有人或者由于动机、立场暧昧尴尬,根本无法理解其精义内涵;或者所受教育不多,为文化素养所限,对马克思主义往往发生误解、曲解,所以歪曲义理之处难以胜数,而出现偏差、错误最多的,往往就是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犬儒化、经济化或庸俗化理解。当时,用经济唯物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种最常见的现象。19世纪 70年代,法国就有一批年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庸俗化地解释唯物史观,以为自己掌握了它的原理,马克思对此气愤地说,如果这样,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95页。。恩格斯为此也做了许多理论上的解释工作,他晚年所写的不少书信,就是专门为此而发的。
马克思主义向俄国的传播,最早是通过民粹派之手进行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俄译本,就是出自民粹主义者之手。但民粹派往往曲解或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一些人物,如特卡乔夫、皮萨列夫和巴枯宁等,就曾把唯物史观作庸俗的解释或粗暴的歪曲。在他们看来,文化艺术都是贵族老爷的“奢侈品”,而劳动大众只配受用解剖青蛙之类的科学实验产品。
事物在数量上的扩张,往往是以质量的降低为代价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这样,它向横广范围的传播,往往伴之以对其原理的粗俗化解释。20世纪头 20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庸俗社会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进派”集团的代表人物波格丹诺夫。在这位“理论家”的鼓吹下,苏俄早期的庸俗社会学兴盛一时,并由它催发了一个由“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主导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同人类文化成果的历史联系,一味鼓吹在无产阶级封闭的阶级环境中,依靠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创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所以,他们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艺术家一概加以排斥,把过去时代的精神文化遗产统统加以抛弃,他们企图在一无所有的广漠的沙滩上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以波格丹诺夫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在 1920—1922年间受到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共 (布)的批判。自此,波格丹诺夫声名狼藉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此后,莫斯科大学教授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又取而代之,作为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浮上台面。在 20世纪 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借着当时掌握的一些权力,把持了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文学艺术部门,为“拉普”等一批取代“无产阶级文化派”而起的极“左”文化派别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与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所捍卫的列宁文化路线相对抗。在 1926—1928年期间,卢那察尔斯基作为苏联文化教育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贯彻 1925年俄共 (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政策》决议中,遇到了以 В.Ф.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派的干扰和抵制。这样,这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苏联文化教育的领导人,便于 20年代末倡导并发起了一场批判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斗争。这场理论斗争第一阶段从 1928年底持续到 1930年,第二阶段从 1932年持续到 1936年。但 30年代初以后,苏联政治形势逆转,加上卢那察尔斯基辞职,后又外放为大使,并继而逝世,这就使这场理论斗争受到中途干扰,而未能循着预定的轨道发展,因而留下了理论清理不彻底的后遗症。
庸俗社会学在苏联影响相当广泛,它不仅在文化艺术领域广为泛滥,而且在史学、哲学、语言学和学校教育等方面都流布甚广。由于它是一种扭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错误理论思潮,而苏联社会是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社会,因此对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深刻影响。由于苏联在理论上对庸俗社会学批判、清理不甚彻底,使其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面都留下了痕迹。据俄罗斯学者讲,它在学校教育领域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的 80年代。
在我国,没有专门进行过庸俗社会学批判,除了文艺学领域的学者以外,人们对这一理论思潮了解得较少。为了较深入地介绍这一理论思潮,我们特从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利弗希茨教授的著作中摘引出有关庸俗社会学的论述,加以编译;同时,顺便也以同样的形式介绍一下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派。在编译过程中,我们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较生疏的学者,凡就我们力所能及,可以从工具书中查阅到的,都尽量做了注释;凡没有查到的,名字后面都附有俄文,以便读者进一步使用、查阅。
一、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所谓庸俗社会学,主要是指在史学、艺术批评、文艺理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一种教条式地的简单化理解。更广义一些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抽象理解,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论财富的损害并走向伪造政治结论;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漫画化。
庸俗社会学这一术语从 30年代起就开始在苏联报刊杂志上使用,但庸俗社会学这一现象本身为人们所了解却要早得多。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有资产阶级知识界的许多受过半瓶子醋教育的代表人物归附于工人运动。他们不去独立地研究各种事实,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所有历史和现代问题的最便捷的方法。马克思在谈到他学说的这些追随者时说:如果他们是这样,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95页。。恩格斯在 19世纪 90年代的一些书信中 (《致约·布洛赫》、《致瓦·博尔吉乌斯》、《致弗·梅林》、《致康·施米特》、《致亨·施塔尔肯堡》)也证实,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庸俗化,在他看来已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庸俗社会学问题,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相联系的。早在 М.巴枯宁和 С.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中,这种不定型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势力就对唯物史观采取了粗暴的歪曲。由此,М.巴枯宁将文化作为与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陈旧贵族习气,进行了批判,或者把社会思想变成了社会斗争的简单工具。把马克思、恩格斯方法漫画化的另一例证,是 П.特卡乔夫在 18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把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同边沁②边沁 (Jeremy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译者的功利主义理论结合了起来。
庸俗社会学史前时期一个更为重要的史实,是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传播实证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在颇大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成分,有时也受到新康德主义的损害。不能不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就连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应该说这些著作是没有任何庸俗性问题的,但也存在着受到 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的痕迹。③这里主要是指受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米基艾尔斯〔Ми к и э л ь с〕和坦恩〔Т э н〕等人的影响。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往往将文化史了解为一系列由社会条件制约的、必然产生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必然性就像苹果树要结苹果,梨树要结梨子一样注定无疑。普列汉诺夫则把这些历史产物的可比性问题排除出了历史的范畴 (形式逻辑、艺术技巧、伦理法则)。但是,可归入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孟什维克流派的大量社会学文献,却比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要逊色得多。
更加接近孟什维克的一种倾向,主要在大量的通俗性书籍文献中得到了反映。除了历史学家 Н.罗日科夫和对 19世纪作家有独到研究的学者 В.Ф.彼列维尔泽夫以外,这种文献的一些代表人物,像在西方一样都不值得特别一提。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学方法在远远超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学术著作中,都得到了反映。В.克尔图亚拉的俄国文学史教程 (1906—1911)可视为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西方的这类著作,则是А.埃列弗特罗普洛斯的哲学史著作 (1900)。这两种情况都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了。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兴起,是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错误的一种反动。这种思潮在社会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法国思想家 Ж.索雷尔 (Ж. С о р е л ь)。这种思潮的典型做法是 ,放弃历史中的客观真理标准 ,由社会学分析转变到阶级观点的完全主观性思想 (社会神话理论)。在俄国,极“左”类型的庸俗社会学由波格丹诺夫的“前进派”集团所代表。或多或少依附于波格丹诺夫一派的是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他们就是М.波克罗夫斯基、В.弗里奇④В.弗里奇 (1870—1929),苏联文艺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1929),1917年入党,一系列学术机构领导人。和 В.舒利亚季科夫⑤В.舒利亚季科夫(1972—1912),文学评论家、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用以说明哲学史方面庸俗社会学特点的术语——“舒利亚季科夫学风”,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等人。他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曾起过大的作用,但不总是正面的。普列汉诺夫为在哲学史方面说明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特点,创造了“舒利亚季科夫学风”这个术语(1909)。把精神文化史的史实变为各社会集团的简单标识和与此相联系的相对主义,也就是说放弃客观真理,不言而喻,同普列汉诺夫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不善于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仍站在列宁反映论的客观历史辩证法之外。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向广大范围的迅速传播,以及一部分旧知识分子为适应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使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实际可感觉到的、对社会主义文化造成严重危险的现象。在文化建设方面建立在滥用阶级斗争观念基础上的蛊惑宣传,采取了特别有害的形式。无疑,来自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有关阶级的体验和无产阶级文化观,在 1920年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庸俗社会学往往导致了可笑的、讽刺画般的,同时也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只要回忆一下取消学校的理论就足够了;而这一理论的拥护者就是像М.波克罗夫斯基这样的人。在俄国史领域,庸俗社会学往往将过去的官方历史学公式颠倒过来,把历史看成“是被推到过去的政治”。从这一观点出发,伪第米特里和马泽帕①И.马泽帕(1644—1709),在 1687—1708年间的乌克兰首领。他力图把乌克兰左岸地区从俄罗斯分割出去。在北方战争期间公然站到入侵者一边。反倒成了他们那个时代革命力量的代表,而彼得改革的进步意义反而遭到了激烈的否定。整个来说,与民族传统和旧国家相联系的一切,都不分青红皂白,遭到了革命词句的谴责。
在革命之初和后来头几个五年计划的转折年代,庸俗社会学为摈弃旧文化遗产的各种极“左”运动,提供了总的发展环境。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想形态,从消灭音乐的宣传,到把艺术溶入生产和生活的理论(“列夫”的主张),有时带有离奇古怪的荒唐性。庸俗社会学往往同现代主义思潮的破坏性论断交织在一起,或者对现代主义的论题加以维护。比如,几乎被证明是正确的一种看法认为,绘画中最适合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来自立体主义的“组织”画派,为鸿篇巨制的画作而否定了画架。从旧社会继承而来的文学体裁甚至遭到了怀疑,当时曾存在过一种取消悲剧、喜剧的理论。庸俗社会学最温和的一种思潮,仍然把旧文化看作是形式主义方法的大坟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虽然为了功利主义目的可以利用这些方法,但这样做时应保持相当的谨慎。
革命为劳动群众打开了世界艺术宝库的门扉,同由此激发起劳动群众高涨情绪的情况全然相矛盾,庸俗社会学把自己或明或暗的目标确定为揭露过去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把他们统统看作统治阶级的仆人。从这个观点出发,每一部艺术作品都被看作是在世界上为权力地位而相互争斗的各个社会集团的暗藏密码和符号;而无产阶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本阶级的心理,表达有别于其他任何阶级的,更加有组织、更加健全、更加积极乐观的心理。
由此,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用以描述文学经典作家的许多可笑而滑稽的说法:把普希金说成是日趋衰落的贵族老爷或者资产阶级化地主的思想家,把果戈里说成是一个小地主贵族,而托尔斯泰在他们看来,则变成了与高等贵族沆瀣一起的中等贵族的代表等等,不一而足。而被看作确定不移真理的,是认为十二月党人捍卫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与粮食贸易利害攸关的地主的事业。这样一来,这种社会学所包含的一丁点的真理,便变成了十足的充满好斗精神的狂言乱语。
庸俗社会学幼稚的狂热性,部分是对所有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对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固有的革命否定的夸大其词。这种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显现出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匮乏,而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对世界文化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党性的共产主义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面的任务是伟大而宏阔的,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刻以全部的深度和广度把这一任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界面前。恩格斯早在当年就曾指出,用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社会现象的更具体方面还研究得不够;不言而喻,在革命斗争的条件下也不能不是这种情况。一些困难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亲近的继承者也没有加以解决,尽管像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有着巨大的才华和修养。用更高的水平解决这些问题,是由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奠定基础的,而列宁主义当时还不为人们所充分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文献的一些习惯公式带有被极“左”“斗争哲学”(С т.沃尔斯基的术语)精神所修正的一些内容,在报章杂志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这一背景下,值得惊讶的是,А.В.卢那察尔斯基以其无比的才华解决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艺术创作的问题,虽然他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迫对庸俗社会学做出了大的让步。
从另一方面说,把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看作是为善良目的而干了不理智的事,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许多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完全不是庸俗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极度文雅、非常讲究的,——庸俗社会学方法的粗鲁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厌烦之事,也是自觉或者不自觉采取的一种哲学。庸俗社会学不是个人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现象。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杂俎,是那些为自己、也是按照自己方式参加革命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一种心理反映。在列宁看来,这也是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危险性的那种爆发户心理的反映。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45页。庸俗社会学的强大时期,在 30年代中期宣告终结。它的最出色的代表,往往也是一些有天分的、彻底坚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再喧嚣了。苏联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巨大社会政治变化,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不再可能直接表现出来;而小暴发户的心理残余无论如何强大,到底还是采取了全然另一种形式。
庸俗社会学的刻板公式属于这样一些意识形态观念,它们是在一定条件下自发地、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产生的。它所特有的独特思维方式,是在为资产阶级社会视野所局限的旧唯物主义时代兴起的。由此,它蜕变、演化成了 19世纪下半期的实证主义。①坦恩 (Т э н)是这种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第一个创立了颇有影响的“艺术社会学”。如果把阶级的词句撇开不谈,庸俗社会学的基础就是抽象理解的有关好处、利益和目的适用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其片面发展中,对资产阶级时代的道德气候是十分典型的。精神生活的整个“理想的”表层,看起来是高贵纯正的幻想,但却潜藏着隐秘的或者下意识的自私的目的。一切具有特质的事物,所有无限的东西,都可归结为有限范围的简单力量的作用。不言而喻,这种世界历史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 20年代,一个剧院演出了莫里哀的《唐·璜》。按照导演的意图,一个有名的探讨快乐的人,他的死因必定不是骑士团团长的幽灵,而是来自一群起义农民的射击。当然,幽灵是不存在的,但在这一稿本中,艺术作品沦为资产阶级陈旧无神论对迷信进行理性批判的牺牲品。另一个导演则把沉思的哈姆雷特变成了一个狡猾、强悍而不知羞耻的政治家,让这个王子充满了嗜权的意志力,借助于臆造的幽灵,在群众中制造出了导演所需要的神话。这种从旧理性—功利主义公式向现代暴力崇拜的转变,给人们指出了庸俗社会学的另一根源。在我们今天,一些同资产阶级社会视野有着内在联系的观念,正经历着巨大的演进。它们现在正通过体现 20世纪非理性哲学和社会学的形态而呈现出来。
的确,庸俗社会学的基本原则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这个词的直接含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含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正是因为这一虚伪的哲学立场而完全不是滥用阶级或阶层这些概念,庸俗社会学才得以能够存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公式,在这里成了压制意识的自觉性,把它变为社会环境和阶级利益的自然产物的最便捷的工具。从庸俗社会学观点来看,一切历史的意识形态都同样是盲目的、有预设条件的、封闭于它本身的社会地平线上。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是存在的,但这种差别不是通过对现实的反映来衡量,不是通过表现在精神生活的此一或彼一形式和程度的历史发展的内容来衡量,而是用具有自我封闭的集体意识②这 是迪尔凯姆“学派”的术语。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法国杰出社会学家。1898年创办《社会学年鉴》杂志,形成迪尔凯姆“学派”,决定了法国社会学的特点。的社会集团的生命力作为主要标准来衡量。因为它们的这种意识是或强或弱地被表现出来的。所有的文化和风格都拥有同等的价值。只有借助于特定的社会诊断学③这 是德国“知识社会学”奠基人曼海姆的术语。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德国社会学家,曾任伦敦大学教育学主任教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欧洲部主任。——译者才能对他们加以相互比较。一个社会集团比其他集团更健康、更强有力,一个在壮大,而另一个却在衰弱,一个作家要比另一个作家更强有力地、更充分地表达了自己本阶级的意识形态。
进步发展的思想并不同庸俗社会学相背离,但是在纯形式、纯数量的意义上,它在这里超出了客观真理、社会正义和艺术完美性这些衡量尺度的范围 (见弗里奇社会学中艺术繁荣的标志)。所有一切,对自己的时代、自己的阶级来说,都是好的。庸俗社会学既诉诸于新旧斗争的抽象概念 (旧事物都是坏的,新事物都是好的)作为客观价值标准的替代品,也诉诸于文化和风格的类型学比较——或相似或对立或冲突,来确定其客观的价值标准 。比如 ,古埃及“组织恢弘的 ”文化与 В.加乌岑施泰因 (В. Г а у з е н ш т е й н)和 В.弗里奇笔下的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 ;在比安基 ·班迪内利 (Б и а н к и Б а н д и н е л л и)那里 ,“抽象 ”的形式与“有机 ”的形式往往可以相互替换;在弗朗卡斯特尔④皮埃尔·弗朗卡斯特尔(Pierre Francastel,1900-1969),哲学博士,法国艺术社会学家。和罗齐·加罗迪⑤罗齐·加罗迪 (Roger Garaudy),1913年生,法国晗学家,作家。1970年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译者看来,共产主义美学与中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风格可相提并论,就是如此。
这样一来,庸俗社会学的基础就是 20世纪资产阶级思想的历史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为许多精神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行纯形式分析,排除了真、善、美的客观内容。庸俗社会学在俄国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阿芬那留斯⑥阿芬那留斯 (Richard Avenarius,1843-1896),瑞士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立人之一。——译者和彼得楚尔特⑦约瑟夫·彼得楚尔特 (Joseph Petzoldt,1862—1929),德国哲学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追随者。——译者的社会学公式通过波格丹诺夫及其追随者所产生的影响。在他们那里,被置于真理地位的是集体的经验或阶级的意识,其他一切只不过是幼稚的现实主义。但庸俗社会学在完成从个性主体向阶级主体转变的同时,它并没有从唯心主义哲学前进一步,而这种哲学是为列宁在反对马赫主义者的有名著作中所批判过的。如果说某些部分的客观内容毕竟为庸俗社会学的许多代表所认可,那只是采取了这种思潮所固有的通常的折中主义形式。就实质来说,他们分析社会意识所残留的一点点现实性,同他们所戴的有色阶级眼镜 (按波格丹诺夫的说法)相比,也就是说,同赋予每一意识形态以预设类型的独特视角相比,只是起着次要的作用。
不管对现实反映之真实、深刻、矛盾的程度如何,但作为客观反映现实的地位在庸俗社会学看来,是为这一公式所占据的,即历史主体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平衡,或者这一平衡遭到破坏。对这一平衡的破坏源自年轻阶级富有生命力的进攻态势,这给向往未来的革命浪漫主义或者由腐朽社会集团的挫败感而产生的浪漫主义提供了基础,而腐朽的社会集团固有一种颓靡的世界观和颓废主义情绪。不言而喻,这个公式散发着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的思想气息,它对具体文化史的财富是无法做起码的涵盖的。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共性,这一公式无疑属于第二国际时代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流行模式。根据这些模式,所有历史冲突一般来说都归结为上升的进步资产阶级反对垂死的贵族和面向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由这一抽象而空洞的概念,生发出对庸俗社会学来说习以为常的、也是与孟什维克传统相联系的一种愿望,就是把自由资产阶级置于农民阶级之上,把农民反动乌托邦的形式同它们的进步内容相混淆 (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列夫·托尔斯泰复杂的精神人格的解释上),将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归结为反动的思想,不理解社会进步的深刻矛盾,也不理解世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对诸如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普希金这些伟大艺术代表人物进行阐释的任何现实感。他们艺术的历史观既不可能因为维护成为过去的封建主义,也不可能因为歌颂新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终结。总而言之,两条战线斗争的立场,也就是说,构成人类艺术发展的真实基础和与之相联系的第三种社会力量——人民的存在,在庸俗社会学看来,仿佛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反动的。
庸俗社会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紧随着尼采之后的资产阶级哲学,把意志而不是意识提到了第一位。像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潮一样,庸俗社会学渗透着极端的能动论。它对各种社会心理观念 (按照现代德国术语学,是社会意识的 Standortgebundenheit)的分类尽管在外观上是客观的,但却带有该历史主体的非理性的自我表现 。由此 ,就产生了里格尔①里格尔 (Alois Riegl,1858-1905),奥地利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译者和沃林格尔 (В о р р и н г е р)的艺术意志论学派对庸俗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只是这种意志被赋予了社会倾向 (取代了沃林格尔的种族内容)。这样,庸俗社会学整个结构的出发点,就成了阶级的自我表现。不言而喻,这种主观主义往往为党性的词句所掩饰 (比如,在模仿马尔特罗〔Ма л т р о〕和弗朗卡斯特尔的罗齐·加罗迪那里,绘画中的党性原则要求现实对象的变形,而文艺复兴时代所创造的与透视画法相联系的绘画的现实形式,只不过是渴望统治权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的表现)。在庸俗社会学所通行的观念中,阶级斗争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它更接近于尼采那里的强者与弱者的争斗,更接近于卢德维格·贡普洛维奇②卢德维格·贡普洛维奇(Ludwig Gumplowicz,1838—1909),波兰社会学家和法理学家。的独立社会物种的兽性厮杀,更像是研究动物政客行为或地道政治动物行为的无数美国社会学家③美 国这些社会学家以以齐美尔和冯·维泽为代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nel,1858-1918),美国社会学家,生于柏林,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冯·维泽 (ф о нВ и з е,1876—1969),原是德国社会学家,形成社会学创建人之一,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副主席。可能后来曾入籍美国,故也称“美国社会学家”。所阐述的形式主义集团论。庸俗社会学把阶级斗争变成了各种自私自利的社会势力为争夺一块面包、一块土地而进行的种族厮杀,这本身就不是对待各个时代基本阶级矛盾的态度。
无可争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第一次为客观地历史分析社会意识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来说任何意识都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的盲目产物。马克思懂得,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部分和该社会形态的自由精神生产之间,存在着一条相对的、但是现实的界线。④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部,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296页。后者总是通过一条“看不见的线索同人民的肌体”连结着。这样,在真正的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同寄生阶级的微不足道的告密者之间,就存在着差别,尽管普希金是贵族诗人,尽管狄德罗和爱尔维修 (C.A.Helvétius)⑤爱尔维修 (1715-177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表达的是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的活动之所以都属于无比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他们所反映的并不是为争夺社会金字塔顶峰那份战利品的斗争,其所以有世界文化价值,是因为他们反映的是塔下面双方之间的根本矛盾:一方的利益最终是同整个社会利益相符合的人民群众,一方是服从于一定的私有制形式和权力形式的寄生阶级上层——社会的临时主人。
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来说,不存在超越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运动的阶级斗争。这是通过各社会力量的对立,通过发展众多小私有者的利益,向前迈进的一条道路,但这毕竟是通向消灭阶级,通向建立真正的、确实是人类共同社会的道路。这一社会的必要性是为世界文化的优秀代表,通过往往互相矛盾,有时甚至离奇古怪但毕竟是有其现实历史根据的社会理想的形式,一直认识或者预感到了的。庸俗社会学的堕落恰恰在于,它不能将人们精神生活的绝对内容,同其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甚而不只起着消极作用的方面结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列宁反映论的基础上,只有在其辩证史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进一步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才有可能。
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广阔历史哲学视野正相矛盾,庸俗社会学赋予社会意识以纯粹的技术性质,对世界的客观真理采取中立的态度。对它来说,意识的形式只不过是简单的斗争工具,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标记和符号。他们无法用包含其中的客观现实内容来说服人们,而只能用催眠的、暗示的和诱发的方式影响群众,而同时却让人们服从于强有力的意志。庸俗社会学在苏联的实践,当年曾提供了不少把文学史归结为各阶级、阶层拳击搏斗的实例。不过,那种把社会意识看作预设条件的产物,看作使人们联合和服从的外在工具的观点,不是任何运用阶级的术语都可以行得通的。
庸俗社会学在这里完全可以被归入 20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之中。只要回忆一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和信息传播的理论就够了,在那里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对客观真理采取中立态度、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用的工具 。在肯尼特 ·贝格 (К е н- н е т Б е р к)的理论中 ,艺术成了社会借助于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从属于个别社会集团的政权的仆从——在人们眼里,这些行动把一定社会等级的现实任务提升到了放射神圣光环的地步。对格伦①阿诺尔德·格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德国艺术史和社会学教授。来说,原始人类的岩画是一种惩戒的形象 (Zuchtbilder)。对科林伍德 (R.G.Collingwood)②科林武德 (1889-1943),英国哲学家、史学家。——译者来说,艺术作品是保障某一社会集团生存下去的手段。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③弗洛伊德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译者和荣格 (Jung)④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译者的追随者,则把艺术形象看作借助于互动交流——比如就像古罗马的农神节和英法狂欢节时上下层象征性的翻腾滚动一样——来解除社会的紧张气氛,成为满足被压迫群众情绪的工具。在这类社会学理论中,魔术作为从原始社会搬来,移植到整个文化史上的用以积极影响群众意识的式样,起了很大作用。上述已经谈到,建立在这种社会学观察基础上的一点点可怜的真理,其外观被极大地、粗暴地夸大了,并且掩盖了社会精神生活的更加深刻的内容,而社会精神生活原是作为客观世界、无边无际的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展现出来的。
既然主观意志的因素和影响他人心理的作用占据了反映现实的地位,那么,庸俗社会学的主要兴趣就从艺术作品转移到了受体对它的接受上。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简单的符号就成了一种预设的东西。它的意义成了一个以接受者为转移的可变数。每个时代,每种社会环境都会把自己本身的独特意义灌注进阅读的字里行间。这样,图画的真正创作者就不是艺术家,而成了一面镜子。既然受社会条件决定的受体的接受点并不相重合,那么思想交流本身,也就是人们的相互理解,就成了不可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艺术作品和其他任何精神文化现象都有其本身的客观核心内容,而在受体千变万化的接受中仍然保持其核心内容不变 (因为它的基础是现实的形象),或者是,社会科学对任何标准都丧失殆尽,而无法区分比如文学事实和其他任何假象,就连对写手们的制作,低俗的小市民报刊或者文牍主义的连篇空话,也无法分辨出真伪来。
庸俗社会学本身还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否定了人类天才杰作同用作信息传播的中档产品的差别。这些中不溜儿的作品,作为简单的符号,甚至更为典型一些。由此,不仅出现了庸俗社会学反对“传记法”的辩论,表现出要写没有艺术家的艺术史的意图来,而且产生了一种直言不讳的要求,主张不要去研究独一无二的杰作,而要专门去研究那种中不溜儿的产品。在西方,著名的法国社会思想史学者 В.加乌岑施泰因(Г р у т х о й з е н),就坚持这一观点。在苏联也曾有过一个时期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 ”陈列品在博物馆里占着优势地位。缺乏才华的平庸之辈,作为中等阶级意识的更典型的代表,在博物馆里排挤了伟大的艺术家。
在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与通常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很困难的。这里有许多中间的和过渡性的台阶。在仅仅表现着资产阶级视野局限性的社会学的抽象概念,与学术著作遵循“社会学方法”所具有的实际内容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中间过渡状态。许多有才华的学者,比如像 В.加乌岑施泰因、А. 戈泽尔 (А. Г а у з е р)、Ф. 安塔尔 (Ф. А н т а л)、比 安基 ·班 迪 内利、П. 弗 朗 卡 斯特 尔 (П.Ф р а н к а с т е л ь)等 ,他们的著作总的来说都是于人有所裨益的 ,但并没有超出庸俗社会学的范围 。诚然 ,“庸俗”一词在其毁灭性的意义上来说,未必见得适当。很可能,彼列维尔泽夫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本书是研究这位作家创作的较好的著作之一,尽管它里面体现的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精神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多于 В.罗扎诺夫那本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但又不失趣味的书。西班牙国内战争的英雄,英国共产党员克里斯托弗 ·科杜埃尔 (К р и с т о ф е р К о д у э л л)是有名的著作《幻想与现实 》(1937)的作者 。这本书惊人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同卡尔·荣格的人类学混杂到了一起。这样的矛盾怎么可能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些矛盾是确实存在的。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一些社会学文献,往往拥有包含着某些新观点的大量历史资料(Э.齐尔策尔〔Э. Ц и л ь з е л ь〕)关于“天才 ”概念的研究著作 ,康福思 (M.C.Cornforth)①康福思,英国哲学家。——译者和韦斯福德〔Welsford〕关于滑稽诗的著作,以及 А.冯·马丁〔А.von Martin〕的《文艺复兴社会学》,就是这样的著作)。但是,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的一般局限性,也常常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很明白,越接近马克思对社会精神生活所提出的科学研究任务,就要求越高,就对所有片面性感觉得越尖锐、越突出。
至于涉及更加狭义的庸俗社会学,那虽然其过渡形式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版本的唯物史观,即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文献中的反映。片面地运用马克思的一些论断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在 20世纪花样翻新的主要动因。马克思主义对诸如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和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 im)
这些杰出社会学家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更不要说其他许多人了。在这个圣水盘里得到新的洗礼之后,那种被错误观点杂质所损害的同样的思想,又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来,这就是庸俗社会学奠基的过程。
有某种反常之处在于,庸俗社会学方法首先可以运用于它自身。这的确是反映一定社会环境所固有的生活形式的集体梦魇。这不仅是因为庸俗社会学虚假的洞察力把全部世界文化史变成了一些自私的社会集团在市场上的一场大厮杀,把人类精神的高峰掩埋进了庸俗社会学家所习惯的道德氛围里。这一套观点体系的主要缺点还在于,它包含着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辩护。
假如说精神生活的所有形式都仅仅是意识形态 (虚假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术语已为曼海姆 (Mannhe im)②卡尔·曼海姆 (KarlMannheim,1893-1947),德国社会学家。——译者、霍克海默尔 (Horkhe imer)③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1985-1973),德国社会学家,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А.戈泽尔和其他西方社会学家所接受,不过他们对这个术语所作的解释却是不正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怎样才能保证社会学家笔下所描绘的历史图画不也是某种形态的虚假意识,即纯粹的预设符号呢?为了摆脱这个恶性循环,我们的社会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意识作为例外,把它变成超意识形态,变成原意识。在现代西方社会学文献中,有许多试图阐述社会学家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尝试,但这一切只能使人置之一笑。如果出发点是可信的,那矛盾就没有解决。如果这个矛盾可以解决,那就需要承认在人类思维中可能存在绝对的内容。
与此同时,问题还在于它的实际方面。社会学家把本身的意识作为例外,给人划分为两个层级提供了基础。一些人是自己环境的盲目的产物,也是各种交际手段,如文学、绘画、电影、电视和其他监管他人意识的强大工具影响他们的盲目产物;另一些人仍然躲在幕后,管理着广大的普通群众。这就是技术精英、行为主义者、人际关系的工程师和社会学家,一句话,是领导社会的埃及的祭司。
且不说这种观点在道德上的低劣卑下,我们只需指出,这种观点的确是集体的梦魇,是得到文凭的小爆发户的幼稚的乌托邦。类似福科 (Foucault)④米歇尔·福柯(Mu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社会学家,曾任法兰西学院教授。或者马克卢汉 (McLuhan)⑤马克卢汉 (H.M.McLuhan,1911-1980),加拿大社会学家。——译者那些富有好斗精神的书籍,一些著作确认开启了一个方法支配内容、预设条件支配现实的时代;这些著作证明,拒绝整个历史文化基础所赖以存在的客观真理,正导致社会意识的严重破坏。正像艺术中的现代主义一样,庸俗社会学成了知识分子的鸦片。
很可惜,由于近些年许多本质性的原因,我们重又遇到了庸俗社会学的活跃,而且是通过两种不相吻合,但却能够接近的形式活跃起来的。一方面,在西方“新左派”的书籍文献中,会经常遇到这样一些思想成分,总是把阶级斗争理解为抽象的观念,将革命看作是对传统形式的赤裸裸的否定;另一方面,在东方的所谓文化革命中,向我们展现出了社会蛊惑宣传的范例,从中可以看到,摈弃经典文献和整个文化遗产起了巨大作用。在那里,真理、道德和艺术成了失去独立客观意义的简单工具,阶级斗争被贬低成了庸俗的暴力论,在那里,对强权的崇拜再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对群众意识进行管理的受教育的少数会处于什么地位,是不难理解的。
——摘自《利弗希茨文集 》(М. Л и ф ш и ц. С о б р а н и е с о ч и н е н и й)(3卷本 ),第2卷 ,莫斯科 1986年 ,第233—244页。此扩展版本也发表于《苏联大百科全书 》(Б С Э),莫斯科 1971年,第5卷。(马龙闪 编译)
二、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派
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派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从十月革命前到 20年代初,主要是以“前进派”集团波格丹诺夫为代表,包括 М.波克罗夫斯基、В.弗里奇①В.弗里奇 (1870-1929),苏联文艺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1929),1917年入党,一系列学术机构领导人。和 В.舒利亚季科夫②В.舒利亚季科夫(1972—1912),文学评论家、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用以说明哲学史方面庸俗社会学特点的术语——“舒利亚季科夫学风”,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等一批人,但经过列宁在 1920—1922年对以波格丹诺夫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波格丹诺夫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到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派以莫斯科大学教授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这一“庸俗社会学派”在文艺学领域为最活跃,与此同时,以 М.波克罗夫斯基为代表的一个学派在史学领域还有相当影响。
乍看起来,对文艺学中以 В.Ф.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这一社会学派在 20年代末至 30年代中所进行的这次打击,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按照该学派成员所做的思考,这种文艺学看起来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观点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的确,这一学派似乎在理论上是为确立苏联文学的一元论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而苏联文学又是工人出身的作家为其本阶级所创造的。这个学派仿佛也为无产阶级文学本身提供了理论根据,而这种文学又是为“拉普”、“列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代表人物在整个 1920年代所一直所追求的。但后来到底还是遭到了被粉碎的命运。这原因大概既有美学本身的问题,也有社会政治性质的问题。
所谓“庸俗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呢?这首先是一个严肃的文艺学派别,是产生于革命之前,确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任何艺术现象进行社会阶级分析的学派。在 1920年代,当其最繁荣的时候,它被文学过程的当事者看作是苏联文艺学的干流。当时在人们思想中,恰是对艺术形象的社会阶级等价物的探讨被认为是美学分析的基本目标。这一学派的奠基者是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莫斯科大学教授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这个学派的思想,在 1920年代得到了诸如 П.Н.萨库林、П.С.柯根这样的著名文学史家的赞同。该学派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不无才华的学者,Г.Н.波斯佩洛夫和 Б.И.阿尔瓦托夫就名列其中。这个学派的一些原理是如此牢固地根植于人们的美学意识,以致于 1929—1930年进行的毁灭性批判并不曾铲除“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这种观点起码在 30年间都表现了出来,而在学校教育的传统中则一直存在到 20世纪 80年代。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绝不是躲在书斋里的学者,相反,他们曾经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公众人物。弗拉季米尔·马克西莫维奇·弗里奇 (1870—1929),曾主持红色教授学院文学系和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部,并担任理论刊物《出版与革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主编,还编辑了当时刚起炉灶的《文学百科全书》的头两卷。瓦列里安·费奥多罗维奇·彼列维尔泽夫 (1882—1968),也曾是莫斯科大学和共产主义学院的教授,他拥有一个广泛宣传自己观点的社会讲坛。早在革命以前,这两个研究者作为学者已经走向成熟。1908年弗里奇完成《西方文学发展纲要》一书的写作,在 1934年以前曾多次再版并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的经典作品。В.Ф.彼列维尔泽夫曾参加 1905年革命,为此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度过了 6年 (1905—1911),他从那里带回来的两本书,一本接一本地连续出版,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912)和《果戈里的创作》(1914)。在 1920年代,他们被人们看作是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普列汉诺夫的直接继承者。
为想方设法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美学现象,这些学者走向直接把文学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等同起来:在他们的理论中,文学是直接由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弗里奇在《西方文学发展纲要》中断言:“每一种经济活动形式,都给该时代的人们造成了共同的心理特征,这是他们在内心世界和创作方法上有别于另一时代的人们”①Ф р и ч е В. М.О ч е р кр а з в и т и яз а п а д н ы х 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М.,1934.- С.48.。这一状况,从他的观点来看,就使文学的发展演变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直接依赖于生产方式。这些表现为相应“创作方法”的“心理特征”,按照弗里奇的看法,也决定着文学思潮和风格。因此,文学的历史是作为各种历史风格相交更替而展现出来的历史,每一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则表现为由社会经济关系所产生,归根结底也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所产生的统治阶级的心理方式。因此,所有文学时代都是随经济形态而出现并从属于经济形态的:艺术家不可能超脱自己时代风格的范围,而且也命中注定要往返周旋于其阶级属性所强加于他的各种形象圈子之内。无论其愿望如何,无论其如何力图自觉地达到这一点,他都不可能超出他自己的界限。而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就成了这个“庸俗社会学”学派的中心思想之一。正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决定着艺术家创作的各种矛盾,而艺术家的生命状况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正好相吻合。比如,拜伦“有时在意识形态上是站在新兴阶级的立场上,但在其心理的潜意识深处”,却无法“与祖辈生活其中的自然经济世界”相决裂。②Ф р и ч е В. М.О ч е р кр а з в и т и яз а п а д н ы х 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М.,1934.- С.43.
1928年,В.Ф.彼列维尔泽夫和他的一批弟子共同发行了《文艺学》的第一个文集,这是一个不定期出版物。这时,该文集阐述的纲领性理论也在同舆论界的各种会见中宣示了出来。这一举动,也大体说明了这位学者具有积极、活跃而带进攻性风格的特点。比如在文集出版前不久,彼列维尔泽夫曾在莫斯科举行的高校教师会议上做报告,总结性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又比如,他还向自己的听众讲解,艺术形象的社会决定性是怎样发生的。
为了把艺术家的创作同他所依属的阶级环境硬性联系起来,彼列维尔泽夫借助一种艺术即游戏的理论来加以说明。彼列维尔泽夫认为,恰恰是游戏,特别是儿童那种完全无私的、不带什么实际利益诉求的游戏,也还是有着很重要的目的性的。这种游戏的实质就在于,它能够再现该社会通行的社会性行为——劳动的、社会的、家庭的和日常生活的行为,等等。彼列维尔泽夫认为,艺术也是一种游戏,只不过是上升到了原则上不同级别的另一高水平。如果说小孩在游戏中扮演大人,在创造成年人生活形象的同时,在这一刻把他自己和成年人等量齐观了,那么在艺术中,形象就同游戏者分离开来,被加以客体化,以文学作品的雕像、画面和人物的形式成为一种独立存在。艺术创作行为也正包含在这种客体化中:“社会性质”、“游戏主体”(即游戏的人、艺术家、作家)被实现着客体化,其本身就体现在他所创造的形象中。换句话说,艺术形象是游戏者,即艺术品作者和创作者的“社会性的投影”。作者好像在舞台上扮演着 (体现在创作的艺术形象中)自己本身社会性的角色,再现着自己阶级所素有的“行为体系”,但却对思考它、从旁边观察自己无能为力。这个过程的发生,并不以艺术家是否愿意自觉地表达自己的阶级观点为转移,或者恰恰相反,也不以艺术家是否愿意自觉地中断同自己环境的联系并建立新的社会联系为转移。
从彼列维尔泽夫的观点来看,这也决定着艺术的职能:通过这种“心理的游戏”影响读者或观众的潜意识,引起人们对它的模仿,从而把社会阶级的行为方式、道德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等等巩固下来。“社会性质”作为彼列维尔泽夫美学的中心标准之一,是由商品生产方式形成的,是它在艺术镜子中的反映。正因这个道理,艺术家命中注定必然是只同自己本阶级相联系的,他不能 (无论怎样想这样做)超越他自己而站在别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那么总体而言,在游戏中可以再现什么样的性格呢?”——彼列维尔泽夫向他在共产主义学院论战中的论敌这样发问,并立即回答道。——“是的,显而易见,是艺术家的性格,因为无论任何人的性格都不可能在这里再现出来”,他“封闭于”他所创造的形象的“特定世界中”,“这个世界的界限他是无法冲破的。”③П е р е в е р з е вВ,Ф.С о д а к л а д//П р о т и вм е х а н и с т и ч е с к о г о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о в е д е н т я.- М.,1930.- С.50-54.
“艺术—游戏论”在彼列维尔泽夫这里得到了充分而彻底的发挥。他把艺术家创造形象时所采用的艺术方法之综合,称作风格,认定它有社会阶级的制约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阶级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坚如磐石的,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阶级的集团、等级、社会阶层,等等。正是这个缘故,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分别是各种各样的,反映着其创造者阶级存在的各种表现形式。文学的历史作为适应于这一或那一社会形态的各种风格的更替代谢而呈现出来;阶级斗争在艺术中作为风格的斗争而反映出来,而艺术家则是作为其阶级意识的表达者而存在。果戈里体现的是自然经济解体时代小地主贵族生活的存在形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表达者而存在。实质上,研究者的任务可归结为揭示这一或那一作家创作的“阶级等价物”。艺术家及其形象体系牢牢依附于生产过程,牢牢地附着于同该过程相联系的一定的阶级,几乎可悲地、命中注定地在阶级“社会存在”所产生的这些形象圈子中打转转儿,——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构建确定不移的文学史发展的一元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不可能诉诸于容纳不了阶级线索的那些艺术作品内容的 (相当重要的)方面,也就是往往被称作普遍人性的那些方面。实质上,文学的历史也只是作为社会经济历史的反映而呈现出来的,它图解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更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政治过程的唯一动力。不言而喻,这样的理论就使文学可能得到的科学阐释变得极端贫乏,尽管 В.М.弗里奇和 В.Ф.彼列维尔泽夫及其弟子们的著作有着明显的才华。因为他们这方面的不少著作即便在今天也是重要的,首先是在有关作品的具体分析方面。①举 例说,现代的读者可以了解彼列维尔泽夫就古典文学所写的一些著作(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这些著作收集在《Уи с т о к о вр у с с к о г ор е а л и з м а》(М.1889)一卷中。
不言而喻,庸俗社会学肯定是存在的,但它首先不是表现在该学派奠基者的著作中,而是更多体现在他们模仿者的文章里。有许多这样的例证,其中就是 Б.И.阿尔瓦托夫早年一篇题为《形式的反革命》的文章。②Л е ф.-1923.- №1.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勃留索夫的诗歌做了“社会学的分析”,表明勃留索夫的伦理观“带有封建资产阶级的性质”,同时顺带一笔,还揭示了“勃留索夫句法结构的反动性”。这样的分析表明,庸俗社会学流派的作品让人将其面目看得何等鲜明。
从 1929年 11月到 1930年 1月,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和语言部进行了有关彼列维尔泽夫理论的争论,这场争论发展成了全社会对庸俗社会学派的严厉批判。1930年 1月,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揭露了”这一学术思潮的“庸俗社会学性质”。
有关彼列维尔泽夫理论的争论,是在“反对机械论文艺学”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一场争论“并不是突然爆发的,它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是为我国革命和文艺科学先前的整个发展所决定,并以此为先决条件的”③П р о т и вм е х а н и с т и ч е с к о г о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о в е д е н и яД и с-к у с с и яок о н ц е п ц и иВ.Ф.П е р е в е р з е в а.- М.,1930.- С.4.。——在争论资料出版前言中这样说道。在讲到为什么恰恰是彼列维尔泽夫教授的这一学派遭到批判,文件又进一步解释说:“同彼列维尔泽夫们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彼列维尔泽夫的理论转向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力图在文艺学领域取得领导权,因为它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路人’,而力图对它取而代之。”④П р о т и вм е х а н и с т и ч е с к о г о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о в е д е н и я ЖД и с к у с с и яок о н ц е п ц и иВ.Ф.П е р е в е р з е в а.- М.,1930.- С.5.
——摘 自 戈 卢 碑 科 夫 (М. М. Г о л у б к о в):《20 世 纪 俄 国 文 学 批 评 史 (1920—1990 年 代 ) 》( И с т о р и я р у с с к о й 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н о й к р и т и к и Х Х в е к а[1920—1990- ег о д ы]),莫斯科 2008 年 ,第167—172页。(马龙闪 编译)
(责任编辑:蒋海升)
K091
A
1003—4145[2010]05—0011—17
2009-03-19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