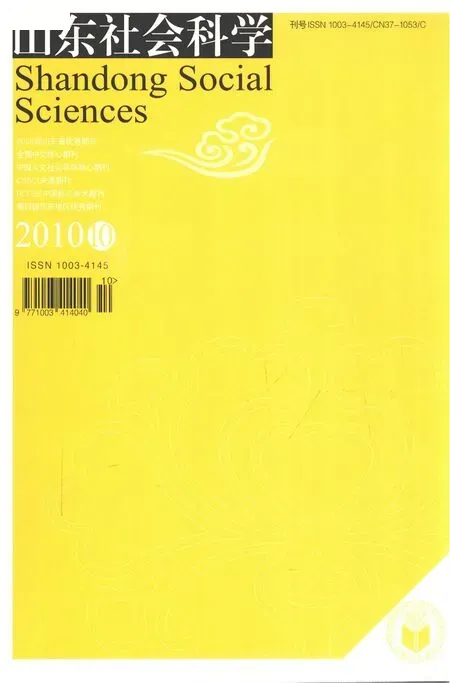情到深处人孤独
——哈维沙姆小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解读*
冯瑞贞 任晓霏 李崇月
(江苏大学外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情到深处人孤独
——哈维沙姆小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解读*
冯瑞贞 任晓霏 李崇月
(江苏大学外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荣格以“集体无意识”和“原型”为基础建构的“原型批评”理论涉及文学、人类学、神话学和心理学,为研究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重新审视《远大前程》中哈维沙姆小姐性格异化背后的诸多因素,认为男性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女主人公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和暗影的过度压抑使哈维沙姆小姐的悲剧命运成为必然,期望能够为狄更斯笔下的女性角色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集体无意识;原型;哈维沙姆;人格面具;暗影;异化
一、“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批评”学说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 (C.G.Jung,1875—1961)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从考古学、神话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广泛深入的思考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学说,从而对人类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艾尔金德所说:“在许多领域……荣格对于直到现在才得到普遍重视的现代人提供了多方面的洞察和顿悟。”荣格还以“集体无意识”和“原型”为出发点观照艺术起源,在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原型批评”研究涉及文学、人类学、神话学和心理学,并且日益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文学批评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对研究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集体无意识”既是荣格对弗洛伊德个人无意识 (personal unconscious)的发展,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创造。荣格认为,人的心理结构是由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系统或层次构成的,即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意识一般被看作是能被人们直接感知到的那些心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和内心体验。而无意识是“不处于自我控制之下的”精神世界活动。①戴桂斌:《荣格集体无意识述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 3期。在荣格看来,构成精神世界的大多数内容都是无意识的。因此,对人类心灵的考察,“如果不包括无意识过程,对人类心灵的探讨将是不完全的”。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经由传承而积累下来的祖先经验的积淀,它是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存在的,是超个体的、具有普遍性与集体性的心理倾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行为的各种本能和原型。正如人类的生理结构带有许多祖先遗传下来的痕迹一样,人们的心理结构同样带有由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有别于动物的特别的文化遗传基因。荣格解释说:“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集体无意识不是从个人那里发展而来的,而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继承或进化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的①荣格:《荣格性格哲学》,李德荣编译,九州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6页。。荣格选用了“原型”作为从集体无意识过渡到具体事物的中介,力求从生物本能的演化,从生命的内在性质和固有规律中去探索集体无意识的奥秘。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指向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时,强调远古与现代在文化心理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集体无意识提供了人的思维、行为的预先的、传承的模式,由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就打上了民族的、集体的烙印。对出生于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而言,其民族心理文化结构是在世代相传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世世代代的祖先经验逐渐浓缩、积淀、内化而成的,它似乎是一种超个人的、非自主的结构,个体通过家庭、学校的言传身教,致使风俗习惯、礼仪和行为规范等,在逐渐的、不知不觉中把这种社会的、具体的结构内化为自己的心理结构,从而形成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常常不被意识到的独特的文化心理。原型批评则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进而发现人类的精神真相,揭示艺术的本质。
这一经典理论在其身前以及后世的文学创造中都得到了具体的阐释。它甚至超越了历史时空和不同语境,在文本结构中通过不断的重建得以延续并不断获得新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些原型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其人文表征变得愈加鲜明而具体,往往能够超越时代、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而被普遍接受,称之为“原型意象”。在以“原型批评”理论关照各国、各民族流传下来的文艺作品并剔除它们不同的文化语境时,其中的“原型意象”常常会使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或者亲身参与之感。
二、哈维沙姆的悲剧是“集体无意识”的必然产物
本文试图在上述理论的观照下,重新解读英国 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中女主人公哈维沙姆小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哈维沙姆小姐因为新婚之夜被新郎抛弃,恨上了世间一切男人。她收养并“培训”了美丽的养女让她向男人报复,伤男人的心,直到自己悲惨的死去。以往对于哈维沙姆小姐的评论,多集中在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即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化迅猛发展的英国,批评家多把哈维沙姆定位为可怕的变态狂,是直接或间接的杀人凶手,把她的异化仅仅归因于男权意识或者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人际关系。本文借助“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原型意象的分析,重新审视女主人公命运悲剧的本质原因,认为男性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和暗影的过度压抑使哈维沙姆的异化成为必然,期望能够对女主人公和一切压抑的女性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试图发掘这种悲剧能够超越时代、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而被普遍接受背后的原型意象。
(一)反复出现的原型意象预示了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房间是一个典型的原型意象,在狄更斯的笔下,人格扭曲、暗影膨胀的哈维莎姆虽然住在一座豪宅里,却俨然是被困在一座监狱里,埋葬在一座坟墓里。
哈维莎姆小姐住的房间里到处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皮普第一次去哈维莎姆小姐的宅邸时就深深感到了那里阴暗、恐怖、压抑、荒凉、怪异的气氛。这所宅第,砖瓦都已年深月久,阴森森的,四面还装着好多铁栅栏。有几扇窗户已经砌没了;剩下的窗户,低一些的一律护着锈痕斑斑的铁杆。宅前有个院子,装了铁栅门。过道里一片漆黑。她的化妆室里也是终日不见一丝阳光,房间里点着蜡烛,影影绰绰,这些特征和黑暗的监狱有着许多相同之处。“铁栅栏”,“锈痕斑斑的铁杆”,“铁栅门”这些意象让人感觉到这就是一座监狱。自从哈维莎姆小姐遭到无情的摈弃,她的心被她所爱的人撕碎以后,不仅她的躯壳被囚禁在此,而且她的灵魂也被囚禁在此。她心如死灰,虽然拥有巨大财富,但是金钱在她婚姻遭受失败以后就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无法给她带来幸福和快乐。她拖着没有情感、没有灵魂的躯壳,在那幢黑暗、潮湿、阴森的宅邸中苟延残喘,她的举动变得越来越怪异,并且变得有些神经质。她终日把自己囚在这个黑暗的牢笼里,穿着泛黄的婚纱,不踏出家门半步。屋子里面没有生机活力,就像一个密闭的墓室,埋葬着一个散发出腐朽味的老处女。其次,哈维莎姆小姐的形象描写也体现出死亡阴影的存在。“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仿佛就是那个蜡人,那具骷髅”,“哈维莎姆小姐坐在那里看我们打牌,活像一具僵尸,她穿一身泛黄的白衣服,脚上只穿着一只鞋……”,这些描写中的“骷髅”,“僵尸”都和死亡有关系。皮普看见哈维莎姆小姐“吊”在那里,这虽然是他的幻觉,但是这一情节的设计也让人隐隐感觉到哈维莎姆小姐的最终命运会是什么,而且也让小说浸染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氛。“阳光全被隔在了外面,屋里散发出一种令人气闷压抑的混浊空气的味道。“湿的旧式壁炉里刚刚生了火,看上去是熄灭的份儿多,旺起来的份儿少”。炉火、烛光在许多小说里有象征意义,与希望、光明相联系,而这句话中炉火的熄灭也不是作者随意设计的情境,而是象征着在这个没有阳光,压抑重重的庄园中的女主人最终的死亡命运。房间内的新婚的摆设几十年不曾变动,可见主人对往昔生活的留恋和对美满婚姻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阴森凄冷的房间同时也是束缚其主人迈出阴影的外化表现。
(二)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和暗影的极度压抑是哈维沙姆小姐性格异化的内在原因
人格面具 (Persona)和暗影 (Shadow)是原型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按照荣格的定义,人格面具是人在潜意识里具有的一种能力,它能按照不同的情景来调整自己的角色。一个人如果对某一种人格面具过于专注,太倾心于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意识自我也就开始全然地将自身视同于这种角色,那么,他人格的其他构成部分会被弃之不顾。这种被人格面具主宰的人会迷失自己的本性,由于他过度发达的人格面具与其人格的发育不良的组成部分发生冲突,因此他便生活在一种由这种冲突造成的人格扩张的紧张心理状态中,从而陷入心灵的危机中。①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12页。
暗影是潜意识中人的基本动物性的部分,深深根植于人类的生理和心理进化的历史中,处于人格的最底层,是兽性的、本能的种族遗传。暗影是一种重要的有价值的原型,因为它可以凭借顽强的本能能力将个体投入更为舒心惬意、更为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中,使人的心理、生理需求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
人格面具和暗影作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相互冲突、激烈的整合过程中达到对立统一、平衡的发展,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个性化”人格,否则,任何一个部分被片面发展,都会导致人格的扭曲和畸形,最终在痛苦的挣扎中趋向毁灭的结局。但是,人格面具原型和暗影原型的显露并不总是表现为个体自身发展的本能的一部分,而外界和社会的规范和期望常常是它们赖以滋生成长和显露的必不可少的土壤。个体的人格面具和暗影原型的显像经常是整个社会的一种“镜像”,社会中各种元素的对立冲突是造成个体心理中不同成分的悲剧冲突的根源。
哈维沙姆是出身贵族世家的名门小姐,森严的门第观念和家庭教育使她从小就脱离现实生活,清高孤傲。在没有母亲的家庭中长大的哈维沙姆是萨蒂斯庄园的象征,即使镇上有身份的人也不能轻易一睹她的芳容;在父亲去世后她替父亲承担起了家族的责任,这个庞大的社会面具一方面满足了她受人尊敬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使她不得不极度压抑内心的自我情感。
家庭环境的熏陶、社会准则的束缚使哈维沙姆小姐远离尘世,固步自封。然而外表孤傲的她其实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需要,长期被禁锢的她甚至比常人更渴望本能的宣泄。于是,她轻信相貌堂堂的康佩森,把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所谓的金玉良缘中,当她坐在梳妆台前精心装扮自己,期待以华贵、美丽的形象出现在婚宴上时,一封来自康佩森的绝情信打破了她的玫瑰爱情的美梦,把她投入深渊。被骗遭抛弃后,这位富家小姐不能接受这种辱没门楣,极不光彩的结果,害怕世人耻笑,于是不再敞开心扉开始新的生活。哈维沙姆把这种对爱的极度渴望畸形转化为对男性世界无情的逃遁和报复。
每天在人格面具与暗影的剧烈冲突中挣扎,哈维沙姆的心灵被不断地撕扯。表面上,她似乎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她聘请律师帮自己打理家族产业,做起了名副其实的萨蒂斯庄园的女主人;而私下里,她收养了一个女儿艾斯特拉,把她塑造成一个美丽、高雅、孤傲、冷血的女人,以图报复男人。看见自己精心培养的翻版正一步步重复自己的悲惨人生,而自己作为始作俑者却无法阻止这个宿命的结局时,哈维沙姆曾经不止一次地责问自己,绝望地喊到:“啊!我怎么做出这种事来!我怎么做出这种事来!”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和家庭强加给哈维沙姆小姐太多太大的压力,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女性,她的美德就是忠贞柔顺,她只有体面地嫁人,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婚姻的失败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打击。在她所处的那个特定的时代 ,女性不是以自己的价值而存在,而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男性价值的一种标志。结婚当天就被丈夫抛弃,这会从很大程度上损害乃至毁灭一个贵族小姐的地位。所以哈维莎姆小姐要承受的不仅仅是来自她所爱的人康佩森带来的伤害,她还面临着来自世俗的各种压力。人们的闲言碎语、胡乱猜忌,人们别样的眼神,都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女子很难承受也无法承受的事实。
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哈维莎姆小姐自身内心对于人格面具的认同。出身名门、家产万贯、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这是多么诱人的人格面具!虽然这面具压抑了哈维莎姆小姐内心对于爱和美满婚姻的追求,使她心生厌恶,但是她又舍不得丢掉这份虚荣,直到最后,她已完全被自己的人格面具所吞噬。对爱的追求和被抛弃的痛恨日日夜夜折磨着她,摧毁了她对生活的信念,使她陷入人格扩张的紧张心理状态,造成人格的分裂与扭曲,也激起了她强烈的占有和复仇的欲望,并因为长时间的心理斗争与挣扎,身心能量消耗殆尽,无法找到自己的精神皈依,因而走向精神崩溃,走向最终的毁灭。这就是这位悲剧女性角色性格上体现出来的原型意象。
(三)男性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操纵了这位女性角色的悲剧命运
无论是在古典的、基督教的还是日尔曼的文明里,女性皆被认为是低于男性的劣等公民。在这样的氛围里男性不自觉地将女性置于被压迫的、受制于他们的地位。荣格认为文艺作品是一个“自主情结”,其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也即“集体无意识”的影响。
作为男权社会的一份子,“男尊女卑”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男性作家的脑海当中,使他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无法摆脱夏娃这一原型,并使这一原型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到外化。生活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下的狄更斯的集体无意识的形成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以上妇女观的影响,而他本人的经历更是刺激这种无意识外化的直接因素。出身卑微的狄更斯与他的中产阶级的妻子的婚姻并不美满,这种不幸的经历无疑又加重了他头脑中关于女性的集体无意识。
如上所述,作家会把这种生命的体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塑造了异化的女性,以表达自己对女人的怨恨和同情。
三、结语
虽然在狄更斯笔下,哈维沙姆小姐被刻画成性情古怪、喜怒无常、情感冷漠的变态女人,但是,她的境遇在文学批评家和广大读者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她的形象成了文学经典中抹不掉的一个典型,成为一个极具个性色彩且值得关注的人物。本文借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分析了哈维沙姆从一个对爱情满怀憧憬的痴心小姐到一个性格怪异、充满仇恨、近乎变态的老处女的心路历程。这个转变过程正是一个女人面具情结与内心暗影不断斗争直至毁灭的过程。哈维沙姆小姐最后葬身大火之中,结束了自己凄惨的人生。这个结局无疑使小说显得格外凝重和晦涩。然而,对于长期在痛苦中煎熬和挣扎,却无法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生,死亡,无疑是最好的归宿。哈维沙姆的死亡带给我们的更多的不是毁灭和灰暗,而是痛苦人生的解脱,是女主人公抗争窒息生命的一种绝望的表达方式,死亡更好地体现了女主人公在寻求自我路上的那种决心、迷惘、无奈和希望。哈维沙姆在生命最后作了忏悔,并请求皮普原谅,从而强调了小说的主题:通过悔悟和同情,罪人是可以得到救赎的。
当我们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对哈维沙姆进行分析和作出评判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诸多人类的共同命运。尽管作品人物与我们处于不同的文化语态中,但倘若拓宽视野,将其置放于人类文明的共时状态中去加以纵向比较和辨析时,就会发现哈维沙姆背后深藏着相同的人类共同经验,即过度压抑的爱会异化为极度的恨:情到深处人孤独。
艺术作品是人类原型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作品的观赏和阅读,可以激发一代代读者共同的体验。具体的文本个人或艺术形象所具有的原型意义,往往能够超出个人的、偶然的和暂时的意义,进入一个永恒的王国,个人的命运也就转变成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具体到本文分析的哈维沙姆小姐,虽然在众多批评家眼里,她是可怕的变态狂,是直接或间接的杀人凶手,她的故事也不过是一个没落贵族女性令人扼腕的爱情悲剧。可是,借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她作为女性无奈的人生轨迹,感知她挣扎的心路历程,从而在一声叹息之后,由衷地祝愿像她一样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悲剧女性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I207.4
A
1003—4145[2010]10—0051—04
2010-07-20
冯瑞贞 (1971-),陕西西安人,江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任晓霏(1968-),山西朔州人,江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李崇月(1967-),四川达州人,江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10BYY007);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08SJD7400004);江苏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JDR2008B07)。
(责任编辑: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