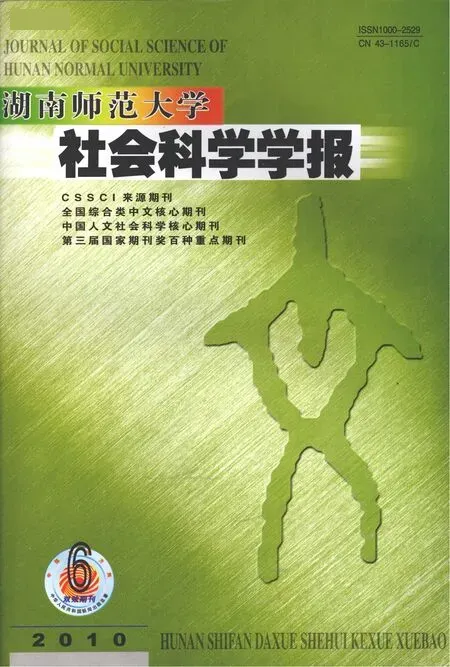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
李 丹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
李 丹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据接受理论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研究跨文化的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现象,重点分析造成文化过滤的原因是:接受者一方的现实语境、语言翻译、传统文化因素、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等。并力图通过对文化过滤的分析来揭示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变异机制。
文化过滤;文学变异;影响;接受
比较文学中传统的影响研究存在着浓重的重视影响者而轻视接受者的倾向,“影响”被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事实,在它的背后凸显的则是影响者的绝对权威。至于接受一方,则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似乎文学交流活动就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单向度流程。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今天,传统影响研究的这种倾向愈益暴露出其局限性。20世纪60年代后接受美学兴起,它肯定接受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从而开启了传统影响研究的现代转型。而在此之前,现象学和解释学已经为破除作者中心、凸显读者作用奠定了哲学基础。海德格尔对“先行结构”、伽达默尔对“成见”的强调,从理解的本体论性质的角度,肯定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创造作用。
文学交流活动中接受者的主体性、选择性、创造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是指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中,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现实语境、价值标准、审美习惯等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移植、改造、重组,它的结果就是源交流信息在本土语境中的变异。对文化过滤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文学变异的机制及其规律,也有助于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文化交流中弱势文化一方的能动作用,反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
任何文学交流都是以文化过滤为前提的。这是因为任何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定性、内聚性,因而在面对异域文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表现出抵御和排它。文学交流中本土文化遭遇异域文化的情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异域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接受者一方进行强制性的文化灌输或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另一种是接受者一方出于发展自身文化的需要,向异域文化中有利于自身的因子主动“拿来”。在这两种情况中,文化过滤都是相伴始终的。第一种情况,接受者一方可能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习性作为防御异域文化入侵的武器,使异域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使接受成为文化过滤之后的接受。第二种情况,接受者依据自身的情况对异域文化进行辨别、选择、改造,吸收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部分,过滤掉其与自身发展不相适合的部分。这种情况下文化过滤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经接受者积极选择、过滤、改造后的文化甚至与原文化相比已经面目全非。韦斯坦因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1](P29)接受者的这种能动性是文化交流史上从来就存在、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史上却长期忽视的事实。当下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文化交流中决定影响源能否对接受者发生有意义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影响源本身,而是接受者一方的社会环境、时代要求、历史传统等。“在一定程度上说,影响者的命运与效应此时由接受者来决定。”[2](P92)
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的存在,提示了两种文化中不可通约的部分,也鲜明地彰显了各自的文化特性。产生文化过滤的深层原因乃是各自文化模子的不同。叶维廉教授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中指出了东西方由于其文明肇始之初确立的根本价值原则的分歧而导致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模子,包括不同的“观念的模子”、“美感经验形态”和“语言模式”等。两个文化模子有叠合处也有不叠合处。其叠合处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共相,是文学交流的基础。而其不叠合处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性及其不可通约性,是文化过滤的所在。一般说来,文化的差异性越大,文化过滤的程度就越高,接受者的创造性接受也越明显,源信息的变异性也越大。
总的来看,接受者面对影响者的文化渗透,从本民族立场出发,组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文化过滤之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现实语境
外来影响的发生,从历史的角度看,决不是一种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是首先源于接受者一方的社会状况、时代环境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刻的内在需求。接受者一方往往根据自身现实语境的需要,而对外来文学的质素进行过滤,使其发生适合于自身需要的变异。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个民族文学对外来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事件,而是一个社会学事件、一个历史事件。因此韦斯坦因指出:“文学‘接受’的研究指向了文学的社会学和文学的心理学范畴。”[1](P47)并强调应“对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在形成文学原则过程中的作用作细致的探讨。”[1](P55)
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母题人物,被历代的作家所书写、塑造。从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到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的拜伦、雪莱,都曾创作过情节不同、性格各异的普罗米修斯故事。而这些而作家们创作时的现实语境,正是其对一些情节质素进行过滤并造成普罗米修斯形象变异的重要原因。
据赫西俄德《神谱》记载,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在进贡时杀死一头公牛,把好肉留给自己,而把肥肉和骨头伪装起来作为贡品送给宙斯,宙斯受骗后把火藏起来作为报复,普罗米修斯则盗火送给人类。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的这一新错误,宙斯把他绑在悬崖上,派神鹰啄食他的肝脏。因此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具有双重性,既是创造者和慈善者,又是阴谋者和反叛者。古希腊雅典民主制极盛时期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采用了普罗米修斯的题材。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埃氏着重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民主和正义而斗争的崇高精神和雄伟气魄,而完全过虑掉了神话原型中普罗米修斯形象阴险狡诈的一面。在普罗米修斯从神话原型到文学形象的这第一次转变中,其性格的变异正是源于当时现实语境的要求。在埃氏创作的当时,雅典民主派反僭主专制的斗争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面对此斗争,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骗子和阴谋者的一面是埃氏不认同的,而他坚决反抗宙斯专制统治的一面,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所迫切需求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中宙斯专制横行、残忍暴戾,实际上是雅典专制时期僭主的形象。普罗米修斯反抗专制、不怕牺牲,是为民主政治而斗争的雅典民主派的化身。可见作为全新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创造者,时代精神、现实语境是如何制约着埃氏对神话人物性格的过滤和变异。
但在埃氏剧中,最终普罗米修斯以和解的态度结束了同宙斯的冲突。悲剧的结局流露出奴隶主贵族出身、政治上属于民主派的埃氏想要调和民主派和贵族派矛盾的愿望。面对埃氏剧作一直以来的强大影响,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再次选取了普罗米修斯的题材。在其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雪莱修改了埃氏剧中普罗米修斯同宙斯和解的结局,不论是奉旨前来游说的麦鸩利的威逼劝诱,还是掌握恐惧、猜忌、怨恨的鬼魂的精神折磨,都无法使普罗米修斯低下高傲倔强的头颅。结局是朱比特被冥王推翻,普罗米修斯被释放,全宇宙一片光明和欢腾。雪莱创作的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失败、神圣同盟力图复辟实行专制统治的黑暗时代。雪莱虽然佩服埃斯库罗斯“登峰造极的艺术”,但决难认同那种“叫一个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的结局。[3](P2)因此诗剧歌颂了普罗米修斯反抗专制压迫、推翻暴君的永不妥协的精神,并展示了斗争胜利的光辉前景,起到了在黑暗时代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
可见不论是埃氏还是雪莱,他们对外来文学影响的选择性接受、对普罗米修斯性格特质的过滤及情节结局的变异处理,都是与作家创作时的现实语境密切联系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现实需要、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神话原型人物,既古老又年轻,他在一个个新的时代语境中,面对一个个新的问题,而一次次地焕发新的活力。
二、语言翻译
不同民族间的文学影响得以发生,往往是要经过翻译这一特殊媒介的。而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负载着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系统,因此语码间的转换不可能完全等值地进行,语码转换过程必然会造成一些文化信息的增添、失落、扭曲、变形。同时,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由于其“前见”或“先结构”,在理解上也不可能完全忠于原著。因此翻译造成的文化过滤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文学在两种语言间穿行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先看译者的因素。翻译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而带上了阐释学、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等的色彩。英国学者斯坦纳在《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也即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翻译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问题,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则是译者对另一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自然状态、价值观念等的理解和阐释。
按照阐释学的观点,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绝对的“忠实、准确”是不可能的,而变异则是必然的。阐释学起源于传统的解经学,解经学的目标是消除误解以达到对原文的正确客观的理解。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正确客观的理解是根本不存在的。海德格尔是从本体论而非方法论的立场上来看待理解的。他认为理解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即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就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带有“此在”的本体论性质。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它总是受到“先结构”的制约,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所谓纯客观理解。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必然不能摆脱“前见”或“先结构”而获得对原作的正确客观的理解。罗兰·巴特高呼“作者死了”,读者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翻译中的过滤和变异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语码转换过程造成的文化过滤和变异。俄国形式主义提出“形式即意义”,文学作品的内涵意义总是与其特定的外在形式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意义。尤其在欧美后现代的文学创作中,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更是登峰造极。而由于语言的差异,正如奈达指出,翻译只能是翻译内容,要在译语中再现原语作品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国古典诗歌,其意境营造、其无以言传的魅力,是与其格律工整、平仄相和、音韵铿锵密不可分的。而一旦翻译成英文,即便能再现原诗的内容,原诗浑然天成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却是无论如何无法再现的。而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失去了的那一点东西,正是真正的诗情诗味所在。因此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才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了的东西。”
即便不谈形式,仅就内容传达而言,所谓“对应词”之间的转换也必定要造成一些内容信息的流失、扭曲和变异。这是因为所谓的“对应词”事实上在各自民族的语言系统内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情感信息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可能做到完全对应,有时在深层意义上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尤其体现在一些特定的文化意象上。各民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审美心理等,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意象,它们在人们的日常语言和文学作品中不断地被重复,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其中凝聚着特定的文化含义,包容着独特的情感氛围,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朱光潜先生曾在《谈翻译》一文中就此提出了著名的“情感雾围”说,指出这类文化意向具有营造一种“情感雾围”的特殊功用。[4](P405)这些文化意象包括植物、动物、地名、数字等。如汉语中的梅兰竹菊,欧美民族语言中的玫瑰、橄榄树、夜莺、威尼斯、数字“十三”等。在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往往只能做到语言表层上的对应,而意象所负载的深层的文化信息却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失落或扭曲了。一般来讲,两种文化的异质性越大,文化意象变形和扭曲的程度也越大。如“龙”,在中国文化里是神圣、高贵、威武的象征,在西方文化里却是一个凶残、可怕的动物,西方的英雄史诗中常常有英雄杀死龙为民除害的情节。因此西方人对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的那种自豪感可能感到非常困惑。即使是同一文明圈,一些文化意象背后所隐含的独特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感情,也往往在翻译中失落。匈牙利翻译家乔杰·拉多曾举过一个例子:匈牙利诗人有一首诗题为《我们需要莫哈奇》,英译者把它翻译成了《我们需要失败》。莫哈奇是一座城市的名字,1526年匈牙利人在此惨败,从此受土耳其人统治。因此莫哈奇对匈牙利人来说隐含着这段屈辱的民族历史和沉痛的亡国感慨。英译者直译出了它的本义,但文化意象背后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内涵却失落了。[5](P190)可见由于文化系统、民族历史等的差异,文化意象及其所凝聚的独特的情感信息在翻译中几乎注定会遭到过滤和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语码转换就意味着文化过滤。
三、传统文化因素
金丝燕指出:“接受本身就是批评。每一次接受,接受者都有意无意地作了选择,而文化框架在文学接受中默默起着过滤作用。”[6](P2)“文化框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民族强大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漫长、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样态等。就跨文化的文学接受而言,接受者的传统文化及其形成的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扮演着“前见”或“先结构”的角色,它制约着接受者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来讲,异域文化中与自身传统文化同构的因素往往能被迅速吸收,而与传统文化异质的因素往往会遭到屏蔽或过滤。传统文化用以规范和过滤外来文化的网络包括民族心理、宗教观念、伦理道德、文学传统等。
东西方民族由于在以上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跨东西方异质文明圈的文学接受中,传统文化因素造成的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表现得尤为明显。朱生豪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焦急等待情人来闺床与自己共度良宵的台词的有意误译、严译《天演论》的注释“罕木勒特,孝子也”,都是著名的例子。
即使在同一文明圈,各民族国家也有着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使得跨文化的文学接受发生种种过滤和变异。
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18世纪传入欧洲,激起了欧洲各国文化界的强烈反映,甚至出现了好几种改编本,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欧洲各国在接受《赵》时产生的差异性,正可为研究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提供佐证。最早对《赵》进行详细批评的是法国批评家阿尔央斯。他指责《赵》剧违反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三一律”,剧本的动作时间长达20多年,且地点多次转换,完全不符合“时间、地点、情节整一”的原则。其次,他指责《赵》违背了古典戏剧纯净的风格和“措辞得体的惯例”,剧中包含着许多血腥的场面和令人吃惊的动作。法国作家伏尔泰的改编本《中国孤儿》将原剧时间从二十多年缩短到一个昼夜,使之符合“三一律”。还在原剧基础上加上一个恋爱故事。剧中成吉思汗一方面是位高权重的君王,一方面是多情的骑士,始终未能忘怀多年前的一段恋情,他对尚德之妻的爱情最终升华为对尚德之妻所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仰慕。与法国批评家的否定和批判态度相反,英国批评家赫德对《赵》剧进行了积极认同。他认为《赵》剧在情节、情感、结构、布局等方面都与古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相似。英国剧作家墨非也改编了《中国孤儿》,墨非指责伏尔泰改编本中成吉思汗向尚德之妻求婚的情节非常突兀,它把一个粗豪野蛮的鞑靼王变成一个谈情说爱、唉声叹气的法兰西骑士,与全剧基调不符。墨非改编本中的成吉思汗始终是个野蛮的征服者,最终以汉族对鞑靼的侵略抵抗到底、取得胜利结束。
之所以造成英法两国对《赵氏孤儿》的不同反映、不同改编、对其主题的不同过滤及人物形象的变异处理,其原因正在于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法国是古典主义大本营,古典主义对法国文化影响巨大,因此不符合“三一律”、不符合古典戏剧纯净风格的《赵》剧在法国遭到了苛评。而法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是骑士文学的故乡,普罗旺斯骑士抒情诗在封建时代对男女之爱的自由抒发曾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因此在骑士风范盛行、民族文化浪漫化基调突出的法国,伏尔泰改编本中的成吉思汗就具有了野蛮征服者和多情骑士的双重色彩。而在英国,古典主义的影响和民族文化浪漫化倾向都相对较弱,因此《赵》剧在英国较少受到苛评,成吉思汗也始终是个侵略者,而没有以多情骑士的面目出现。加之当时英法战争的背景,更使得对反对侵略、追求自由的时代精神注入墨非剧中,歌颂了汉族对成吉思汗外族入侵的抵死抗争。
四、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
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文本是一个充满了诸多“空白”与“未定点”的“召唤结构”,只有当读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填充了这些空白与未定点,使之“具体化”之后,艺术作品才会最终完成。读者先在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屏幕”在此填充过程中起着制约和过滤的作用。期待视野是指一种“文化先结构”,它是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已经具备的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实际上就是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前已然存在的立场、观点、审美标准和去取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接受屏幕”决定了哪些外来文本在读者那儿会被认同而哪些会被排斥。
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与其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是其传统文化形成的民族接受“先结构”的具体而微的表现。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出现接受屏幕的制约和期待视野的错位,也就越容易发生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这在东西方异质文明圈的文学接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即使在同一文明圈,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读者个体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修养、知识背景、审美趣味等,也往往形成迥然相异的接受屏幕,使外来文本在不同读者处产生不同的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
布吕奈尔说:“在同一时期古典主义的伏尔泰和浪漫主义的勒图诺尔在莎士比亚面前不可能有同样的态度。”[7](P60)面对同一个莎士比亚,作为莎剧读者和译者的伏尔泰和勒图诺尔,出于不同的审美趣味、艺术修养和价值立场,对莎剧作品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映、过滤和变异。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是精神实质上的浪漫主义者。莎剧澎湃激越的情感、驳杂狂放的艺术表现都体现了浪漫主义美学的核心。而伏尔泰是古典主义的信徒。古典主义的美学立场与浪漫主义针锋相对。面对莎剧中恐怖惨烈的场面以及一些低俗粗鄙的词汇,伏尔泰以其纯正的古典主义审美趣味无法接受,因为古希腊悲剧历来回避血腥恐怖场面、并且使用崇高庄严的语言。因此在伏尔泰看来,莎士比亚简直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闹剧作者”、“一个喝醉酒的野蛮人”,其作品充满了“博大而奇怪的思想”。“在他不由自主地狂怒之下想揭露这个野蛮人的失礼”时所翻译的莎士比亚的作品,着力凸显了莎剧恐怖和鄙俗的一面,而其崇高、诗意的一面则被忽略或屏蔽了。与此相反,作为浪漫主义者的勒图诺尔,其审美趣味与莎士比亚的艺术风格完全契合,他对莎士比亚充满了热爱。他翻译莎剧作品,宣称“要把莎士比亚献给自己的同时代人,并使他们爱他。”渗透了他自己的情感、理解和艺术再创造之后的莎剧作品,与伏尔泰笔下的完全不同。以致法国文学界有一句名言:“一个世界和伏尔泰一起结束了,一个世界和勒图诺尔一起开始了。”[5](P144)可见读者本人的艺术趣味、美学立场所形成的接受屏幕是如何影响了他们对异质文学的接受、过滤和变异。
综上所述,对跨文化的文学接受而言,文化过滤是首先、必经的环节。这既是各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接受主体基于深刻的内在需要而主动选择的结果。文化过滤有着复杂的过滤机制,现实语境、语言翻译、传统文化、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等是其中主要的几个因素,此外还有出版市场的控制、政府政策等其他的因素。应当指出,造成文化过滤的以上因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常常是共同起作用的。研究文化过滤,对于研究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特性、研究各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需、揭示跨文化的文学接受中的变异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英]雪莱.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原序(邵洵美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朱光潜.谈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7][法]布吕奈尔.什么是比较文学(葛 雷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Cultural Filtering and Literary Variation in the Cross-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LI Dan
(College of Literal Art,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ultural filtering and literary variation in the cross-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by reception theory and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It analyses the causes of cultural filtering:the reality context of receptor,language translation,traditional culture,individual reception screen of receptor,etc.It tries to reveal the variation rule in cross-cultural literary reception by the study of cultural filtering.
cultural filtering;literary variation;influence;reception
I206.7
A
1000-2529(2010)06-0125-04
(责任编校:谭容培)
2010-08-23
国家社科基金“文学变异学研究”(07BWW004)
李 丹(1979-),女,四川眉山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