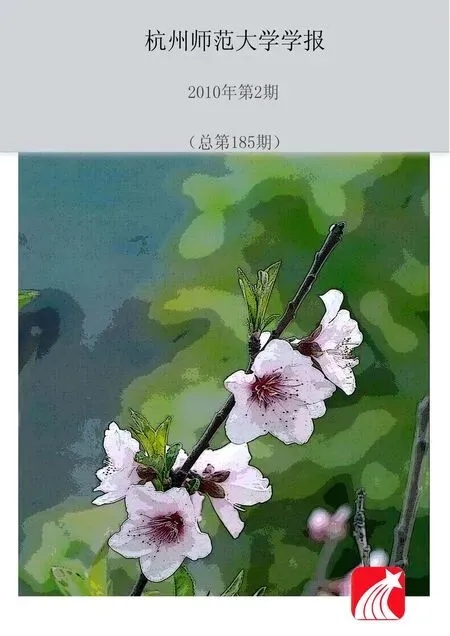论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力量
段京肃,任亚肃
(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媒介与大众传播研究
论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力量
段京肃,任亚肃
(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力量是包括政治力量、市场力量和公众力量在内的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体系。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力量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强,所以市场化的大众传播模式被认为是目前主要的也是理想的传播控制模式。但在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市场、公众和政府(执政党)三种控制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政府(执政党)的控制力量。当社会的诸种控制因素发生冲突时,其他的社会控制力量必须让位于政府(执政党)力量。在成分已经比较复杂的大众传播市场上,政府(执政党)“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分配者、规则制定者”,是大众传播媒介控制的核心因素。
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市场;公众;控制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中,大众传播活动的全过程被分解为五个环节:“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1](P.230)
拉斯韦尔这一被称为“5W模式”的经典划分最终演化“成为限定美国传播研究的范围和问题的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1](P.231),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长期的传播学研究中,对“谁(who)?”的研究,即传播“控制研究”,却有一些不甚了了的地方。在一般的研究中普遍将传播活动的“控制者”理解为职业传播媒体和专业传播工作者。吴文虎和程曼丽都曾引用了前任国际传播协会主席詹姆斯·霍洛伦的话解释这一现象:“以往的传统研究实际上大都站在‘谁’的立场上看待传播,无形之中都把‘谁’视为不必探究的已知数,至少也把它当成无关紧要的未知数,由此出发去探究取得最佳传播效果的途径。”[2]在我国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研究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即将媒体的控制片面地理解为是媒体和媒体人的行为,如果传播行为得不到社会的褒奖就把板子都打在媒体身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对媒介的表现颇多微词,而媒体人对此又有一肚子的委屈。尽管可以说“改革后,在政府的宣传管制、市场利润、大众需求以及自身专业诉求这些权利光影交错的互相作用中,媒体意识到需要在中间求得平衡”[3],但实际上在我国媒体所面对的各种权力博弈中,几种权力所起的作用是明显不同的,由此决定了我国媒体的特色。麦奎尔曾说:“要了解媒介结构和动力的主要原理,需要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如果不对影响媒介机构的广泛政治与经济力量做一个起码的描述,就不可能了解大众媒介的社会与文化意涵。”[4](PP.158-159)本文就是遵循这样的思路对我国媒介运行中的几大制约性力量进行分析。
二 文献回顾
关于媒介控制力量的情况,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但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媒介发展中又都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其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对媒介控制三大力量的认识。简单说来就是对媒介运作产生直接影响力的政府和执政党的力量、市场(经济、商业)的力量和公众(社会)的力量。
赫伯特·阿特休尔认为,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媒介都是工具,支持那些使它们得以出版的人”。[5](P.128)赫伯特·席勒认为,新闻传播媒介的控制与使用始终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因为“信息的专门使用权被认为是通向权力的通道。对于传播媒介的控制通常是取得政治权力的首要一步。位于现代组织机构中心的信息机构传播信息的方式永远不是随意的”。[6](P.29)他曾经尖锐地指出:“今天,在新的通信设备武装下,美国企业的强大影响力得到无法估量的加强。”[6](P.29)他认为:“由于从无线电广播的早期开始,报纸、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就大量地用于市场营销,因此,美国的信息机构也更加合理地被理解为销售机构了。”[6](P.8)
在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大众媒介的传播权力——主要是内容的控制权逐步落入美国之手,例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波斯湾发生的事件及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都来自美国这个单一的信息源”[6](P.1)。
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史蒂文森认为,为了准确地理解媒介的架构和话语,“我们需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公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7](P.2)。他认为,在商业性力量和政府政党力量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商业媒介以事件为导向的本质意味着它的行为背离了当地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些人试图通过媒介将图像制作合理化和规范化”。[7](P.156)
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在分析新闻报道不断出现的好恶周期时认为:“控制新闻报道方向的不是记者的好恶,而是政府中不断变化的权力之争(谁是热门人物,谁不是)、是新闻人物的专业传媒策略和政治欺骗、是新闻机构面临的经济压力。这种经济压力促使新闻机构不断发现新的、更为戏剧性的故事以满足挑剔的观众。”[8](P.34)
麦奎尔总结了媒介和社会的关系后指出:“在实践中,新闻的运用和政府、有实力的经济利益以及其他权威有密切的共生关系。”[4](P.128)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西方的传播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传播媒介的控制因素,“新闻机构一方面是老板赚钱的工具,但在过程中也要顾及服务大众的理念,是社会公器。新闻规范与商业规范同时并存,但有时又互相矛盾”[9](P.35)。
有的学者探讨了政府和媒介的关系,认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直至现在,对于政府,媒体就像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但却又不能不依附于政府。原因很简单,政府掌握着最为丰富的社会资源、信息资源,换句话说,政府对媒介的操纵,是通过掌握媒介所必须的资源来实现的,当政府通过其掌握的资源,能有效地左右媒体的利益,甚至对其生存造成影响,控制或曰操纵就由此产生。用‘场域’理论来解释,脱胎于权力场域的媒介场域,其生存条件是权力场域能够提供其基本的资源滋养,一旦断了奶,它也就难以存活。”[10]而反过来看,媒介利用政府和社会所给予的资源又在做什么呢?在许多情况下,社会资源转变为媒介自身资源最终成为媒介的自身利益。“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民主的正常诉求场所,只不过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11]通过资源和利益的转换,在媒介的三大控制力量中政府和媒体完成了事实上的交易,实现了各自的目的。而作为大众传播重要服务目标和资源的社会公众,除了被一次次“转卖”外,并没有可靠的手段实现影响媒体的企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媒介的控制因素中,人们目前更加关注的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媒介的产业化、商业化和跨国媒介集团的发展,经济的控制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对媒体产生多种控制能力的政府力量同样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 研究假设
中国大众传播媒体同样受制于多种社会权力的控制。主要有:政府(执政党)——实际是各级党政机关和官员;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群体——以利益和利润为中心,主要是各类有实力的经济体;社会公众——媒体的受众;媒体的自身控制。潘忠党等认为,“新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商业营利、服务公众利益和政党宣传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12]本文所涉及的是除社会公众以外的其他控制因素。
在控制媒体的多种权力中,政府(执政党)的权力是最根本的、发挥作用最显著的力量。这一控制是以国家、民族和全民的名义进行的,秉承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这一控制权力最终落实在各级党政管理部门和官员手中。但迄今为止媒体从这一角度所进行的改革是最保守最缓慢的,媒体运作中所遗留的计划经济痕迹是最重的。特殊环境决定了中国媒体实现专业主义理想的主要博弈对手目前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权力。中国大众传媒的精英们面对市场时表现出了绝不逊于外国同行的聪明才智,在近十几年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大量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但当面对政治权力时,媒介人同样只剩下了无奈的叹息。赫伯特·席勒指出:“由广告商赞助的私人电视台很少能够提供批评节目,而由政府资助的非商业性的传播机构就能够提供这种节目吗?”“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由总统任命总裁、资金来源于国会的年度核准的公共公司能够对统治集团的观点开展独立的、持续的批评。”[6](PP.148-149)在欧洲人们曾经试图以建立公共广播的方式为全社会的普罗大众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服务,但事实上公共广播的建立“并没有改变社会权力的分配,而是维护了中产阶级对其他下层阶级的统治”[13](P.102)。英国学者格雷姆·伯顿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府都可以运用媒体来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发布信息,也可以通过媒体来检验新近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效果,最为重要的是在公共领域内,为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14](P.14)
同世界范围内商业权力(公司、企业集团权力)对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加强的趋势不同,在中国,商业权力还不足以构成对媒体的决定性影响。在国外,“公司表达意见的自由、特别是发布销售信息的自由已经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发生的共同变化”。“实际上,全球市场日益被大型文化工业公司所操纵”。[6](PP.11-12)媒介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媒介逼上了市场的轨道,赚取足够的资金成为媒介不得不向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业低头的基本原因。就中国而言,目前并无任何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可以对媒体施加如此的影响。尽管多年来不断有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企图进入大众媒介领域寻求自身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有关的政策在大众传播内容的决定权上对非媒体的各种社会力量关闭了大门。尤其在人们十分感兴趣的新闻(宣传)领域,目前各种商业力量无任何染指的可能。
从媒介自身的权力(专业主义理念的控制)看,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媒介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因此在与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博弈中一直在企图将专业主义理念通过大众传播过程体现出来。但无论媒介曾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宣称,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1]。此话可以被理解为在媒体内部控制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媒介人的自身利益。虽然新闻专业主义是近年来媒体人的一面旗帜,但由于管理体制(主要是经济来源)上的一些变化,我国媒体人的身份由原来的“准公务员”转变为要自食其力的“企业人”,集体和个人的经济收入都直接与媒体的经营状况挂钩,因此如何在传播活动中求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媒体人的重要目标,也就成为媒体人在控制媒介时考虑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在上述的三大控制力量中,发挥主要、核心作用的无疑是党和政府的控制力量,其他的控制力量是在党和政府力量之下发挥作用的。当几种控制力量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其他控制力量当然要让位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量。媒体必须将视其为至高无上的、必须服从的、不得讲任何条件的控制力量。
政府(执政党)对媒介的控制并不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它是通过由上到下的各级党政官员来执行的。对这一情况笔者早在1991年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全民所有制决定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管理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各级党政干部手中,由他们代表党政机关对大众传播事业进行控制和指挥。这些干部的思想水平、风格特征直接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水平、风格和特征。客观地说,党政干部的绝大多数是一心为人民办事的,在控制和指挥传播媒介方面也是出以公心,试图在最短时间内充分发挥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使其成为建设强大祖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十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真正了解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式。换句话说,有利用、支持大众传播媒介的热情,却不掌握传播事业的基本规律去控制它、使用它。”*段京肃《改革开放与传播观念的变革》,1991年4月2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宣读。今天看来,大众传播事业被各级干部掌握控制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
四 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的问题
近几年笔者围绕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核心因素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了观察、访问,得到了一些相关的第一手材料,切身感到了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传播的媒介工作者面对官方和代表官方的个人的控制力量时的“难言之隐”。而这些媒体主要是一些被认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认为:“市场化新闻模式有它的优点:第一是能把政府排除在新闻运作结构之外,令政府对新闻的干预减少。”[9](P.35)而事实上这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幻想。在基层,许多官员片面地理解了中央关于“党管媒体”的原则,认为党管媒体就是官员自己管媒体,媒介作为党的喉舌的功能成为官员个人的喉舌。在他们眼中,当地媒体是自己手中随心所欲的工具,是自己工作成绩的光荣榜,是自己日常工作的传声筒。由于媒介素养低,他们不掌握基本的媒介运作规律,经常在媒介管理中提出一些完全违背规律的要求。
(一)市场化媒体的人事权控制在党政机关及官员手中,媒体管理的专业人才常常由不懂媒介运作的人员充任
《××晚报》常务总编X先生:我在晚报干十几年,最大的问题是体制。晚报是市场类报纸就应放在市场上,实际上限制太多,要继续承担党报的任务。我们市上管新闻的(领导)什么都不懂,有时改的稿子标点符号、语句都不通,但要求你就要这么做,编辑不敢改。我们认为是市场报就要接受市场的挑选,但是运作中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领导的任命,人员的任用都是他们说了算,而且经常给你压(安排)人,总编辑根本没办法。(上级部门)既然要管就应该全管,可是花钱、挣钱的事他不管,对设备都不管,越做越难办。对中央规定的几不准报、红头文件规定的我们能理解,可恶的是我们任何一个领导都能下命令。再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体制,班子的配备是上级说了算,谁跟他们好就提拔,我们是市场化的报纸,可干部的任命都是他们定。*2004年7月12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二)总编辑(社长)直接对管理部门负责,而不是对读者负责 将新闻传播媒介的党性原则片面理解为对自己的直接上司服务,媒介成了党政机关负责人的“排行榜”和日常工作的“流水账”。
《科技×报》社长、总编辑Y先生:我在这家报纸做了两年(总编辑),我非常谨慎,从不涉及批评,你不让报道的我就不报道,你说了我就不报道,凡是说了(不让报道),(报纸)又报道的是(总编)没本事,和领导对着干。我两年没有受过(上级)一次批评,以前我在晚报时每个月要被提溜去批评一顿。现在我的运动员(编辑记者)是年轻的,不管前锋怎样踢,我的把关人(总编副总编)是超一流的。我在本报两年没被批评一次,这是奇迹。②
《××日报》新闻部主任F先生:你的文风,你的报道思路必须是为上负责,为下负责你做不到,这可能是党报的通病。党报跟主要负责人的思想解放程度有很大关系,像宣传部长管、市委书记当然也要管。作为党报必须在体制上松绑,要相信我们能办好,但官本位的思想强烈,目前还没有减弱的趋势,这样你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县区好多通讯员的稿子都没有版面登。*2004年8月4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三)党政负责人直接插手新闻报道,视新闻媒介为自己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 有的领导人认为自己是“万能型”的人才,对什么都内行,随意对媒体发号施令,甚至干脆自己操刀上阵。在新闻报道的业务领域,媒介专业人员的自主权极为有限。
2007年8月20日长江三角洲某省会城市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市“交通事业发展白皮书”。会后不久,该市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宣传的副部长便接到了市长电话,给出了该新闻稿第二天见报时的版面要求,并拟出了大标题,要求一个字都不许动,报纸只有照办。*这是笔者亲历的一件事情。
在文革时期曾有地方报纸同人民日报对版面的事,那是因为极左政治的原因。而今政府领导仍然将对新闻媒介的控制做到如此之细,却并不是特例。
西部某省会城市的电视台台长告诉笔者,该市市委书记曾经要求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将他本人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7000余字)全文播出。后因新闻节目的时间只有20分钟,加之还有其他新闻,所以书记的讲话只播出了摘要。书记为此大光其火,将台长召到办公室严加批评,并明确告知:再发生这种事情就换人(台长)。*2004年7月8日访谈录音整理稿。
东部某省会城市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告诉笔者,在每晚本地新闻节目内容定稿后到播出前的一段时间中他采取不接电话的办法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无论是什么领域,只要是涉及批评的稿件,总会有人在第一时间知道并立刻找到相关的上级领导打招呼,有的领导明确说:就是开天窗也要把某某稿子撤下来。这位主任不得不在节目播出前“玩失踪”,消极对抗来自各方的压力。
最典型的例子如,辽宁西丰县因对媒介报道不满,竟然派公安人员携带传唤文件进京试图拘捕中央媒体记者。权力干预媒体的随意性一目了然。至于以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为代表的控制机关不时发出的关于“不准”的指令,因许多已经公开,此处不赘。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对大众传播的把关相对于怀特提出把关理论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大众传播媒介运行的过程中不仅仅存在着权力巨大的“把关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掌握不同权力的“把关人系统”。对媒介的管理细到如此程度,有的可能是因为官员对新闻传播有兴趣,想借此“票”一把,而有的则是将媒介当作了自己手中随心所欲的小玩意。在层层把关人心目中,并没有媒介的市场竞争意识,甚至也没有媒介的受众意识,他们只是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出发对媒介进行控制,媒介的公共资源性质在这里荡然无存。
五 研究与结论
在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几种权力中,执政党及其政府是实力最强大的力量,它将媒介资源和传播市场资源掌握在手中。而它对媒介的控制目的则主要体现在对传播内容的控制上,“有选择地发布信息的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根本”[15](P.74)。在保证传播内容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传播形式是次要的。席勒早已指出,国家是传播服务的主要使用者[16](P.90),尽管学界和业界一直试图通过强调媒介的“公器”性质和“专业主义”的精神提升政府以外的社会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力,但几无成效,因为党政机关在传播中的角色极为特殊,“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分配者、规则制定者”[17](P.518)。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目前我国媒介中的所谓“主流媒介”是掌握在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手中,这些是媒介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主持制定的各种媒介运行规则自然带上了有利于自身的东西。因此在实际的媒体运作中,无论是否是“主流媒体”,都要在“主流媒体”的规则下活动。
以广告为核心的商业控制目前在我国的大众传播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明显。广告宣扬的绝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商品,它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向社会发展的深层扩展。“广告不仅仅是促销商品的工具,它还控制着日常生活,支配着社会关系。同时广告引导人们自私,不关心他人。它同时又给人们强加了一种集体品味。”[18](P.71)但广告商的行为同样必须限制在制定的规则之内,这其中有的规则是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明确的,更多的则是通过随时下达的各级党政机关的文件或“精神”确定的。
对媒介产生明显控制作用的第三种社会权力来自广大的社会公众。媒介运行需要能够有效推销自身的良好市场环境,而这一市场环境的核心力量就是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早已认定“受众为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16](P.83),麦奎尔引用加拿大人史密勒的观点说:“受众实际上是为了广告主而运作的(因此,是为了最终的压制者而‘工作’)。受众付出闲暇的时间来观赏媒介产品,然后这些‘劳力’就被媒介以一种‘新商品’的形式打包出售给广告主,整个商业电视和报业系统,就是依靠在经济上剥削受众来榨取剩余价值的。”[4](PP.308-309)媒体的商业性越明显,受众在其中所受的“榨取”就越严重。不过媒介信息到达受众必然要受到大众的选择。“通常,人们会带着对政治问题和候选人的某些既定想法来看电视、读报纸和浏览网站。这些态度和意见会像某种思维过滤器那样发挥作用,将人们感觉不舒服或与自身想法不吻合的信息过滤出去。”[19](P.161)
在几大权力的交互作用中,不同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不公平。如贝戈蒂克安在《媒体垄断》一书中所描述的:“大量的社会成员和他们的事物被媒体忽视,被报道为逸闻趣事,或是以最糟糕的形象出现——作为少数族裔、蓝领工人、中低收入人群,或穷人。他们只有在重大事故、罢工、被追捕等惊险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新闻中。其他一些团体和机构,如政府、学校、科研部门、非主流政治运动等,会时常受到新闻的监督和批评。另一类少数人群,像运动员、服装设计师、演员,定期得到媒体的追捧。”[15](P.87)随着新媒介的作用日益强大,有人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对社会信息资源的控制将渐趋公平,然而也有学者早就指出:“权力正日益集中于从发展中获益的精英手中,他们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拥有的特权。”[20](P.3)在媒介资源仍然是紧缺资源的情况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媒介资源将被以政府(执政党)为核心的社会精英集团所控制。所以这种带有人为色彩的媒介资源紧缺现象将持续下去。
中国的媒介体制决定了政府(执政党)在掌控媒介时的特殊角色地位——“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分配者、规则制定者”,其他任何力量在媒介资源的分配和媒介权力的掌控中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推进,政府(执政党)在媒介的掌控方面已经表现出越来越科学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新闻传播媒介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1]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这是一种开放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又是一项公民掌握信息的可操作的法规。这一条例实施不到半个月,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从政府到各级媒介在此次自然灾害的信息发布和报道中表现了我国媒介前所未有的积极和开放。有几个明显的突破:一是以最快速度发布信息,基本做到了与事件的发生同步,改变了以前突发重大事件消息“出口转内销”的现象;二是在第一时间允许包括门户网站在内的互联网媒体发布自采的消息,而不再局限于新华社通稿。众多媒介迅速选派记者进入灾区,以连线、直播等方式进行实时报道,在新中国的新闻报道历史上是第一次;三是允许境外和国外媒体进入灾区自由采访并独立发稿,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众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在现场直接接受境内外媒介的采访;四是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对灾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形象性报道,给受众以关于灾害的详细、准确信息,突破了以前的同类报道以英雄人物和事迹为主的报道模式;四是凸现了新闻对“正在进行中的事实”的报道,满足了广大受众了解事态最新状况的需求;五是凸现了对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众多人物在面对灾害时的感情报道,使受众通过报道产生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此次震灾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力量的一次机会,全国各地在如此短的时间中产生如此快速和巨大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本次全新的新闻报道模式。它充分说明,媒体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各种控制力量在行使自己对媒介的控制权利时必须尊重这些规律,才能使媒介生产力得到最大的发挥,使媒介产品得到社会和公众的真正认可。如此公开快速的报道并没有出现某些管理部门的人员以前所担心的那种“负面作用”,它提示我们在媒介控制过程中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信任媒介、信任公众,是发挥媒介控制力量的前提。
[1]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3]童静蓉.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6,(1).
[4]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刘晓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M].顾宜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M].杨晓红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9]苏钥机,李月莲.媒体理论[C]//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林明志.作为操纵手段的资源控制[EB/OL].(2005-08-25).http://www2.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
BlogID=210978&PostID=2531820&idWriter=0&Key=0.
[11]尹连根,王海燕.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EB/OL].http://blog.xinhuanet.com/blogIndex.do?bid=76358&aid=15276703&page=detail&ag Mode=1.
[12]潘忠党,陆晔.成名的想象[J].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4).
[13]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吴靖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史安斌主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5]本·H.贝戈蒂克安.媒体垄断[M].吴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16]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7]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C]//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8]阿瑟·阿萨·伯杰.媒介分析技巧[M].李德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9]施密特·谢利·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M].梅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0]Srinivas R Melkote,H Leslie Steeves.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ero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M]. Sage Publication India Pvt Ltd.,2001.
[21]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沈松华)
CoreFactorsintheControllingForcesofMassCommunicationMedia
DUAN Jing-su, REN Ya-s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The controlling force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various social factors which include political power, market power and public power. The controlling capability of the market power upo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has kept on increasing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fore, a marketized mass communication model is regarded as a basic and ideal communication control model at present. However,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in China remain special. It is the governmental controlling force (ruling party) who plays a dominant role among the three controlling factors, namely market, public and government. When a conflict happens among various controlling factors in the society, other controlling forces would have to give in to the governmental power (ruling party).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market made up of complicated components, the government (ruling party) is “a producer, a consumer, a distributor as well as a ruler maker”, hence a core factor in the controlling forc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government; market; public; control
2010-03-01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网络社会的传播控制研究”分项成果
段京肃(1955-),男,山西襄汾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重点为传播与社会发展、媒介研究、媒介素养研究;任亚肃(1957-),女,山西平遥人,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和图书管理。
G206.2
A
1674-2338(2010)02-0070-07